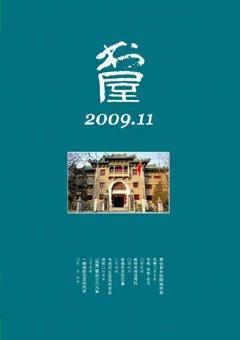暢銷書閑話兩則
雷池月
《蟹工船》的紅火不是一種文化現象
2008年,日本十大流行詞語中,竟然包括了“蟹工船”這樣一個當代人根本不知所云的生僻字眼。這是因為年初再版了一本名為《蟹工船》的小說,該書上半年銷量就突破了六十萬冊,到今年春天,發行數已累計百萬冊以上,高居暢銷書榜首。小說的暢銷又帶動了改編的熱潮,漫畫版本銷量達數十萬冊,由偶像派和實力派明星合作演出的電影也于今年夏天上映。上述空前火爆的形勢自然在全世界產生了影響,首先是歐洲,《蟹工船》一書強勢進入市場,被推為“working poor”的必讀書目,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中國反應也頗快,譯林出版社于今年一月就推出了中文版本,只是在學界和市場似乎都并未引起太大的動靜,這一現象可以讓人產生多方面的思索。
《蟹工船》是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成名作,是一部反映勞動階層的痛苦與抗爭的書。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尚處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階段,為了爭取更多的外匯,興起了捕撈并加工海蟹主供出口的產業,附有加工設備的捕撈船就叫“蟹工船”。海蟹產于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北方海域,那里氣候寒冷,遠離陸地,船工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都非常艱苦,所招募的工人大多是赤貧且并無一技之長的臨時工,由于船主和工頭們的刻薄和殘忍,船工們團結起來和雇主展開斗爭——《蟹工船》所反映的就是這些船工們生活和斗爭的一個斷面。作品具備當時左翼文學最基本的特質,即通過揭露社會黑暗的現實來喚醒被壓迫者的階級意識,促進階級的分化和對立,從而推動社會革命的進程。
這部書為小林多喜二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可就在此書問世后不久,小林于1933年2月在獄中被軍警拷打致死。當時世界左翼文壇反應十分強烈,紛紛表達對日本軍國主義者暴行的譴責和聲討,魯迅代表“左聯”發出的唁電在中日兩國都很著名。由于1932年的軍部政變后政治環境的險惡,《蟹工船》一書并未在日本繼續產生影響,而戰后日本進入了由所謂“神武景氣”所帶動的資本主義高速發展時期,勞資矛盾由于勞動者處境的改善而相對緩和,正如有位評論家所言:“日本人把蟹工船轉移到國外去了,他們自己成了吃蟹的國家。”于是,小林多喜二和他的《蟹工船》長期地遭遇了冷漠甚至遺忘。
《蟹工船》在問世八十年后的今天大受歡迎,據說“最大的理由是日本的‘新貧人口從中找到了折射自己受窮的一面鏡子”。“新貧人口”即指那些在當今西方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中涌現的極其貧困的群體。由于長期的不景氣,業主越來越不愿意雇傭正式工,因為那要負擔諸多的社會保險,不像臨時工可以隨時解雇,這和《蟹工船》里老板招募工人的情景十分相似。日本今天的臨時工已占勞工總數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四點一),這些臨時工被解雇以后,常常“流落街頭,日食面包二個,在網吧過夜,走投無路,或因患病無錢救治而自殺”。《蟹工船》的讀者大量的就是出自這個階層,日本偶像作家雨宮處凜說:“《蟹工船》里寫的與現在自由打工者的狀況非常相似。”“現代打工者和《蟹工船》里的漁工在情緒上是相通的,他們的不滿一樣地集中在兩個方面:工作環境的惡劣和管理者態度的惡劣。”年輕的讀者反映說:“我很羨慕小說里工人團結一致面對敵人的做法”,“船上的工人都是我的兄弟,就在我的周圍”。
有評論家指出,“蟹工船”的火爆彰顯了日本從未有過的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現在的“新窮人”生存狀況有的還不如當年蟹工船上的漁工。這個說法或許失之夸張,但可以肯定一點,與《蟹工船》的紅火密切相關的是,“新窮人”現象的惡性發展確實導致了日本政黨生態的極大變化。以日本共產黨為例,自上世紀中葉以來,面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連續繁榮,日共的政策一直左右搖擺不定,實力和影響日趨減弱,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世界社會主義低潮的到來,生存狀態更是每況愈下。世紀交替之際,日本經濟隨著泡沫的破滅走向衰退,日共才終于獲得了喘息和復蘇的機會。到了此次金融危機,竟可說是好運連連。他們不失時機地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站在維護窮人權益的立場,向資本主義制度下無法根治的各種社會弊病(包括“新窮人”現象)進行猛烈的揭發和抨擊。日共的這個態度理所當然地贏得了底層群眾的擁護,一年多來,《赤旗報》的訂戶逐月上升,每月平均新增黨員一千五百人,黨員總數已達四十余萬。日共在國會的議席已經超過曾經是日本第二大黨的社民黨。社民黨控制工會的傳統局面也早已根本改觀。所有這些都說明《蟹工船》的火爆既是一種文化現象,又并非一種單純的文化現象,它確實是當前日本經濟、政治、社會諸多危機交相作用下,在文化這塊屏幕上產生的鮮明投影。
左翼文學在取得主流地位之前,由于它所堅持的批判立場所決定,在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歷程中,確實作出過重大的貢獻。《蟹工船》一書的命運似乎也可以佐證這一點。但在取得主流地位之后,由于“工具論”之類的誤導,在權力的干預下,左翼文學的地位和作用往往產生質的變化。以我國的情況而言,就曾經留下過或者“假、大、空”,渾身虛胖(如大躍進時期);或者氣若游絲、命懸一線(如文革階段)的史鑒。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于政策的變化,出現了一段由批判精神引導的文學的繁榮,但左翼文學不僅未能高舉批判的旗幟掌控話語主導權,相反聽任自己被逐漸邊緣化。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隨著社會的轉型,兩極分化和勞資矛盾一類社會問題出現了,這本來是左翼文學可以大施所長的時空條件,但人們看到的卻是它近乎失語的狀態。想一想歐洲,曾經產生了多少表現資本家和工人這兩大階層各自的生存狀況和相互間關系的作品和大師?而在我們這里,能拿得出一本真實地(不求其深刻地)反映這一當代最重要主題的書么?“富二代”和“農民工二代”之類新名詞已經正式進入媒體和日常語言系統——產業工人做到“第二代”還被稱為“農民工”,這叫什么話?這后面潛藏著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危機能不令人憂慮嗎?從前我們常說“蛋糕做大了,問題自然解決”,現在,“蛋糕”已經大了幾十倍,而問題卻還在繼續發展并拖累著國家前進的腳步,只有因為喪失信仰而麻木不仁的官僚才會對這一切無動于衷。關于資本反人性的本質,馬克思早已明喻于前,今天,礦難和黑窯一類事件又佐證于后,有志于建設和諧社會的人,都會明白自己的責任所在,可是,在這方面承擔著特殊重要責任的文學呢,它在哪里?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包養著一支數量不小的文學大軍,媒體上有時能看到他們聽到他們在角落里嘀咕,說:諾貝爾評獎委員會不能只有馬悅然一個人懂漢語,只有委員會改組了,中國人才有希望獲獎云云……
令自己難堪,讓他人尷尬
塵封了三十多年的張愛玲遺著《小團圓》不久前先后在兩岸三地出版,很是對書市造成了一些刺激。香港的情況最火爆,臺灣就比較一般,至于大陸,則遠不及上世紀八十年代《傾城之戀》帶來的那種震動了。海峽兩岸比較一致的反應,其原因也大概相同:這本書的自傳性質過于明顯了。廣大的張迷們喜愛的是張愛玲駕馭文字、描摹心理、營造氣氛的能力,而不是她個人古怪的性格和荒謬的情感經歷。《小團圓》的失敗之處,就在于她堅持要把自己生命中理應努力加以遮掩的部分,充分向他人展現。她或許是希望讀者能從純粹的文學或審美角度給予她理解。然而這實際上是絕無可能的,因為在中國人有史以來的所有政治高調中,民族大義向來是被擺在第一位的。很多喜歡她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涉及她個人往事的追索和評析,如今她自己竟直接走上前臺來講解,無論如何妙筆生花,那結果只能是:令自己難堪,讓他人尷尬。
據說,張愛玲曾經交代她的遺囑執行人宋淇,《小團圓》書稿要銷毀。但這只是一句話,書稿一直保留在她本人身邊。宋淇的兒子小宋(也已經年近花甲了)說,整理張的遺物時發現了這部稿子,由張愛玲本人工筆謄正,裝訂也很考究,足見作者并不真想毀掉它。小宋認為不該讓這本書就此湮沒,公開出版,不惟廣大張迷能享受到閱讀的愉悅,同時也算是完成了作者的遺愿。她地下有知,當為之欣慰。小宋先生的話大概是可信的,因為,他已經將大部分版稅捐贈給了香港大學的某個基金會。那就是說,沒有牟利的動機。
張愛玲堪稱一代才女,除了情商有點問題,語言功力、藝術感覺都無疑可以讓她置身于新文學重要女作家之列,只是還沒有到達夏志清所認定的那樣一個高度。她確實不能和魯迅、沈從文比肩,有些研究者把她和蕭紅并論或作比較,其實也是很不相宜的——倒不是什么高下之分,而是兩人差別太大。蕭紅是傳統的(請看她是如何為端木蕻良忍辱負重)、平和的(既不是勇敢的斗士,也不是馴服的順民)、良善的(她無負于她愛過的每一個男人);而張愛玲則是現代的(嫁與西人作婦當時仍屬罕見)、偏頗的(只服從感性的支配而拒絕理性的思考)、冷漠的(除了男女間的一時茍且,舉目世界何處曾寄托她永久的愛!)。作為一個作家,張的精神世界的某些缺失是致命的,這使她放棄了對所處時代最起碼的社會擔當,有時候甚至于是喪失了一般的判斷是非的能力。
龍應臺指責張愛玲“冷血”,當否且不說,至少這個“冷”字一針見“血”!張本人也從不掩飾自己的“冷傲”,至于“冷漠”、“冷酷”以至“冷血”云云,這類對她常見的評價,都可謂“雖不中,亦不遠矣!”她的“冷”,自然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可以說是她經歷和性格相互作用的結果。她出生于腐朽而沒落的清朝遺老世家,先人的煊赫早已隨時光飄逝,后人的不肖則堪稱“與時俱進”有增無減。從她懂事起,驕傲而敏感的內心,想必從未接納過她那些病態的、淺俗的親屬,當然她可能也沒有從親人那里得到過情感的溫暖。她有許多作品都使用了自己的家庭作為背景材料,以親屬做人物原型,但其中找不出一處細節或場景能給人帶來光明、溫暖或希望的感覺。她叫自己的母親為“二嬸”,形容自己的舅舅“像酒精缸里的孩尸”,親屬們這個吸毒,那個同性戀,還有她并無根據的對他人亂倫的猜想……這些揭露的后果當然很嚴重。早在她離開學校走向社會以后便和親人基本斷絕了來往。冷漠從少年時代就滲透進她的靈魂深處。
張愛玲很早(不過二十歲)便走上了文壇,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她的才華吸引了許多崇拜者,而她卻將崇拜者的胡蘭成選做了自己崇拜的偶像。她知道胡蘭成的漢奸身份,卻讓自己高傲的頭在胡的面前“低到地底下去”。以她和胡蘭成夫唱婦隨的關系,她也是可以按漢奸治罪的。何滿子先生就主張將她定性為漢奸作家。也是種種原因,戰后他受到了寬大待遇(當時大漢奸金璧輝的男寵、某李姓伶人就曾被捉將官里去問罪)。1947年,總算和胡某離了婚,但也是明離暗不離。此時胡蘭成如喪家之犬,生活無著,要依靠張愛玲的接濟(對此張的解釋是過去自己用過胡很多錢)。解放后,因為有柯靈、桑弧甚至夏衍這樣的大人物罩著,張的情況還不錯,不過經過“三大運動”之后,她也明白了此地不可久留,便跑到了香港。當時香港的情況不好,大量難民還在饑餓線上掙扎,何況她這種國、共兩方面都無法投靠的人,生計更是艱難,于是于1952年去了美國。她的英文不錯,可以進行寫作,但想成為主流作家以賣文為生卻絕無可能,只能找些資料員、管理員之類工作糊口。雖然她的才氣在聶華苓、於梨華這些人之上,但生存狀況卻無法和他們相比。經濟的困窘一直到她的書重新在臺、港打開局面以后才有所緩解,而當時她連回香港辦理出版事宜的機票錢都頗難籌措。在艱難的日子里,她的心境可以想見,大約除了以“冷漠”自勵,以“冷傲”自慰,還有就只可能是對自己遇人不淑的懊惱,這種懊惱,用《小團圓》里盛九莉那悲涼的自況來表達,就是所謂“漢奸妻,人可戲(欺)”。
晚年的時候,張愛玲在兩岸三地都已是暴得大名,但她的心卻似乎已經由冷漠而歸于冷寂,連追逐名利的本能都趨于麻木了。對于紅顏才女,年華的老去和才情的消逝總是構成正相關的。而且,由此導致的蕭索的心情和對外部世界的疏離感更是相輔相成。她越來越封閉自己,過著基本與世隔絕的生活。由于題材的枯竭,偶有寫作,也局限于對早年記憶的搜索(如《小團圓》之類)。丈夫賴雅去世后,她身邊沒有親友,以至于死在公寓里好幾天才被人發現。回溯她的一生,薩特所說的“他人即地獄”是個貼切的寫照。
《小團圓》是一部自傳體的小說,主要角色都有原型可以對號入座。張愛玲當時的創作動機,就是要就自己的過去向讀者(世人)作些說明。因為其時胡蘭成出版的新書《今生今世》引起了臺、港傳媒的熱議,張說她“不能讓別人壟斷了書寫這段愛情的權利”,要“不惜打一場筆墨官司”。于是《小團圓》出爐了。她將書稿寄給在香港的宋淇,讓宋聯系出版。宋看完之后勸阻了她,因為宋覺得,出版此書,一是會給胡蘭成制造更多的炒作機會,二是會令反日情緒高漲的臺灣讀者產生反感——他們不會接受張愛玲迂回表達的觀念,那樣一來,剛打開局面的市場就將前景難卜。宋的意見令張愛玲猶豫不決,《小團圓》就這樣擱淺了三十多年。說要“銷毀書稿”,那是在回答宋淇的諍言,但始終舍不得“毀”,因為其中有她自己很想交代明白的觀點。
什么觀點?不是民族大義,更不是政治正確之類,她不會企圖把自己說成“曲線救國”的義士,也不會像陳璧君一樣強辯“汪先生也是為了救國”。在書里,她其實只說明了一點,就是她在《色·戒》已經表述過的:一個女人被男人征服了(用她的原話,這征服是“通過陰道”進行的),從此,所有的倫常大義、是非標準于她就都失去了意義。她的這個表達應該是真誠的,但這畢竟只是她個人的觀點。所以當李安在《色·戒》影片里對這點作出真實而充分的演繹時,并不為所有觀眾所接受,連臺灣的中統老人也出來為王佳芝的原型鄭蘋如抱不平,說影片“玷污了愛國義士的英靈”,號召進行抵制。也許只有“易先生”(丁默村)才會從正面叫好——憑著自己超強的性能力,竟然讓一個身負使命的敵方女特工甘心為我所用,對丁默村這個摧花辣手(他玩弄過的良家女子和娛樂明星不可勝數)來說,沒有比這更令他愜意的事了。不過《色·戒》所取的是一種客觀敘事的角度,作者和讀者都可以見仁見智,匪夷所思的情節反而讓廣大張迷不會受到多大震動。《小團圓》就不同了,讀者很快查找出角色的原型:盛九莉就是張愛玲,邵之雍就是胡蘭成。人們或詳或略都知道他兩人的故事,也知道胡蘭成是個很齷齪的小人。所有愛讀張愛玲的人,大概都不大愿意接觸到張的這段歷史,因為人們多半不忍心看到張被胡玩弄、欺騙和背叛的細節和場景。在胡蘭成眼里,張的分量還不及另一個情人——流氓漢奸吳四寶的老婆佘愛珍,這不能不令張迷們痛恨和惋惜。而《小團圓》竟還要翻開沾滿污漬的舊賬本,披露作者的那份自覺的卑微的愛——你自己即使不覺得難堪,也應該想到“粉絲”們的尷尬。孜孜矻矻研究“張學”的教授對此只能毫無底氣地解釋:“小說就是小說,不能夠在生活中對號入座。”多為難啊!此稿當年不毀,是失策了。
據說,張愛玲晚年曾有意研究丁玲。張一生眼界極高,甚至表示過不能接受冰心和她相提并論,何以會對人生道路的選擇和她完全不同的丁玲感興趣?想必是發現了彼此相通的某個心靈的節點。這使我想起五十年前在大學資料室里讀過的一本書,叫做《勞者之歌》(或《勞動者之歌》?),是三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合編集。內有丁玲作品《續莎菲女士日記》,講述了她和馮達在南京時的一段戀愛故事(這本書和這篇作品解放后都未再版過,因此,讀過此書如今還健在的人肯定不多了,但張愛玲應該是讀過的)。馮達是個變節分子,丁玲和他相愛了,同居了。丁玲為自己的這段愛情所付的代價是很慘重的,從延安時期的“審干”到解放后的“肅反”、“反右”等歷次政治運動,反復受到猜疑盤問、批判指責,馮達成了她一處永不能愈合的潰瘍。她對此事一直保持著低調,雖然解放初期(自己剛獲得斯大林獎金,正炙手可熱)在被周揚逼急了的時候(竟公然在大會上就“歷史問題”不點名地威脅),也曾挺身而出表示抗議,但終究不敢正面接招,再沒有當年寫《續莎菲女士日記》時的勇氣。丁玲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和她為愛所承受的委屈,張愛玲想必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才會動了“研究”的念頭,如果不是這樣,我真想不出還有什么理由能把這樣兩個完全挨不著的人聯系在一起。張愛玲和丁玲,情感遭遇或許有近似之處,后來的處置態度卻迥然不同。丁玲懂得回避,盡管還是為此經歷了無數的坎坷(雖然另有除此以外的諸多原因),最終卻總算獲得了蓋棺論定的榮譽。張愛玲卻不然,對于理應回避的往事,卻偏偏不肯放下。我有時設想,她也許是忘記了焚毀書稿,而且又沒有估計到自己的突然去世,那么,如今她若地下有知,恐怕就只能夠喟然長嘆:“小宋誤我!小宋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