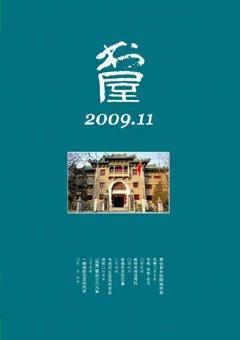“另冊”里的三六九等
賀越明
偶然在書店看到《我的人生檔案——賈植芳回憶錄》一書,翻了一下目錄,毫不遲疑地掏錢買下。理由再簡單不過,作者賈植芳曾與我有“一面之緣”,而書中“我的三朋五友”一輯,寫到兩位我熟識的師長,一是王中教授,我讀本科和研究生時的系主任;另一是潘世茲教授,雖然也在復旦大學,但從未教過我,卻又有數年的交往。即便是為了看看賈先生如何寫那兩位我還算了解的前輩學者,也足以激起我購書的沖動了。
與賈先生的“一面之緣”,實際上是一次偶然的路遇。記得大約是1986年夏季,我在該校新聞學院任教,有天中午去校門對面的教工食堂吃飯,看到迎面有位瘦小的老人緩步走來。同行的女同事輕輕地說了聲“賈植芳”,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人停下腳步,與她聊了幾句。那女同事向他介紹我:“系里的青年教師。對了,他也是山西人,和你是同鄉。”我恭敬地叫了一聲“賈先生”,沒再言語。不知是聽口音還是看外表,他斷定我沒有在山西生活過,笑著以濃重的家鄉口音說:“你是晉籍滬人,我是滬籍晉人。”我一聽,老人不愧是江湖上闖蕩過來的,真是機敏,一句話就點出了我與他在籍貫意義上的異同。因被老人如此幽了一默,時隔二十多年還記憶猶新。
賈植芳那年已七十歲,正是其一生中“夕陽無限好”的時光。他的大名,因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的罪名,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起陷于縲紲十數年,至少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院系盡人皆知,但他的全部經歷卻未必人所共知。他早年留學日本攻讀社會學,1937年聽聞盧溝橋事變毅然回國,帶筆從戎,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為此坐過日偽警方的監獄;抗戰勝利后,因參加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又被中統特務關進大牢。他一直追求進步,向往革命,為此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一生中三度蹲大獄,而又以解放后那次為時最久,這還不計出獄后被監督勞動的日子。所以,他在這部自傳體回憶錄里,形容自己經歷過的那些特殊歲月,是從“人”變成了“鬼”。換言之,是公民的權利被剝奪,打入了“另冊”。
可是誰能想到,在也成為“鬼”的同校教授潘世茲看來,賈植芳與他是有區別的。賈植芳在該書的《我的后來者——潘世茲先生》一文中,記述了在校印刷廠被管制期間與潘世茲的一段對話:
有一次,他對我講:“你的情況和我不同,你是共產黨的宣傳人員,我是洋奴買辦,是帝國主義走狗。”我立即抗議道:“你別胡說,我只是個作家,不是共產黨的宣傳人員。”潘先生知道我的事情,也曉得我進步教授的身份。我進震旦中文系當教授,一去就做了系主任,頗帶點占領“資本主義學術陣地”的意味。我也知道像潘先生這樣的人對左翼作家懷有偏見,一概將他們視為“宣傳人員”而非作家。他聽了我的申辯,笑著說:“什么作家,共產黨的宣傳人員罷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見第368頁)
這一段文字,描摹出這兩位學者在相同境遇中的不同定位,既有自我認識,也有彼此認知,可謂準確而傳神!我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拜識退休居家的潘世茲,并受托每月為他代領薪資,有機會多次登門,深感其晚年仍遺留極深的洋派人物印記。他出生于上海工部局高級華人幫辦家庭,在英國劍橋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圣約翰大學歷史政治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長等職。解放前,無論從教育背景還是職業經歷,都只是與英、美國家有關,而與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無涉,因而他在建國初批判英美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中就受波及,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遭人誣告欲與王造時、孫大雨成立“中華社會黨”,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坐牢七年。不光是教育背景、職業經歷,還有思想信仰、學術志趣,他與賈植芳都無相近相似之處。即使同為“難友”,他對早被貼上“洋奴買辦”、“帝國主義走狗”標簽的身份頗有自知之明,確認身處社會階層的最低層,并以“自慚形穢”的口吻道出了與賈植芳的彼此差異所在。的確,如果不是因為都被列入“另冊”,又同在“文革”中發配到一個地方監督勞動,他們二位很可能不會來往,更不用說是無話不談了。
盡管賈植芳被潘世茲視為“共產黨的宣傳人員”,而他也自認是“左翼作家”、“進步教授”,但令人絕對想不到的是,在另一位“另冊”成員的王中教授眼中,竟又是迥然不同的定位!在《回憶王中》一文里,賈植芳描述了其與王中接觸的切身感受:
在干校里,他的身份跟我們還有所不同:他是革命干部,雖然劃為右派,但是屬于可以改正之列;我的身份卻是“專政對象”,屬于“敵我矛盾”的“反革命”之列……即使在“文革”當中,他已經也被打翻在地,卻仍然以革命干部的觀點看人,覺得他們當右派,乃是他們自己內部矛盾,和我們根本不同,我們是搞“反革命”的,覺得“我們黨”是不會冤枉好人的。要說冤枉,只有鄧拓這些人才是冤枉的。而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本來就形形色色,我們黨怎么會弄錯呢?說到底,他還是一個很正統的黨員,而且有很強的優越感。(見第332頁)
這段文字,寫的是賈植芳的內心感覺,而他是從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在人際關系上應會更敏感些。在我讀本科和研究生時期的印象里,王中確實與常見的學者不太一樣,言談舉止有一股明顯的官氣,不怒自威。這不奇怪,他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入讀山東大學外文系,但主要精力用于參加學生愛國運動;抗戰爆發后加入了中共,以后長期從事兵運和新聞工作;1949年5月隨解放大軍進入上海,擔任市軍管會新聞室軍代表,參與接管新聞機構;1950年調到復旦大學,先后出任校黨委常委、統戰部長、副教務長、新聞系主任等職,直至1957年中期因“宣揚資產階級新聞觀點”被打成“右派”。以他的革命資歷、高干級別以及所擔任的各種職務,尤其是統戰部長一職,無疑更似派來占領“資本主義學術陣地”的,這就使他身上難免具有濃重的政治優越感。但當自己也淪落為“鬼”時,還對其他的“鬼”流露出這種優越感,則只能視為氣質、習慣使然了。不過,賈植芳在文中還寫道:“一直到平反以后,他和我們在精神上還是有距離,覺得我們在精神上還是‘反革命。”這一句,當是賈先生個人獨特的感受,沒有任何王中的言行可資佐證,讓我讀來多少有些疑惑:王中應該不至于那么冥頑不化啊!在我的記憶中,他不光在新聞學術觀點上很大膽、超前,就是平素談吐所表露的觀念也很開明、開放。也許因為彼此經歷和身份頗不相類,他與賈先生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未必一致,但怎么可能繼續“在精神上”視后者為“反革命”呢?對這一憶述的準確性,我以為似可存疑。
上世紀中葉后開始流傳一句名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后還會是這樣。”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中,賈植芳、潘世茲和王中這三位和許多老學者一樣,總體上都被歸于“右”的一類,而且只有罪錯大小之分,政治身份歸屬并無差異。可是,看到他們盡管身處“另冊”的悲慘境地,各自的心里對彼此卻有“不同”的定位,還能分出個三六九等,這就不能不使人驚怵和悲哀!在階級斗爭的政治濃霧籠罩下,先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后斗革命“同路人”,再斗黨內“走資派”,如此這般,大網一撒再撒,網眼越來越小,沒有誰能逃脫落網的命運,而因為畢竟有前后之異,加上原本的出身和經歷也有分別,便給“另冊”中人帶來了不同的心理影響和定位依據。顯然,并非他們自己對社會等級有了新的發明和創見,而是這個社會曾經不斷、反復、升級的“折騰”導致的政治分層,在他們之間鍥入了“精確”得可怕而又荒誕的政治定位關系。
設若不是恰好對王中、潘世茲這兩位教授較為了解,我相信自己恐難解讀賈植芳回憶錄的上述有關文字;同時也可斷言: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讀者,將不可能領悟這些文字蘊含的意義及語境了。潘世茲、王中和賈植芳,都先后過世了,其中以賈先生受難最早,吃苦最多,倒是最長壽的,享受了較長一段苦盡甘來的晚晴歲月。我想:升入天堂后,那里沒有政治運動的折騰,人人都是平等的,除了先來后到外,彼此該不會再有任何有形或無形的等級區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