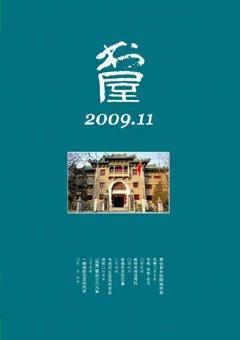徐志摩惹禍的三篇序跋
彭林祥
現(xiàn)代文學(xué)三十年期間,文事論爭層出不窮,真是你方唱罷我登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劉炎生先生著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論爭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就梳理出了現(xiàn)代文學(xué)三十年間共九十次文學(xué)論爭,由此可見新文學(xué)文壇文事論爭發(fā)生的密度。而作家間論爭總是需要由頭,或者說是導(dǎo)火線。在筆者收集整理新文學(xué)序跋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許多新文學(xué)序跋常常充當(dāng)了文壇論爭的導(dǎo)火線。拙文僅以徐志摩所寫的三篇序跋為例,梳理因序跋所引起的三次文事論爭。
1923年7月7日的《時(shí)事新報(bào)·學(xué)燈》刊登了徐志摩的詩作《康橋西野暮色》,這是一首沒有標(biāo)點(diǎn)的詩作,詩前有一段小序,專門對詩作有無圈點(diǎn)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小序中,徐志摩有這樣的話:
我常以為文字無論韻散的圈點(diǎn)并非絕對必要。我們口里說筆上寫得清利曉暢的時(shí)候,段落語氣自然分明,何必多添枝葉去加點(diǎn)畫。……真好文字其實(shí)沒有圈點(diǎn)的必要……我膽敢主張一部分的詩文廢棄圈點(diǎn)。
爭論由此引發(fā)。7月13日,《晨報(bào)副刊》上登出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十地的《廢新圈點(diǎn)問題》,他質(zhì)問徐志摩:不知西洋的“圣經(jīng)賢傳”上有無圈點(diǎn)?彌爾頓一流的妄人所編的不說也罷,不知道像徐先生一樣有教化的西洋紳士們所看的古書,是否都用散字母排成平方一塊的版本?徐先生的書庫里一定有不少沒有圈點(diǎn)的西洋“圣經(jīng)賢傳”,何妨請用銅版印一頁在《學(xué)燈》上,給我們長點(diǎn)見識呢?另一篇是松年的《圈點(diǎn)問題的聯(lián)想》,也對徐志摩的小序中的關(guān)于圈點(diǎn)的主張?zhí)岢隽伺u:“我們每嘆一部好書沒有圈點(diǎn),但世間也會有嘆息痛恨于一部好書可惜有了圈點(diǎn)的人。”稍后的7月18日,《晨報(bào)副刊》上又登出了黃汝翼的《廢棄新圈點(diǎn)問題》,對徐志摩的觀點(diǎn)進(jìn)行了批評,并把徐的觀點(diǎn)奚落稱為“徐志摩定律”。徐志摩實(shí)在不堪他們的詰問和諷刺,在看到黃汝翼文章的當(dāng)天,他就寫了致伏廬(指《晨報(bào)副刊》編輯孫伏園)的《一封公開信》,此信在22日的《晨報(bào)副刊》登出。在信中,他申明:
我相信我并不無條件的廢棄圈點(diǎn),至少我自己是實(shí)行圈點(diǎn)的一個(gè)人。一半是我自己的筆滑,一半也許是讀者看文字太認(rèn)真了,想不到我一年前隨興寫下的,竟變成了什么“主張”。不,我并不主張廢棄圈點(diǎn)……
他在申明自己主張的同時(shí),也承認(rèn)了自己筆滑。但因前面幾篇批評他的文章的發(fā)表,徐又對《晨報(bào)副刊》的編輯方針提起了意見:
所以我勸你,伏廬,選稿時(shí)應(yīng)得有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揣詳附會乃至憑空造謊都不礙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這是編輯先生,我想,對于讀者應(yīng)負(fù)的責(zé)任。
這是針對作為編輯的孫伏園,責(zé)怪編輯為什么要發(fā)批評自己的文章,這就得罪了孫伏園。所以在徐的公開信的后面,作為編輯的孫伏園寫了《伏廬后記》,對于徐志摩的意見進(jìn)行了反駁。《后記》中首先就批評徐志摩:“辯論而至于教訓(xùn)記者,這是下下策。”最后,孫伏園反唇相譏道:“平常作者被人駁倒無可申訴卻遷怒于編輯的窠臼,這是大文學(xué)家們不屑為的。”
徐志摩與魯迅的結(jié)怨,也是緣于他的一篇小序。1924年12月1日,《語絲》第三期出版,刊有徐志摩的譯詩《死尸》(波特萊爾作),前面有他寫的一小序,他提出了自己的“神秘文藝論”:“詩的真妙不在他的字義里,卻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節(jié)里;他刺戟著也不是你的皮膚(那本來就太粗太厚!),卻是你自己一樣不可捉摸的魂靈。”接下來,他又有這樣的話:
我深信宇宙的底質(zhì),人生的底質(zhì),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zhì)——只是音樂,絕妙的音樂。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鴨,樹林里冒的煙,朋友的信,戰(zhàn)場上的炮,墳堆里的鬼燐,巷口那只石獅子,我昨夜的夢……無一不是音樂做成的,無一不是音樂,你就把我送進(jìn)瘋?cè)嗽喝?我還是咬定牙齦認(rèn)賬的。是的,都是音樂——莊周說的天籟地籟人籟,全是的。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朵太笨,或是皮粗,別怨我。你能數(shù)一二三四能雇洋車能做白話詩或是整理國故的那一點(diǎn)子機(jī)靈兒真是細(xì)小有限的可憐哪——生命大著,天地大著,你的靈性大著。
這篇小序引起了魯迅的反感。半月之后,在《語絲》第五期上刊出了魯迅的《“音樂”?》。文中開始就說,因夜里睡不著,坐起來點(diǎn)燈看《語絲》,不幸就看見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談。接著,他馬上糾正,不是神秘談,而是看到了音樂先生的關(guān)于音樂的高論。但是,對于魯迅來說,他這樣皮粗耳笨的人能聽到天籟地籟人籟,卻沒有聽到徐先生所謂的絕妙的音樂。所以,他這樣調(diào)侃徐志摩:“我不幸終于難免成為一個(gè)苦韌的非Mystic了,怨誰呢。只能恭頌志摩先生的福氣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而已。”但是,他又筆鋒一轉(zhuǎn),諷刺道:“但倘若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將這位先生‘送進(jìn)瘋?cè)嗽喝?我可要拼命反對,盡力呼冤的——雖然將音樂送進(jìn)音樂里去,從干脆的Mystic看來并不算什么一回事。”最后,魯迅意味深長地反問:“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在那里!?”
不難看出,魯迅顯然不同意徐志摩的神秘主義的文藝觀,而徐志摩對音樂的看法,也讓他不敢茍同,這是兩種不同的文藝觀的交鋒。所以,他就寫了這篇略帶戲謔和諷刺的妙文與徐志摩爭鳴。十年之后,魯迅在《〈集外集〉序》中還提及到此事:“我其實(shí)不喜歡做新詩的……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就果然不來了。”
1925年9月,徐志摩開始主持《晨報(bào)副刊》的編務(wù),改版為《晨報(bào)副鐫》,10月1日出版第一期。但是就是在第一期里,徐志摩又是一篇序跋惹了禍。在這一期發(fā)表的凌叔華的小說《中秋晚》后面,徐志摩隨手寫了幾句跋語,其中一句是:“還有副刊篇首廣告的圖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謝。”這一句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副刊篇首廣告的圖案是由凌叔華畫的。這一筆誤自然給了人口實(shí)。一周后,《京報(bào)副刊》上就刊出了重余(陳學(xué)昭)寫的《似曾相識的〈晨報(bào)副刊〉篇首圖案》,文中指出,偌大的北京城,學(xué)者專家隨處皆是,但是為什么都沒有發(fā)現(xiàn)竊賊呢?作者很想看到有人發(fā)出點(diǎn)聲息,但是使我等得耐煩了。文章末尾,作者只好自己來點(diǎn)明這幅畫是剽竊琵亞詞侶的:
琵亞詞侶是英國人,他現(xiàn)在已變?yōu)槌舾?已變?yōu)槟嗤?總之是不會親自出馬說話的了!但這樣大膽是妥當(dāng)?shù)膯?萬一有彼邦的人士生著如我的性格一樣者,一入目對于這個(gè)“似曾相識”起了追究,若竟作大問題似的思索起來,豈不???我覺得難受!
可是仔細(xì)想想我又何必著急替人家難受?反正人家有這樣的本領(lǐng)做這樣的事,呀喲!真——算了罷!!!
這一指責(zé)針對凌叔華,徐志摩知道事情鬧大了,當(dāng)天便寫信給《京報(bào)副刊》編輯孫伏園,請求將此信刊出,說明事情經(jīng)過,為凌女士辯誣。10月9日,《京報(bào)副刊》刊出了徐的信。信的開頭就交代:“這回《晨報(bào)副刊》篇首的圖案是琵亞詞侶的原稿,我選定了請凌叔華女士摹下來制版的……幸虧我不是存心做賊,一點(diǎn)也不虛心,趕快來聲明吧,”但是,徐又在信中也對質(zhì)疑者表達(dá)了不滿,在他看來,“琵亞詞侶的黑白素繪圖案,就比如我們何子貞、張廉卿的字,是最不可錯(cuò)誤的作品,稍微知道西歐畫事的誰不認(rèn)識誰不愛他?”言外之意即是,你以為別人剽竊,實(shí)際上是你自己孤陋寡聞而已。
自然這幅畫很快就被撤下來了。到10月17日出第九期時(shí),就換上聞一多畫的刊頭。但是,此誤會并沒有完。在1926年年初,魯迅在《不是信》中還提起此事,說陳西瀅以為是他揭發(fā)了凌叔華剽竊琵亞詞侶的畫,才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整節(jié)的抄襲了日本學(xué)者鹽谷溫的書。凌叔華也不甘休,在《關(guān)于〈說有這么一回事〉的信并一點(diǎn)小事》(刊于1926年5月5日《晨報(bào)副刊》)發(fā)泄了自己的不滿:“哪曉得因此卻惹動了好幾位大文豪小文人,順筆附筆的寫上凌○○女士抄襲比斯侶大家,種種笑話,說我個(gè)人事小,占去有用的刊物篇幅事大呀!因此我總覺得那是憾事,后來就請副刊撤去這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