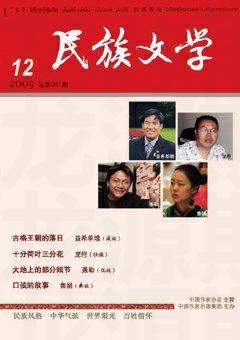我說《滿族文學》
于曉威(滿 族)
作為一家雙月刊的純文學雜志,《滿族文學》出刊二百期了。如果把它們擺放在一起,我就覺得那是一扇扇小窗。
《滿族文學》前身《杜鵑》,一九八六年改刊《滿族文學》,成為國內文學界和少數民族事業一道獨特的風景。啟功題寫刊名,愛新覺羅?溥杰、老舍夫人胡絜青、舒群、端木蕻良、侯寶林、馬加、關山復、關沫南等滿族著名文化界人士題寫賀詞。近三十年來,僅小說這一領域,它不僅發表了國內許多著名的或正在活躍的外省作家作品,如賈平凹、胡昭、水運憲、梁曉聲、雷加、趙大年、阿成、何玉茹、杜光輝、羅偉章、陳然等,同時,遼寧省內許多重要和知名作家的作品也大量在這里刊發,如刁斗、劉元舉、王寧、白天光、孫春平、馬秋芬、邊玲玲、孫惠芬、劉嘉陵、黃世俊、女真、肖士慶、林和平、于德才、王金力、巴音博羅、李鐵、白小易、荒原、解良、周建新、力哥、閻耀明、方明貴、馮偉、李銘、萬勝、梁靜秋、李燕子、張魯鐳等等,其中不乏許多作家的處女作和滿族作家的優秀作品。此外,丹東及外地其他作者和作品更是無以計數,這些作者因文學而分布黨政、文藝、部隊、醫療、工廠、農村、學校等各個社會領域,成為其中的中堅或代表力量,為潛移默化、構建和諧社會、提升社會人文水準和道德力量做出了殊異的貢獻。那些無數的文學作品,更是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直接或間接支持并見證了遼寧乃至全國新時期和新世紀文學的發展。近三十年來,《滿族文學》不僅成為遼東文化群落中的一方重鎮,在文學事業上,也成為遼寧文學大軍中一員驍勇的裨將。在國內少數民族事業上,也成為一面鮮亮的旗幟。
我一直覺得《滿族文學》中的“滿族”和“文學”兩個詞搭配起來很有意思,我不把它看作是一個偏正詞組,即前詞限定后詞,而看作是一個并列詞組或聯合詞組。也就是說,《滿族文學》不僅僅限于發表跟滿族有關的東西,它是既有滿族的東西,又有文學的東西,它的外延由此而擴大。另外,它有一個很好的平臺,即雖然立足丹東,但名義為遼寧省作家協會和丹東市文聯主辦,算是一家準省級刊物,這在全國文學刊物中大約只有兩家(另一家是河北邢臺市《散文百家》,名義為河北省作協主辦);同時,在全世界范圍內,將滿族和文學聯系在一起的文學刊物,《滿族文學》是唯一的一家。它不僅在日本等許多亞洲國家有訂閱,在美國也有訂閱。我記得省內一位女作家出訪德國回來后,曾對我刊已故主編王中和老師說過:“中和,我在德國國家圖書館竟然見到了《滿族文學》!”
是的,我常想,一座城市動輒斥資幾百萬、幾千萬來蓋一座賓館,乃至投入更多資金修建各種樓堂館所,包括打造虛假的仿古景點等等,何如拿出上述資金的一個零頭,來支持一本嚴肅高雅的文學刊物呢?目下來說,再繼續探討所謂一個地區和城市該不該由政府出錢支持一份文學刊物——這種話題已經是過時和落伍的了,現在要探討的已經應該是怎樣把這份刊物支持得更好。固定建筑是要人家來到一座城市才能親自欣賞,而文學刊物卻是真正走出去贏得欣賞,并在人群中手手相傳,乃至被人家的圖書館收藏,以利發揮更大閱讀效力并贏得文化自覺和自尊。在一個不斷重視文化戰略和文化軟實力的國家(包括地區和城市),文化和物質的長久利益高下立現。
《滿族文學》多年來得到了許多滿族同胞和讀者的支持,這中間不乏許多感人的事跡。我們經常在新年和創刊紀念日時,收到許多滿族同胞寄來的手寫的滿語賀卡,它們代表了一份份心意;我們也經常收到許多滿族同胞的并不是投稿的信件,它們代表了一份份叮嚀。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滿族老人西林和璠,因為喜愛《滿族文學》,短期內竟聯系了四十多位滿族同胞訂閱《滿族文學》…… 今年,因為要充實刊物的原顧問陣容,我忐忑地邀請了幾位國內滿族界和文學界有影響的人士,這也是我們一直打算而沒有實施的事情,原因就是擔心請不動人家,用我們刊物主編的話說,我們辦刊和辦公經費實在拮據,一不能給人家發津貼,二也不能我們自己花旅差費一一前去拜訪,真是不好張口啊。沒想到我第一個電話打到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著名作家關仁山先生那里,剛剛說明情況,他就爽快地答應了,并且說了一句:“嗨,這是我們自家的事啊!”讓我感動莫名而又信心倍增。最后,電話打到天津市文聯副主席、著名作家趙玫女士家中,她得知情況,高興而和藹地說了一句:“沒問題!有上述幾位名家在里面,我還值得說什么!”
《滿族文學》真的像一扇窗口,透過這扇窗口,不僅是外界看我們,我們更由此看外界,感受著外界對我們的關愛,感受著滿族同胞對我們的情誼,它們匯成持久的凝聚力,我們聆教和受益其中,理當勤力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