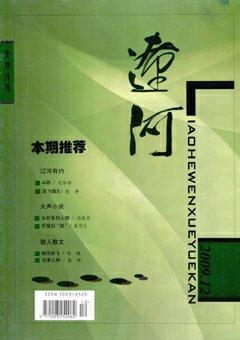藝術與物質之間的抉擇
王仙子
一、唯美主義運動及“為藝術而藝術”
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古典美學和藝術思想傳到法國,繼而在十九世紀中葉由當時在法國學習的英國藝術家惠勒斯和斯溫伯等人帶往英國,并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以英國為中心形成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前后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漫長歷程。它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從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以先拉斐爾學派和權威文藝理論家羅金斯為代表的創作和評論為第一個階段。從80年代到90年代末以斯溫伯恩、佩特、王爾德為代表的美學運動是它的第二個階段。在此期間出現的一大批唯美主義者,如批評家佩特、文學家王爾德、畫家比爾茲利、工藝美術家羅塞蒂等,他們都從藝術、生活各方面、各專長領域標榜唯美的文學創作規律、藝術審美要素、生活起居模式等等。從它所宣稱的口號來看,唯美主義倡導文學自律、藝術無功利性、純形式、純粹審美經驗,以及廣為人知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從所體現的社會生活實踐來看,有關生活藝術化密切相關的室內裝潢、衣著服飾、舉止談吐、花卉園藝等成為反映領域, 并以其優雅精致、奇特時尚、高貴顯耀的生活方式等成為其反映領域。
“為藝術而藝術”是唯美主義的鮮明旗幟。意即藝術是為寫作、繪畫、雕塑、音樂及一切情感表現形式而存在,無功利目的性。這一口號由法國詩人及評論家戈蒂耶創造,但這一觀念,即所覆蓋的文藝思想,如藝術的獨立性,藝術的無功利性,藝術與生活的分離,以及純形式的內容,卻源自德國古典美學,其中康德和席勒的美學思想對其影響深遠,具有濃厚的康德主義和德國浪漫主義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說,‘為藝術而藝術實際上是對康德與席勒美學一種簡略和平俗的表述”。在唯美主義者眼里,藝術成了神圣的情感凈地和世外桃源,“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成為拯救人類的宗教,一個“烏托邦”世界。以此為據,唯美主義者所倡導和推行的藝術審美經驗里,大量存在唯美的藝術情調。大到唯美主義者奉行的藝術理念,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件精致、美輪美奐的物品,都表現出這樣一種藝術的價值取向。
二、審美體驗的轉型
唯美主義強調和推崇“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理念,這一文藝觀念反映在藝術的審美領域里,是藝術的自律獨立性、無功利目的性、純藝術的表現形式等等。其倡導的審美體驗是藝術純潔高尚、形式美和精神自由。然而,我們需要在這里重點強調的是:“那些看起來不在場、邊緣化或模糊不清的東西可能為理解它的意義提供了最關鍵的線索。”因此,縱觀唯美主義運動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們可以發現唯美主義已背離其所宣稱的藝術獨立性,而走向了對藝術品瞬間美的感受、對商品消費藝術感官強烈刺激的“歡欣鼓舞”、對“物化”物質享受的無限崇拜、走向了十九世紀“資本”這一文化邏輯之中,開始以現代性的思維方式體驗生活,感受藝術審美快適感。
《真誠的重要性》是王爾德最出色的喜劇之一。此劇情講述了兩個浪漫的女孩尋找自己心儀的對象的故事。這兩個浪漫的女孩希望找到一個有“真誠”這一高尚品質的男士相依相伴。問題是該如何確定知曉一個男人是否具有“真誠”這一品性呢?她們的想法很出乎常人的想法,那就是一定要嫁給一個名字叫“歐內斯特”(Ernest的中譯名,英語語境中為“真誠”之意,人名與此單詞諧音),因為她們覺得這個名字才安全可靠,可以托付終身。王爾德用這個喜劇意在理解藝術形式才是生活的全部本質,只有在藝術的自由國度里感受瞬間,用全部精力捕捉瞬間,永恒之物才可能真正存在,只有形式大于內容,名稱重于內涵,藝術的救贖功能才會實現,人類才可能在“藝術”這一靈魂棲息地享受生的樂趣。再如王爾德的另一部戲劇《莎樂美》(Salome)則從人的感官視覺聽覺觸覺角度闡述唯美主義審美體驗的方式和目的。劇情說的是希羅底的女兒癡情于施洗者約翰,但是遭到約翰的嚴詞拒絕。求愛受挫后,莎樂美勃然大怒,一氣之下請求父王將約翰殺死。希律王要求她跳了“七重面紗之舞”之后,然后滿足了她瘋狂的愛欲。莎樂美最終一親吻約翰的頭顱而死,此劇也達到了最高潮。《莎樂美》析出的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物欲橫流的情況下人的物質性感受強烈釋放,是對瞬間的執著追求。
事實上,通過對唯美主義文本的審閱,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十九世紀中后期商品經濟向全球各個角落和領域的無限擴張,特別是商業資本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唯美主義的藝術體驗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商品資本的文化邏輯,藝術為了在日趨商業化的市場激烈競爭大舞臺上站穩腳跟,不得不以商品的模式展銷在人們眼前。“物化”的商品經濟意識也深深地烙印在唯美主義者藝術創作之中,由此而推之,唯美主義的審美體驗將帶上商品文化的特征和訊息。尋找強烈的感官刺激,對美的瞬間感受與執著,贊頌短暫的藝術效果,崇拜肉體物欲等都成了他們的最為主要的審美體驗特征。唯美主義先驅佩特認為:“詩的激情、美的渴望、為藝術而熱愛藝術,乃是智慧的極致。因為藝術來到你的面前,除了為你帶來最高品質的瞬間之外,別無其他;而且僅僅是為了這些瞬間。”畫家比爾茲利的畫風具有獨特的創作風格和價值取向,主要以崇尚肉感,曲線美為特征和目標,彌漫著浪漫唯美頹廢的氣息,完全架空了人的靈魂,在他的畫里面,人完全成為物質的單純載體,藝術的神圣禁地被十九世紀的商業文化意識駕馭操控,失去了自我主體性。對物質的強烈欲望和要求,商品物質結構對藝術進行形而下的解構,使藝術審美體驗呈現出“物化”的消費形態,唯美主義的藝術自律和獨立性已經轉入對消費社會下物質體驗。王爾德說過:“每個雄心勃勃的人都以自己所特有的武器與他的時代作戰,這個時代崇拜財富,財富是這個時代的上帝,要成功就必須擁有財富。”[4]這赤裸裸的“商品拜物教”和對財富不擇手段的占有征服說明了資本主義文化體系下一個真理:“資本”、“財富”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商品時代的到來使唯美主義者在審美閾限里無從擺脫物質對官能的誘惑與奴役,更遑論藝術對主體的救贖功能,而只能以感官刺激,“商品拜物教”等形式來融入商品經濟的大時代趨勢和背景,求得藝術自身的生存、發展。唯美主義者由此而產生的藝術審美體驗不斷地徘徊徜徉著,是“為藝術而藝術”?還是“為藝術而生活”?在沒有尋找到二者最佳結合點的時候,他們明顯地走向了后者。在王爾德的一些反映空間審美體驗的作品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他對瞬間美感的強烈感受和執著,在這些心理體驗的過程中,視聽覺物和“物化”審美意象的出現更為具體形象。王爾德的詩歌《印象》(1881年)的詩組中,曾這樣描寫過這樣的畫面:
藍色和金色的泰晤士河夜曲
在灰色中漸漸和諧
裝滿褐色干草的駁船
駛出碼頭,駛向清冷
黃色的霧從橋上向下蔓延
直至房屋的墻角
又變成一片片陰影
而圣保羅教堂
像是泛現于城市上方的水泡
這一幅城市黃昏景象中,充斥著強烈色彩、物質實體的想象幻影的融合,審美體驗由純粹的藝術自律層面進入到官能(主要是視覺、觸覺和聽覺)系統的雜糅交匯,“物質性”成為這組詩歌的關鍵詞
《道林-格雷的畫像》是一部以城市漫游者為主題的小說,可以說這部小說是王爾德對城市審美體驗的最佳闡釋。一天,主人公道林-格雷看過表演,從劇院走出來:
他不知道他走到了哪里。他只記得他穿過昏黃的街道,走過拖著巨大陰影的拱門和面目可怕的房屋。女人們粗魯的說話聲和尖利的笑聲追隨著他。醉鬼們從他的身邊走過,像怪誕的餓猴子一樣自言自語。
他看到相貌奇特的小孩在院門口臺階上擠做一團,聽見從黑洞洞的院子里傳出尖叫聲和咒罵聲。
這里,道林-格雷的審美體驗更趨向于感性化的物質化,完全失卻了藝術上純粹的音樂感和詩歌性,在雜亂無章、尖聲怪語、異形丑狀的夜色中,主體開始了分裂,感覺跟著客觀物質進行持續不間斷的分裂。人在現代城市中的失落感和位置的喪失,是主人公精神頹廢情緒混亂的直接原因,他只能依靠純粹的感官系統來體驗生活的百態。因而王爾德筆下的各種人物的審美實踐活動緊密地與客觀世界的物質相關聯,物與物的關系進入到人與物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王爾德筆下的人物一般在進入到憂郁、焦慮的精神世界后,通過獨有的身心感受,又進入到情感釋放的階段,即對瞬間美的體驗與占有。道林-格雷在考文特花園,他又經歷了一個從焦慮到解脫的過程:
拂曉時分,他發現自己走進了考文特花園。……巨大的馬車載著顫抖的百合花從空曠的街道上出現。空氣中彌漫著濃郁的花香,美麗的花朵好像對他是痛苦的解毒劑。
在這樣一個優美的環境中,人物不再以焦慮、憂郁和苦悶的心態感受世界,他在形象豐富物質充沛的世界里,感覺不再雜碎,主體自我意識不再分裂,自我得以構建,身份得到認同。此時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物質瞬間美麗的世界,得到了物質靈魂就得到了凈化升騰,得到了瞬間精神就獲得了永生。而在這一瞬間審美體驗方式的確立從根本上來說是商業消費物質最大化的集中體現。事實上,主體分裂癥的形成與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以及普及有相當的關系,主體精神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線性時間觀混淆后,將會有更多的精力和意志關注瞬間和當下,能有全景式的思維空間容納物質和實在。道林-格雷由憂郁焦急走向平和,實際上就是在審美體驗的轉化中用主體精神分裂的方式來實現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主體精神開始的混亂通過對當前“百合花”、“馬車”等具體物質的投射得以重整和規范,主體身份最終得到確認、認同。從另外一個維度上說,“百合花”、“馬車”這些物質性的存在,在資本主義“物質”的文化語境以及它的邏輯運演過程中,審美體驗早已沾注定被“物化”的命運。
綜上所述,唯美主義在經歷了商品經濟時代潮流的強烈沖刷下,其審美體驗所呈現于世的特征與它所倡導的是不一致的,二者儼然是一個對立的矛盾體。“為藝術而藝術”的審美體驗終究讓位于強烈感官刺激和瞬間感受,唯美主義運動的審美體驗走進了物質性這一時代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