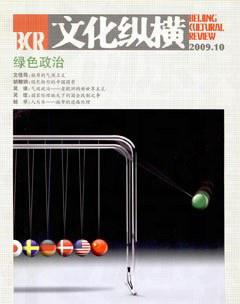全球綠色政治的歷史譜系
劉東國
自1972年第一次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以來,全球環境合作已經走過了37年的歷程。在這一進程中,環境問題從過去的技術問題轉變為政治問題,又從最初的低政治議題轉向高政治議題。隨著2009年12月7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哥本哈根)會議的臨近,綠色政治更是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可以說,人類已經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從過去的工業文明走向了生態文明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以資源和環境保護為特征的綠色經濟和政治已經成了進步和發達程度的尺度和代名詞。
綠色政治的發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一方面是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使然,另一方面與各種力量的推動是分不開的。眾所周知,全球環境政治的發展是國際組織、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普通民眾共同推動的結果。其中最關鍵的是各國政府。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組織是政府間合作平臺,它提出的一切議程最終都要經過各國政府的確認和實施。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各種行為體也是靠影響政府來實現自己的主張。一個國家的政府對環境政治抱什么態度取決于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同時還取決于不同社會力量對執政黨的影響程度。如果說社會主義思想從西歐傳播到世界各國離不開共產黨和社會黨的貢獻的話,那么綠色政治思想能夠成為今天各國政府的共識,也同樣離不開綠黨的推動。
綠黨的主張及其發展
綠黨成為一種政治勢力,并對國家政治議程產生重大影響是發源于西歐的。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歐各國都相繼成立了綠色政黨(盡管名稱有所不同)并參加各級選舉。之后不久,大部分西歐綠黨都獲得足夠的選票進入包括歐洲議會在內的各級議會。到90年代后半期,芬蘭、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德國綠黨相繼與其他左翼政黨合作,組成全國性的紅綠聯合政府而成為執政黨。其中德國綠黨的政治實力最強,1983年,在與德國社民黨聯合組閣時,15名部長職務中綠黨擔任了3名,綠黨領袖約施卡,菲舍爾還擔任了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要職。此外,綠黨還積極參與了歐洲一體化建設,成為歐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近幾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綠黨總體力量一直名列第三,僅次于歐洲人民黨黨團和社會黨與民主黨進步聯盟黨團。在歐盟委員會,也有綠黨成員擔任歐盟委員職務。
西歐各國綠黨取得的政治成就,極大地鼓舞了世界其他地區的綠色政治力量,他們紛紛效法西歐綠黨的做法,成立了本國綠黨并參加選舉。為了加強各個綠黨之間的聯系,形成整體的力量和政策,綠黨效仿社會黨國際的做法,開始進行橫向聯合。1993年成立了歐洲綠黨聯盟。隨后,在美洲、非洲和亞太地區都相繼成立了地區性的綠黨聯盟組織,在此基礎上,2001年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同時成立了全球綠黨協調和全球綠色網絡兩個組織。前者是各國綠黨之間的政策協調性組織。后者的范圍更廣泛一些,既包括各國綠黨,也包括非政黨性質的綠色社會運動團體。目前,全球綠色網絡聯絡著79個正式成員和7個觀察員組織。其中非洲綠色網絡19個成員,美洲綠黨聯盟11個成員,亞太綠色網絡14個成員,歐洲綠黨聯盟35個成員。
綠黨的生命力在于它提出的生態主義哲學觀和一整套綠色政策主張。綠色哲學對以往的人類中心主義哲學進行了批判,突出生態中心。從這哲學觀出發,綠黨提出了自己所要追求的綠色價值,包括生態優先、人權、基層民主和非暴力等內容。其中最能體現綠黨創新的是它的生態優先價值。就是要以生態可承受能力為準繩,重新調整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發展模式,放棄人口和經濟的無限增長,減少人類生存對自然的壓力。
根據這些理想和追求,綠黨制定了自己的各項政策。在經濟上,主張變革經濟理性,根據社會實際需求而不是為賺錢組織生產。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廢止以國民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的指標,代之以更能準確測量生態可持續性和社會平等程度的指標。限制甚至廢除商品廣告;調整經濟結構,淘汰浪費資源和高污染產業,發展清潔節能產業。通過行政、立法、稅收、財政等手段嚴格限制環境污染。征收生態稅,限制化學農藥、轉基因技術和各類催肥劑在農牧業生產中的使用;限制過度的經濟(包括旅游區)開發,保護野生動植物生態環境不被破壞。在社會政策方面,主張減少工時增加就業;修改法律切實保護婦女、移民、同性戀者、妓女等社會弱者的權利。在對外政策上,主張裁軍,廢除核武器,反對戰爭。主張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援助,幫助其盡快脫貧,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和開發。
這些思想和主張是以往傳統政黨所不曾關注的,它體現了時代的最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政治體系中的不足。
綠黨與歐盟政治經濟的綠化
綠黨作為一種政治力量,至今仍然屬于邊緣性政黨。過去曾一度上臺執政的幾個歐洲綠黨目前也處于在野地位。但它對歐洲政治經濟議程的影響卻是深刻而長久的。正是由于綠黨的推動,歐盟國家才成為全球環境政治和環境經濟技術方面的領軍者。
綠黨通過參加各級選舉的競選活動來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這也是個對選民進行綠色思想教育和綠色知識普及的過程。在綠色政治高漲時期,綠黨的一切活動都成為西方媒體的追蹤熱點和關注焦點。經過長期的反復宣傳,綠色思想在歐盟國家選民中已經深深扎下了根,綠色成為一種時尚。綠黨政治的第一個作用點是培育了歐洲的綠色選民。
選民的綠化,使得傳統政黨的選票越來越多地轉向綠黨。這一形勢迫使傳統政黨不得不改變其排斥綠色政治的態度,轉而將綠黨提出的思想主張納入自己的綱領。用當時流行的話說,偷走綠黨的衣裳披在自己身上。
首先進行綠化的是左翼政黨。德國社民黨改革派代表人物拉方丹于1985年出版了《另一種進步》一書,提出要把“生態社會主義”作為社民黨新的奮斗目標。從而引發了黨內“生態優先派”和“增長優先派”之爭。經數年討論,社民黨在1989年12月柏林特別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生態目標優先的新黨綱和紅綠聯盟新戰略。拉方丹隨后當選為社民黨主席和總理候選人。正是依靠這一戰略,社民黨才在1998年德國大選中奪回了丟失16年的政權。在紅綠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中,綠黨倡導的新社會運動議題成為重要內容。英國工黨因提出“第三條道路”理論而聞名于世,并依靠這一理論重新上臺執政。但無論是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還是工黨理論家吉登斯,其思想體系中至少有一半內容都與綠黨提出的主張類似。
歐洲右翼政黨對綠色政治的排斥遠勝于左翼政黨。但面對中右翼選民對環保思想的接受,也不得不作出綱領調整。從1985年開始,英國保守黨理論家沙利文和佩特森等人就紛紛發表文章,闡述環境轉向的必要性,并奉勸撒切爾政府要盡早采取措施應對綠色政治挑戰,因為未來爭奪綠色選票將是決定左右翼勝負的關鍵。在黨內改革派的呼吁下,保守黨政府最終采取了行動,于1988
年成立了由撒切爾首相親自擔任主席的內閣環境委員會,并相繼出臺了《我們共同的遺產》環境綱領和《環境保護條例》等重要政策文件和法律。
德國社民黨和英國保守黨的綠化,只是西歐傳統主流政黨吸收綠色政治思想和主張的一個縮影,在西歐絕大多數國家,傳統主流政黨都經歷了這樣的轉折過程。這是綠黨政治的第二個作用點。
第三個作用點是推動了環境立法和環保制度建設。綠黨進入各國議會和歐洲議會后,提出了大量的環境立法議案,其活動能量遠遠超過了他們占有議席數量的比例。一位歐盟委員會高級官員評論說,“在歐洲議會,我們從綠黨那里聽到的東西最多……在歐洲議會,他們是個小黨團,但卻是一個重要的小黨團。”在上世紀80、90年代,綠黨影響力較大的環境委員會是提出議案最多和立法工作量最大的委員會。綠黨在環境立法方面的超常能量源自于三個方面。一是綠黨成員非常善于利用各種立法程序和游說手段,采用了很多富有創意性的措施來推進環境立法。二是在西歐一些國家傳統左翼和右翼政黨勢力相當,但又都無法構成單獨執政所需多數席位。這樣,與第三大黨的結盟立場就成了決定哪個主流政黨能上臺執政的關鍵。比如在德國和法國,如果沒有綠黨的支持,社民黨和社會黨上臺執政就非常困難。綠黨正是利用這樣的有利地位,迫使聯盟伙伴作出較大的讓步,在執政期間更多地關注綠黨所提出的議題。三是上臺執政的綠黨大都擔任了環境和公共健康安全方面的部長,他們利用掌握國家權力的機會大量推進了環境立法和相關制度建設。
目前歐盟國家制定了世界上最超前的環保戰略,建立了最完善的環保和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和執行監督機構。在這些戰略機制的推動下,歐盟國家的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得到了進一步優化。在國際舞臺上,前德國外交部長菲舍爾所倡導的環境外交成為歐盟國家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切都與綠黨的長期努力分不開的。
全球綠色政治升溫的背后
進入21世紀后,世界面臨著能源短缺、糧食危機和氣候災害加劇的嚴峻挑戰,這些問題對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生存安全構成了威脅。在這一背景下,環境政治再次升溫,世界政治主題和國際秩序格局特征正在圍繞著資源環境問題而進行著重組。
從國際合作層面看,無論是G8、G20峰會,還是APEC這樣的地區一體化機制,甚或是G2(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這樣的雙邊機制,環境問題都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從國內政治層面看,各主要大國目前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一場圍繞著解決能源危機和環境瓶頸而展開的發展模式調整。對資源環境問題的應對被提升到戰略高度,成為大國間爭奪21世紀世界領導權的競賽場。
日本于2002年頒布了《能源政策基本法》,2006年又出臺了《新國家能源戰略》文件。這些政策的總體目標是實現能源結構的多元化、自主化和高效能化,確保日本中長期能源供應安全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歐盟委員會于2008年11月13日出臺了《能源安全和整體行動方案》。在當年12月布魯塞爾歐盟領導人會議上,各國就歐盟能源氣候一攬子計劃達成一致。提出要在2020年之前,實現三個20%的中短期目標: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20%,節能20%,使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從目前的7.4%提高到20%。到2050年,在整個歐盟內實現無碳發電。
美國一向被視為全球環境合作的絆腳石。小布什政府帶頭退出《京都議定書》,給全球氣候變化合作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但隨著奧巴馬上臺執政,美國政府也開始打出環境政治牌。如果說奧巴馬政府執政半年多來有什么新的創意的話,那就是竭力推行“綠色新政”。2009年6月26日,美國眾議院以微弱多數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提出要增加清潔能源投資,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目標和實施方案。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方案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美國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20%的具體目標。
在這場綠色政治的角逐中,中國同樣提出了自己的議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場全面而深刻的經濟發展模式變革。發展思路從過去的“又快又好”轉變為“又好又快”。雖然只是順序的改變,但卻體現出是發展第一還是環保第一的重大戰略轉折。
這場全球性的“綠色革命”唱主角的是各國政府,但綠色政治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其背后仍然與綠黨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國際舞臺上率先挑起綠色競賽的是歐盟國家。而歐盟國家的綠色政治經濟優勢源自于綠黨的長期綠色改良。經過多年的產業和能源結構調整,歐盟國家在環保和節能技術方面形成了相對競爭優勢。這一優勢使得歐盟成了全球環境政治和環境經濟的領頭羊。在世界格局朝著多極化發展的過程中,歐盟一直靠打環境牌來爭奪世界領導權。這一戰略的直接結果就是推動了國際環境合作的不斷升級。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環境合作體系中,歐盟國家始終是最積極的推動者。無論是臭氧層保護合作機制,還是氣候變化合作機制,或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合作機制,歐盟國家都提出了最高的環境治理目標,并相應承擔了最多的國際義務。如果沒有歐盟國家的強烈要求和積極推動,國際環境合作日程將大打折扣。
“綠色代表未來”,這是綠黨最先提出的口號。歐盟國家把這個口號變成了實際行動,掀起了綠色產業競爭。尤其是綠黨上臺執政時期,提出了征收燃油稅,提高汽車能耗標準等一系列立法舉措。這些措施使歐盟國家的汽車產業和能源產業形成了相對競爭優勢,而美國的汽車產業開始衰落。直到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后,美國才開始意識到,他們在環境政治方面所持立場不僅僅只是環境問題,而是一場全面的經濟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競爭。意識到這一點的奧巴馬總統不甘落后,他多次發表演說強調,“哪個國家如果能夠在開發新能源方面領導世界,哪個國家就能領導21世紀的全球經濟。美國能夠成為這樣的國家,美國必須成為這樣的國家。”
全球綠色政治升溫也是各國綠黨和各種環保運動力量從國內推動的結果。全球80多個綠黨和綠色團體通過參加本國的各級選舉活動而將綠色思想主張傳播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即便是在綠黨力量受到異常壓制的美國,總統選舉中也出現了納德爾和辛西亞·麥金妮等綠黨總統候選人。美國前副總統戈爾雖然是民主黨人,但也成為一個非常積極的環境政治推動者。他因拍攝引起全球高度關注的環保電影《難以忽視的真相》以及為推動全球環保事業做出的巨大努力而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一道,共同獲得了2007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在這些綠色力量的推動下,美國已經形成了良好的綠色政治土壤。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其他十多個州,州政府已經率先發起了本州范圍的綠色革命,其標準和進程都高于奧巴馬政府在聯邦層次出臺的政策。
在歐盟,各國綠黨和歐洲綠黨聯盟對重大的環境議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立場主張,并對本國政府、歐盟機構、八國集團峰會以及聯合國等多邊機制進行了大量的游說活動。比如當歐盟委員會提出三個20%目標一攬子政策方案時,歐洲綠黨聯盟對該方案沒能提出減排30%的目標提出了批評,同時還對法德兩國降低汽車排放標準進行了譴責。呼吁“歐盟領導人必須堅定立場,反對那些要使歐盟推卸責任,不去發揮應對氣候變化領導作用的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4次締約方會議期間,全球綠黨聯盟發表聲明,呼吁“工業國家必須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要承諾在1990年的基礎上到2020年國內減排至少30%,到2050年至少減排80%”。這些主張雖然不會被各國政府所直接接受,但它所營造的社會輿論氣氛會對各國政府的政策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綜上所述,目前全球綠色政治的升溫首先是傳統的工業文明走到盡頭的結果,同時也是人類哲學智慧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的產物。但是,從過去把發展與環保對立起來的思維模式轉向將二者統一起來,把環保看作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的思維模式,這一過程的實現不能抹殺綠黨從政治運作角度的積極推動和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當20多年前綠黨提出綠化政治和經濟,綠色不代表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倒退,反而是推動新型發展模式的動力這一口號時,當時的主流政黨尤其是執政黨都把它看作是綠黨一黨之私的狂想和政治欺騙。而如今,這些思想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政治實踐。當我們在新的世紀步入生態文明的門檻時,不應當忽略和忘記綠黨給人類所帶來的思想和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