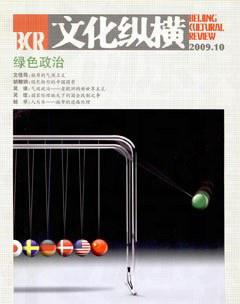經濟學話語淡出公共領域
編者按
1970年代未~1980年代,“文史哲話語”是當時公共討論的主力。對文革的批判,對階級斗爭理論的否定,對未來世界的憧憬,集中運用了文學、哲學和政治學的話語,當時的學界名流多是美學家、哲學家、文藝理論家、文學家等,極少有經濟學家在內。而從1980年代末到整個1990年代,經濟學話語在否定計劃經濟的斗爭中逐漸形成,在捍衛個人利益和權利的斗爭中壯大。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導向下,在整個社會追求財富的大氛圍中逐漸發展,并徹底取代了文革時期和改革初期的“文史哲話語”。學界名流中,經濟學家的人數迅速上升,而哲學家、美學家、政治學家則從社會焦點中漸漸消失。2001年中國入世,更是將經濟學話語推向媒體輿論的頂峰。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概念框架、運思技藝,幾乎成為人們討論公共問題的出發點和終極依據。某種程度上,我們所面臨的是一種情緒、一場運動,是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東西,它深入乃至統治著我們的人心,影響乃至重塑著我們的民情。經濟學的地位和作用已經遠遠不止是一門單純的社會科學。
30年經濟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逐成定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其最初的內涵、作用已大大不同了。中國人日常需求的滿足,已主要倚賴于企業的連續性經營供應。經濟學話語與中國宏觀改革的關系隨之而淡化。另一方面,經濟系統日益增長的復雜性,中國巨型社會變遷所面臨的新問題,都對經濟學主流話語的解釋力構成了嚴重挑戰。盡管金錢觀念深入人心,但資本力量的無情沖擊也讓人頗多痛感。人們發現,物質屢足未必是生活幸福的保證。而市場邏輯自然導向的社會分化,更讓人對經由普遍競爭導向普遍富裕的夢想產生幻滅。且不論,在轉軌語境下四處可見的特權/身份與產權/契約的怪異結合(秋風將其歸結為60年來官方經濟學與商人經濟學的合流)。正是因為這些緣故,經濟學話語遭到頗多詬病,逐漸淡出公共領域。為此,我們組織了此次筆談,邀請體制內外幾名活躍的經濟學研究者對此做出反思。
在筆談中,莫之許分析,主流經濟學淡出公共領域,正是其話語在中國體制內外同時失勢的結果。經濟學話語不再是自明的普遍性知識。改革之初,經濟學家曾帶有“先知”與“布道者”的神秘光環,隨著經濟學卡理斯瑪的日常化,隨著經濟行政日益的官僚化,經濟學“導師”角色的隱退就只是時間的問題。如皖河所說,中國自此進入“后經濟學時代”。經濟學一旦被官僚科層體系內化,經濟學家曾所占有的神圣地位就將無疾而終。而經濟學一旦成為引車販漿者流的行話俚語,也將意味它“不再時髦”(張曉晶語)。更不必說,人們已經學會運用經濟學的武器盡挪榆與嘲弄之能事。
梳理并回顧這個過程,并不是對經濟學展開情緒化的道德清算,而是對中國公共話語空間的重新反省。冷靜評估其歷史得失,我們期待未來中國的公共討論能夠建立在更為健全、理性、坦率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