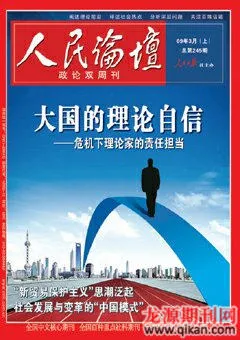“理論霸權”更值得警惕
西方部分人士總是愛玩弄話語霸權,鼓吹或者推銷西方制度或價值觀。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擴大,“華盛頓共識”的破產以及中國的迅速發展,不同的論調開始泛起,甚至出現了“只有中國才能拯救資本主義”的聲音。西方話語霸權的根基在于其“理論霸權”,我們應該拋棄對于西方理論的過分迷信,開創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
西方“理論霸權”具有意識形態特征
資本主義在冷戰后的意識形態攻勢,是以社會科學的學術理論為主導的,希望借此來使帶有強烈政治傾向的宣傳披上科學、客觀和普遍性的外衣。從廣義上來說,大部分社會科學的理論本質上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不管所謂的科學家們對科學研究持有怎樣超脫的態度,他們的理論不可能超越自身所處的歷史時代和階級的限制。這里并沒有否認理論家們在主觀上從全人類普遍的角度上去思考問題的努力,但他們的理論成果,及其對政治、經濟的看法也還是帶有一定傾向性的。更何況學術理論作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根據宣傳的需要被進行“解釋”,從而讓學術理論染上更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
西方話語霸權的理論基礎是從不同角度出發的學術或政論著作。這些著作包括了從政治、哲學到經濟學的廣泛內容,但它們的政治傾向有著明顯的內在一致性,即認為資本主義(自稱為自由民主制度)對于共產主義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某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實行的政治、經濟制度具有普世性,這些模式應該、也必須在全球推廣。
作為政治學概念,意識形態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反映特定階級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相當程度流行性的,對社會、政治做出根本性規定的思想體系和價值體系,其最主要的政治功能是對政權合法性支持和攻擊的功能。意識形態作為意圖指引全社會的思想體系,必然極力證明自身的正確性,同時隱含著否定其他與自身沖突的價值的傾向。意識形態自身的性質,決定了不同的意識形態交鋒成為必然。意識形態之間從來就沒有什么和平共處,面對異類的意識形態,要么融合它、控制它,要么就擊潰它。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之間合作與交往更加密切,然而這不能成為中國放松警惕的理由。樹欲靜而風不止。應該看到,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出于自己戰略和利益的考慮,對中國政治的攻擊就不會停止。東歐劇變后西方社會出現的“三大預言”正是一次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發動的全面而立體的意識形態攻勢,盡管今天看來它的預言已經落空了,但是應當注意到,這樣的意識形態之戰,已經代替了傳統的軍事、政治對立,也已經超越了冷戰期間的意識形態斗爭的范圍和程度,恐怕在未來將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主要形式。
意識形態不是一個可以不爭論的領域,不自己表達自己,就會被別人表達。中國要應對外來意識形態的滲透、沖擊,執政黨要在績效之外尋找更為持久和穩定的合法性依據,中國社會政治需要更深層次的整合,對外需要通過對自身發展模式的總結和闡述提升自己的軟實力,這些都需要加強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來完成,而這些都需要有真正經受實踐檢驗的理論來作支撐。
理論一旦成為強行推銷某種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強權
學者根據自己的學理邏輯,不論得出什么樣的結論,都無可厚非,黑格爾曾經認為君主制最能體現“絕對精神”,因而是最完美的制度,這與啟蒙思想家們所倡導的、今天風光無限的“民權”、“民主”理念大相徑庭,但這并不影響黑格爾作為偉大思想家的地位。事實上,各式各樣的理論之間的爭論,正是為人們現實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種選擇和反思。總體而言,任何看似偏激的理論都符合一定的學理邏輯,本身都有獨特的價值。但是理論一旦成為強行推銷某種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強權。
自冷戰結束后,西方壟斷了理論與政治評判的話語權,他們采用偷梁換柱的辦法,將人們對普世性價值的追求,變成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追求。他們的公式是:普世性價值等于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模式是普世性的模式。不僅如此,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對自身進行重新包裝,把自己與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繁榮等一切美好的東西聯系起來,并把自己的制度標簽改為“自由民主制度”。這樣一來,資本主義不僅把自己的制度本質深深掩藏起來,而且傳統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就儼然變成了“自由民主制度”與“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對立。西方一下子搶占了政治評判和道德評判的制高點,一切不符合西方政治指標的制度都要面臨政治合法性與道德的雙重拷問。
發展中國家長期的貧困與落后,使他們產生了學習其他國家成功發展模式的想法,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不僅動聽,而且有其強大的物質成就作為后盾,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相信,通過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理念,自己的國家也會全面發達起來。發展本來就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況且西方政治的外衣下,包含了太多的內容——民主、自由、繁榮、公正……以至于它自身的框架根本無力承載,因此也就無法兌現這些承諾。我們看到資本主義推銷自己“普世性制度”的業績非常糟糕,發展中國家也逐漸認識到了,探索發展之路是個艱辛的過程,要把示范性的模式與本國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一種從本國歷史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制度模式,往往比嫁接的制度更加有效。
理論很少被另一種理論打倒,卻常常被現實否定。曾幾何時,冷戰的結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今后的世界中,人們終于可以以一種非意識形態的、客觀的思維方式來考慮人類社會共同的、普遍性的發展問題。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模式推銷遭遇困境,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反思“普世性”的內涵。 這從另一個角度也使我們能夠更加客觀地對待這些理論之爭,不盲從所謂的“普世性”論調。它使我們看到,即便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21世紀,人們對于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認識仍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對于如何實現完美的良好社會,仍然沒有一個最終的定論,人類仍然沒有探索出一種標準的社會政治模式,使全世界共同受益。任何斷言這種探索已經有了結果、人類的政治發展已經終結的言論,都失于狂妄。而這些預言者不是過于天真,就是別有用心。(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