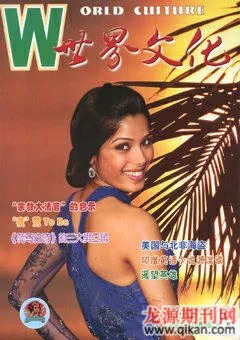遙望英雄
英雄是什么?一千個人有一千個答案。而遙遠的十九世紀卻傳來這樣的聲音:“英雄像北極星一樣,它能透過層層云霧塵埃以及形形色色的激流和火災為人們指導方向”。話音未落,只見一位扛著大旗,目光犀利,精神矍鑠的老人向我們緩緩走來。他就是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文豪,“切爾西的圣哲”,具有英雄主義情結的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
卡萊爾一生著述頗豐,散文、評論、歷史、社會批評均在其寫作之列。而借古諷今,針砭時弊更是他所擅長的。他雖然極其關注現實,但在西方和中國社會卻備受爭議。有人譽之為圣賢將其膜拜,也有人斥之為法西斯先知而冷落他。兩種觀點大相徑庭,觀其本質,卻是卡萊爾式的英雄史觀在背后影響著人們的評價。英語中的Carlylism,指的就是卡萊爾風格,表現為好用談話和不規則的長句,引入新詞和德語詞,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的寫作手法。馬克思曾把卡萊爾的風格與柏克司尼弗式偽君子的風格相比較,認為前者“往往夸張而乏味,但卻往往絢爛綺麗,永遠獨特新穎”。這種獨特的風格使得藏在卡萊爾心中那抹不去的英雄崇拜更為激烈。他認為英雄崇拜中有治理這個世界的永恒希望。“即使人類曾經創造的種種傳統、辦法、信條和社團都消失了,英雄崇拜依然存在,英雄必定要降世。當英雄們來到人間,崇拜英雄就是人們的職責,人們的需要”。諸如此類的描述,在其著作中不勝枚舉。
而1795年出生于蘇格蘭小村子伊克利斐珊的卡萊爾,一開始的人生目標卻不是寫作。有著虔信的加爾文基督教徒做父母,身為長子的卡萊爾從小承載了父母太多的期望。他們辛苦供他讀書,希望他以后能夠做牧師。但事與愿違,在卡萊爾14歲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后,他受到自由開放的文化氛圍的影響,廣泛涉獵數學、文學和懷疑論哲學等方面,逐漸動搖了對基督教的信仰。經過一番痛苦掙扎,他放棄了原本要做牧師的打算。此后為謀生計,他教過書,學過法律。至于寫作,最初也只是一種謀生手段。
1821年,卡萊爾26歲,那時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家境殷實的醫生之女,簡·貝麗·韋爾什小姐。此后兩人鴻雁傳書,終于1826年結成伉儷。婚后由于生活拮據,二人在荒涼的克雷根普托克山莊里隱居6年。隱居的孤寂并沒有挫敗卡萊爾的斗志,反而促使他走上寫作之路。1833年至1834年,卡萊爾在《弗雷澤雜志》上連載發表了第一部奇書《舊衣新裁》。1836年,在愛默生的大力推舉下此書的單行本首發于美國,1838年又在英國出版。此后卡萊爾的名聲才漸漸大了起來。
《舊衣新裁》是卡萊爾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而寫成的。很多時候,從主角德國教授圖非斯德婁克身上都能看到卡萊爾的影子。他曾放棄基督教信仰,做過律師,與上流社會女子相愛。愛慕遭到拒絕后,圖非斯德婁克四處漂泊,尋找真理的存在,最后得出“所有的象征都是合體的衣服;所有靈魂借之傳于感官的形式,外在的也罷,想象而生的也罷,都是衣服”的結論。在此,他不僅批評基督教是過時的舊衣服,也對病態的維多利亞時代提出勸誡。
《舊衣新裁》并沒有給卡萊爾帶來多少經濟收入,但卻為他的文學事業開辟了道路。而1830年,《論歷史》的出版則是他歷史觀的初步表白。卡萊爾認為歷史是無數傳記的提煉。即使有再多的歷史文獻和記錄,也難以對歷史進行全面的描述。因為“歷史是一真實的手稿,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解釋”。但作為歷史學藝術家,卻應該站在更高的角度對歷史進行整體考察。他曾說“作為一個農夫,他對更高的神奇事物的忽視是無可指責的;但是作為一個思想家,自然的重視探索者,他這樣做就不對了”。而一個歷史學家,如果循著各種方向和道路從整體來鳥瞰歷史,那么他會“發現自己并非完全失敗”。
如果說卡萊爾在《論歷史》中還曾強調過普通大眾的創造作用的話,那么從1834年夫妻倆移居倫敦當時文人聚居的切爾西區開始,卡萊爾一步步轉向英雄史觀。3年后,《法國大革命》問世。在這部作品中,卡萊爾把翔實的歷史材料與獨特的寫作文風相結合,攻克巴士底獄、刀尖之宴、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臨刑等章節都寫得字字傳神,句句動情。讀者看到的不再是呆板被動的棋子式人物,而是活生生的、情感復雜、性格鮮明的男男女女。如果說人物刻畫的栩栩如生是卡萊爾對英國文學一大貢獻,那么對偉大人物的塑造,則更是鬼斧神工,畫龍點睛。如他所推崇的米拉波、拉斐特、拿破侖等,他都盡力以渲染筆法去寫,這正是他英雄崇拜思想的體現。例如米拉波,真誠的天性、雄辯的口才、對王室的忠心耿耿和力挽狂瀾都是卡萊爾所推崇的。而米拉波在法國大革命前期所起的中流砒柱的作用是最受其稱道的,以致于米拉伯的逝世,在卡萊爾看來這樣的一個亂世英雄,如果還活著,那么“法國和世界歷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樣了”。
這種英雄崇拜在1840年的演講集《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跡》中更為突出。在此,卡萊爾坦率的指出世界歷史是偉人的歷史。“在我看來,世界的歷史,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已完成的歷史歸根結底是世界上耕耘過的偉人們的歷史。他們是人類的領袖、傳奇式的人物、蕓蕓眾生踵武前賢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說,他們是創世主,我們在這世界上耳聞目睹的這一切實現了的東西,不過是上天派給這個世界的偉人們的外部物質結果、現實的表現和體現。可以公正地說,整個世界歷史的靈魂就是這些偉人的歷史”。演講集中列舉了六類英雄:一、神靈英雄,以奧丁為代表;二、先知英雄,以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為代表;三、詩人英雄,以寫出《神曲》的但丁和“戲劇之王”的莎士比亞為代表;四、教士英雄,以扛著宗教改革大旗的路德和堅持真理的諾克斯為代表;清教;五、文人英雄:約翰遜、盧梭、彭斯;六、君王英雄,以克倫威爾、拿破侖為代表。這些英雄的代表,在卡萊爾看來,存在著必不可少的品行——真誠。“真誠是偉人和他的一切言行的根基。如果不以真誠做首要條件,就不會有米拉波,拿破侖,彭斯和克倫威爾,就沒有能夠有所成就的人”。不管是在塔布克戰役中質問以天氣熱為由要退出的部下,坦率的說“是的,天氣的確熱,但地獄更熱”的穆罕默德,或是不受淫威,把木頭做的圣像丟進水里,說它自己可以游泳的諾克斯,抑或是過度誠摯與神經過敏和軟弱性格并備的思想混亂的盧梭,還是拿破侖立足現實的根本的真誠,卡萊爾都認為是真誠使他們成為英雄。
“最偉大的人是沉默的”,“雄辯是銀,沉默是金”,卡萊爾一次又一次的強調英雄或偉人應該沉默。但盧梭卻不具備沉默的稟賦,因而被卡萊爾認為是“令人遺憾的氣量狹小的英雄”。在卡萊爾看來,“只有那種身負千鈞重擔,卻勝似閑庭信步的人才能稱得上是強者,一個人在說話和行動的事跡尚未成熟時,不能沉住氣的人,就不是健全的人”。不善于在議會中演講卻善于即席禱告的克倫威爾,就是能沉住氣的人。每當有難以解決的問題時,他都要與眾臣禱告,直到有決策產生。他認為克倫威爾的禱告,能穿透人的靈魂,遠遠超過了雄辯。這種在極其困難時期,也不放棄上帝的事業,而兢兢業業尋求方法的人,是上帝的光輝在人間的閃耀。卡萊爾心目中的英雄,就是誠懇的接受上帝的指引,帶領人們走向光明的人。
由奧丁到克倫威爾、拿破侖,有些人認為卡萊爾英雄的眼光從前期下層英雄轉向后期對軍事帝王的獨裁統治的崇拜。從1843年的《過去與現在》(又譯為《文明的憂思》)到1845年的《克倫威爾書信與演講釋義》再到1865年的《普魯士腓特烈二世大帝傳》則將卡萊爾的英雄史觀推向極致。他找遍各種理由為腓特烈二世的殘暴開脫,認為獨裁是唯一可行的興國之道。這些均被視為其對軍事獨裁者的推崇。因此希特勒的精神導師,法西斯主義的先知等稱號接踵而至。他對現代民主、議會制的反對,使得人們逐漸冷落他,疏遠他,就連他的老朋友穆勒也與其漸行漸遠。即使如此,仍要看到,卡萊爾心中所認為的英雄的使命是來拯救世界的。當社會陷入混亂不能自拔時,英雄,只有英雄的降臨才能拯救世界。而克倫威爾,腓特烈二世雖為專制,但仍對現時社會做了改觀。
文學家的好惡分明、灑脫不羈,歷史學家的苛求真實、字字珠璣,兩種鮮明的個性匯聚到一個人身上,必然產生復雜的思想。而卡萊爾則通過自己的著作形象地演繹了兩者的結合。卡萊爾永恒的主題是英雄及英雄崇拜。不管是對文人英雄,還是教士英雄,抑或是帝王英雄,雖然他們表現形式不同,但卻為拯救世界而來。而歷來西方社會對卡萊爾的褒貶,皆起源于此。對于毀譽,梁啟超曾這樣認為:“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后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卡萊爾的是非,交由歷史評判。而作為平凡的我們,沉下心來,讀一讀卡萊爾,掩卷后能撩起對往事的回思,對歷史的追問,已然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