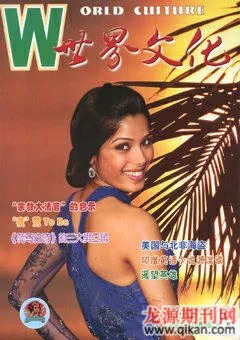“宗教大法官”的啟示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和宗教哲學家布貝爾曾就一百年以后,19世紀的哪位作家仍然是人類思想的領袖這一問題爭論了整整一個通宵。尼采、托爾斯泰、左拉還是雨果?第二天早晨,當太陽從東方升起時,在他們的名單上只剩下兩個人:一個是丹麥哲學家基爾凱郭爾,另一個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茨威格和布貝爾真是慧眼識英雄,天才地預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現代性和世界意義。
果然,20世紀以來,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文學和思想領域內的影響和地位不僅毫無疑問地超過了屠格涅夫、果戈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超越了老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化遺產已經成為了20世紀知識分子應對社會變遷的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1928年,德國批評家Julius Meier-Gradfe在他的專著《陀斯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中寫道:“陀斯妥耶夫斯基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他探索的諸多領域都是為前輩們所不知的……在不久的將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影響力就會像歌德或席勒那樣,甚至已經是如同莎士比亞那樣發生了作用,這不是夸張的假定。只有他這樣一個俄國人才獲得這種全歐性的影響,而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價值中并不是任何一種時髦的大眾化訴求都被容許存在的。”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是什么?這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窮人》是他的成名作,當時頗受俄國“自然派”理論家和作家的歡迎,但并不能代表他的思想和創作的真正風格;《白癡》是在“拷問靈魂”,但它似乎具有過多的理想化的色彩和人為雕琢的痕跡;《罪與罰》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但似乎還有些簡單,不夠豐富;惟有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博大精深,是他的思想和藝術的總結性作品,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他的代表作。而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那個有關“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這個故事充分體現了陀氏思想的偉大、深邃和矛盾,并給后人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思考和啟示。弗洛伊德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宏大的小說,特別是那里面的“大法官”插段敘述是世界文學的頂峰之一。英國小說家勞倫斯在給《大法官》這個片段的英譯本撰寫的序言里,描繪了自己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時的激動不已的心情:頭兩次閱讀因為作品敘述得太真實而被擊倒,第三次閱讀依舊有那種從頭到腳的靈魂的震撼。“白銀時代”的俄羅斯作家和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一書的第八章專門探討了“宗教大法官”關于自由的理論和思想;洛扎諾夫則寫了專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因此,從“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切入陀氏的思想,大概是最直接,也是最令人著迷的。
有關“宗教大法官”的故事見于小說第二部第二卷的第五章,它既是長篇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又可以獨立成篇。舊俄時期的外省地主卡拉馬佐夫有四個兒子:長子德米特里性情暴烈、生活放蕩;次子伊凡上過大學,善于思考,是個無神論者;三子阿遼沙從小在修道院里長大,天性善良、純潔正直、謙恭溫和;四子斯麥爾佳科夫是老卡拉馬佐夫早年奸污瘋女人麗莎后留下的私生子,他是惡的化身,卑微、狠毒,為奪取錢財而敢于為所欲為。最后,斯麥爾佳科夫在伊凡的煽動下終于殺死了父親老卡拉馬佐夫,并嫁禍于德米特里,因為他聽信了伊凡一再宣揚的理論:“既然沒有上帝,則什么都可以做。”伊凡不信上帝,卻主張打著上帝的旗號實行專制主義統治,在專制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全人類的統一。伊凡理論的主要來源就是有關“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由伊凡對他的弟弟阿遼沙講述的。
16世紀,耶穌依據自己的諾言降臨在人類最痛苦的地方——宗教大法官統治下的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塞爾維地方,在宗教裁判制度最可怕的時代,各地每天燒起火堆,頌禱上帝,在美麗奪目的火堆上,燒死兇惡的邪教徒。”耶酥來到這里治病救人、祝福人類。“人們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擁到他的面前,圍住他,聚集在他身邊,跟隨著他走。”宗教大法官認出了他,并逮捕了他,對他說,他已沒有權利下凡來干擾教會的事,因為耶穌已經將“系繩與解繩”的權利交給了教會。他對耶穌說,“到了明天,我將裁判你,把你當作一個最兇惡的邪教徒放在火堆上燒死,而今天吻你的腳的那些人,明天就會在我一揮手之下,爭先恐后跑到你的火堆前面添柴,這你知道嗎?”(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耿濟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上冊第154頁。)
耶穌沒有答話,于是大法官陳述了他的三條理由:一、當魔鬼引誘耶穌把石頭變成面包時,他拒絕了。這便是那個古老的“面包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在大法官看來,在人們面臨餓死的絕境下,應該先給食物,再問道德;而耶穌則認為,道德在先,食物在后,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況且道德也只有在食物匱乏的情況下才能體現出來。二、當魔鬼引誘耶穌從廟宇尖頂上跳下來時,他拒絕了,因此,他喪失了統治人類的三大要素:奇跡、神秘和權威。只要耶穌從尖頂上跳下了,就創造了奇跡,同時也產生了神秘,因而也就必定具有了權威。大法官認為,人們與其說是相信上帝,不如說是相信奇跡,沒有奇跡,上帝的存在也就是可疑的。三、耶穌只挑選了幾個強有力的“選民”跟他走,而將大部分的人留在了罪惡之國。大法官說,現在,所有這些耶穌沒有做到的,教會都做到了,它替耶穌統一了世界,拯救了人類。它替耶穌統治著他拒絕統治的地上王國。
耶穌仍然沒有說話。于是,大法官又開始談及“自由”。他說,耶穌太尊重人類了,反而少愛了人類。他把“靈欲抉擇”的自由交給了人類,無異于把人類無法負擔的重荷壓在人類身上,所以這“自由”是“殘酷的自由”。人類生來就比耶酥想象的要軟弱和低賤,根本就不配享有自由,甚至根本就不能理解自由,更不能在現實中合理地自由選擇。因此,面對自由,軟弱者是免不了要犯罪的,而他們是值得同情的。教會代表上帝懲罰他們,是替上帝受過,犧牲小我而完成大我。而軟弱者卻因為受到懲罰,良心得以凈化,可以升天堂了。因此宗教大法官是愛他們的。又因為“自由與平等”不能并存,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是平等的,而徹底地平等必然會限制他人的自由,所以,為了使人類獲得真正的自由,教會便借上帝之名,收回人類的自由。人類由此獲得了真正的自由,教會卻將一切罪名承擔下來。人們因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死去,反倒沒有了痛苦。再zhleKM/dFk04OKlaT2lExQ==者,人類愛好自由,卻又不愿負責。這樣,奴隸將自由交給了主人后,沒有了負擔,因此自由了;主人因接過了奴隸托付的自由,負擔加重了,反倒失去了自由。所以,奴隸比主人自由。宗教大法官就是這樣做的,他“承受了羅馬和愷撒的寶劍”,成為“地上的王,唯一的王”。
陀斯妥耶夫斯基認為,只要有自由,就必然會有罪惡。亞當之所以選擇了犯罪,乃是因為他是自由的。然而,依據其可能引來的罪惡而拒絕自由,只能使罪惡變本加厲。自由是一種考驗,它既導向苦難,又導向解放,它是悲劇性苦難的基本條件。這便是人類自身品格深處的隱秘。罪惡是每一個人能夠發現他自己或者上帝之前所必須走過的悲劇性的必由之路。人類正是通過罪惡而自覺自愿地取消自由,最終皈依上帝。
面對宗教大法官的長篇大論,耶穌一直沉默著。故事的結尾,耶穌忽然一言不發地走到大法官身邊,默默地吻了他那沒有血色的嘴唇。大法官打了個哆嗦,他打開門說,“你去吧,永遠不要再來。”
這個故事顯然是針對天主教教會的:羅馬教會已經完全違背了基督教教義,墮落成了專制制度的信奉者和執行者。同時,這個故事也是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揭露和批判:東方專制主義剝奪人的自由,實行殘酷的政教合一。在這個故事中,也可以說,宗教大法官象征人類的理性及其實踐,它追求的是現世的功利目標;耶酥則象征著人類的良知,而良知是非功利的,良知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糾正理性的偏差和極端。宗教大法官與耶酥的矛盾對立也就是人類社會和人的內心的矛盾對立的反映。當然,這個故事更為重要的是充分地表現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的矛盾:上帝既有如此多的惡,所以他不存在;沒有上帝,便一切都可以妄為,比如欺騙、虛偽、弒父等等,因此不能沒有上帝。上帝如果存在,那么他在做什么?他究竟有多大作用?陀氏痛恨魔鬼,但痛恨中帶有一些親切感;他愛慕上帝,但愛慕中帶有一些生疏感。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輩子都在證明上帝的存在,但他到末了也未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而恰恰正是這一點,反倒證明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偉大與不朽。
如果我們將19世紀俄國著名的三位小說家拿來作一番比較,我們或許可以勾勒出這樣一幅簡略的圖畫:托爾斯泰總是對我們帶著冰冷的同情,他要求我們品格高貴,要求我們在這里犧牲一點,以便將來在那里少受一些苦;契訶夫則經常以哀憐的眼光望著我們問,“噢,朋友,你為什么如此生活呢?”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則深知人之所以如此生活,乃是因為他們如此思想,同時深知除非他們陷入窮途末路,否則,他們不會改變思想。因此,他狠辣辣地問道:“你知道你是誰嗎?”的確,這是一個令人們的靈魂不得安寧的問題,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不喜愛他,甚至恨他,但又不得不尊敬他、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