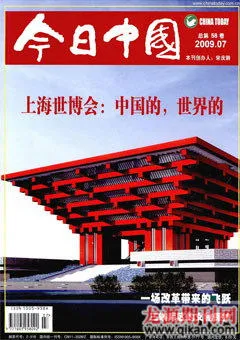借物抒情的花鳥畫
1994年春天,一幅巨大的中國畫掛上中南海接見大廳的一側墻壁。從遠處看,這幅畫上閃爍著類似法國印象派作品的斑斕色彩,走近看卻是地道的中國式筆墨巧妙地塑造出的一草一木,整個畫面上郁郁蔥蔥花團錦簇,像一個慶典活動上著意擺放的花壇,又見一泓清泉在花叢與山石間跳躍,仿佛叮咚之聲不絕于耳。
這幅畫名字叫《春光圖》,出自當代花鳥畫家郭怡蹤之手。他繼承了花鳥畫善于表現精神的傳統,但是又不滿足于只表現畫家個人情感的小天地,經半個世紀的執著追尋,他創造出一種適應當代人欣賞的新花鳥畫。
在中國,從7世紀開始就有以植物和動物為主要題材的繪畫形式,經過幾百年演變,到10世紀形成了以黃荃和徐熙為代表的花鳥畫的兩種主要風格。黃荃的畫法更像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的古典油畫技法,而徐熙更像印象派的直接畫法,或者英國的水彩速寫的方法。后人把黃荃與徐熙兩種不同的畫風概括為“黃家富貴,徐熙野逸”。花鳥畫從此歷經千年,很多朝代都建立國家畫院,畫家們都享受著高官厚祿,有的皇帝也親自參與創作,留下了大量精美之作。
新時代的嘗試
1955年秋的一個下午,位于杭州的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曾經召開過一次全體員工大會。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要取消花鳥畫課程。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一個階段內,政府更加強調藝術的社會教育功能,當時最常見的繪畫作品就是在建筑工地畫在磚墻上的壁畫,內容也多是和現實一樣的勞動場面,宣傳勞動模范、戰斗英雄。講求“風花雪月”的花鳥畫沒了用場。“中國畫當中除了人物畫能夠表現重大題材可以保留,其余都應拋棄。”主張取消花鳥畫的人認為,“花鳥畫是古代文人把玩和自娛自樂的小畫科,不能表現現實生活,不能激勵人民的勞動熱情,而且形式單薄孱弱,根本無法跟畫幅大、表現力強的油畫相比,因此應趁早把它從美術學院的課程中剔除出去。”
時任浙江美術學院院長的花鳥畫家潘天壽大聲疾呼,不能把國粹輕而易舉地丟棄。他認為,花鳥畫是可以表現現實題材的,也可以畫大幅作品,可以用它特有的方式來為現實服務。
潘天壽不但從理論上作出了回應,在實踐上也做出了成功的嘗試。潘天壽年輕時期在傳統花鳥畫上下過很深的功夫,除了具備文人畫的全面修養之外還受過一些西洋畫的訓練。他不同意中西結合的理論,認為“所謂中西結合,就是用西畫的標準來改變中國畫”。他強調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在中西繪畫的比較中,他認識到借物抒情的寫意性是中國畫的長處。
潘天壽很喜歡用巨大的石頭占滿整個畫面,再表現細小的花草從巨石縫中頑強的生長,各種山花野草參差錯落,蓬蓬勃勃,隱喻著生命的力量不可阻擋。他也常在兩塊巨石之間畫上一只青蛙,表現它從一塊小石頭上奮力向大石頭攀爬,動作生動之極,既有氣勢又有情趣。
潘天壽善于畫雄鷹,他創作過很多這樣的作品,雄鷹站在懸崖上雄視遠方,表現志向高遠的寓意。他創作的《記寫雁蕩山花》系列作品1962年在北京一經展出就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當時中央美術學院的花鳥畫教研室主任、著名花鳥畫家郭味蕖激動不已,親自撰寫兩篇論文稱贊潘天壽花鳥畫創新的成功,認為他的花鳥畫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表現的意境不再是古代文人的孤獨苦悶,而是鼓舞人們奮發向上。
郭味蕖之所以如此興奮,是因為他在孤寂的奮斗中找到了同道。為了挽救花鳥畫的命運,他做出了畢生的努力。他經常帶領美術學院的學生下鄉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參加勞動,和農民交朋友,對于老百姓的審美需求十分了解。郭味蕖創作了很多表現勞動工具和農業產品的花鳥畫,借此來贊美勞動、歌頌豐收。在技法上郭味蕖是很富有創新意識的,他主張各個畫種之間應該互相學習,不要涇渭分明。他運用山水畫與花鳥畫結合、寫意畫與工筆畫結合、潑墨畫與重彩畫結合的方法,創作了一批很富有時代氣息的花鳥畫精品,這些作品使花鳥畫的古典形態與現代形態之間結合得十分融洽。
大花鳥精神
在潘天壽、郭味蕖等人的努力下,花鳥畫在當代中國得以繼續發展。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腳步逐漸加快,國家的文藝政策也作了重大的調整,郭怡棕就幸運地在這個時期步入花鳥畫創作的前沿。郭怡蹤認為,花鳥畫也應該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由于傳統花鳥畫產生于慢節奏的農業社會,人們的審美習慣于慢條斯理的品味。而現在生活節奏加快,人們沒有更多的閑暇去慢慢感受一根根線條的魅力,人們需要的是瞬間的視覺沖擊,需要關注社會的變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對傳統花鳥,進行了多方面改革。
他首先從色彩開始。中國傳統崇尚節儉,認為過于鮮艷豐富的色彩會使人眼花繚亂、滋生欲望,從而難于守住清貧。正因為如此,傳統花鳥畫以黑白水墨為主的傳統到潘天壽時期也沒有太大的改變。郭怡掠開始大膽借鑒莫奈明亮豐富的色彩,又長期深入研究他的家鄉山東民間年畫單純樸實的用色習慣。此外,敦煌的佛教壁畫用色也是他直接學習的范本。他認識到,無論是民間年畫還是佛教壁畫都是古代文人鄙視的低俗藝術,但這些藝術卻是普通市民最喜愛的。
色彩的改革使花鳥畫如虎添翼,更加具有時代感。另外,他希望花鳥畫在表現重大題材時,畫幅要大,題材要寬。花鳥畫不僅僅只畫花、畫鳥,天上的禽鳥、水中的魚蝦,大到山石、大樹、獅子、老虎,小到蒿草、苔蘚、蟋蟀、蚊蠅,也就是說除了以人本身,花鳥畫可以表現任何題材。
古代的花鳥畫家借助植物、動物的生活特性比喻個人的情懷。在中國文化中很多動植物都有其擬人化的寓意,竹子因挺拔修長受到文人的喜愛,竹竿的空心也被文人視為“虛心”(謙虛)的象征;梅花開在冬天,不畏嚴寒依然綻放,因此被用來比喻文人不畏強權、潔身自愛的品格;菊花則由于不與眾花在春夏爭艷,與文人不爭名奪利、默默奉獻的精神完全符合;而蘭花生長在深山峽谷,不畏風雨,清雅幽香,質樸無華,被中國文人喻為孤傲、超凡脫俗。無疑,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瑰寶,但郭怡碂也主張,總在古人創造的模式內徘徊,并不利于花鳥畫的發展與創新。他說:“花鳥畫雖小,但是對它的寄托要大。畫家不要滿足于植物標本似的描摹花草,要發揚傳統文化的長處,也要關注社會的變遷,關注人類的生存環境,我們要有大花鳥意識。”
1997年香港回歸,郭怡棕創作了一幅題為《日照香江——為香港回歸而作》的巨幅作品,畫面上層層疊疊的紫荊花是香港的市花,他用香港人熟悉的題材贏得了他們的贊許。作為一個花鳥畫家,他熱愛大自然,關注生態問題,他創作了一幅以沙漠植物仙人掌花為題材的作品《赤道驕陽——我的內羅畢宣言》,以此表達畫家對環境保護、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