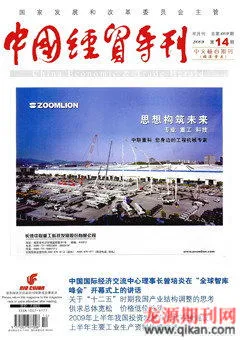試論銀行對票據簽名的審查義務
一、兩大法系立法例的考察
(一)日內瓦法系——形式審查主義
1、票據背書簽名的形式審查主義
因為票據為無因證券、文義證券,臺灣《票據法》第37條規定“執票人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不需要提出其它證據證明其為實質權利人,因而“付款人應負責查核背書之連續,但對背書人之簽名,不負認定之責”。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臺灣票據只要求審查背書形式上是否連續,而對背書簽名是否真實不做審查,所以應為形式審查主義,但到期日前付款除外。
2、票據出票簽名的實質審查主義
日內瓦法系多數國家立法中規定,因為偽造的簽名對被偽造人不生效力,付款人對出票系偽造的票據付款以后不得借記入被偽造人賬戶,而要自負其責任,因此銀行對出票簽名須負是否真實的認定責任,是為實質審查主義。
(二)英美法系——實質審查主義
根據英國《1882年匯票法》24條的規定,“如果某一匯票上的簽名是偽造的,則該簽名無效,任何人(包括善意行為人)均不能據其取得票據上權利”,那么不僅在出票偽造的情況下,銀行錯誤付款后不能借記人被偽造人賬戶;即使善意從偽造背書者手中取得票據的被背書人也不能取得票據權利,銀行對其善意付款不能解除付款責任,須向真正權利人再次付款。
日內瓦法系、英美法系之所以存在這種差異,是因為從本質上來說是由于對善意取得規定的不同。日內瓦法系廣泛承認了動產善意取得,以保護交易安全,英美法系卻不同,“美國財產法以最大限度地保護所有人為原則。
二、對我國《票據法》及《規定》六十九條的評述
(一)《規定》的解釋有違法律文義
《票據法》中規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惡意或者有重大過失付款時,應當自行承擔責任”。按照法律上特殊意義解釋,“所謂惡意,系指明知”,“所謂重大過失,系指付款人若為通常之調查,即可知悉執票人無受領之權限,竟不為通常調查,因而不知其為無受領權限,而對之徑行付款”。從文義解釋來看,票據法采取了形式審查主義。而《規定》認為只要付款人未識別出偽造、變造即屬“重大過失”,只要出現這種結果,付款人就沒有任何免責的理由顯然是不符合法律文義的。
(二)《規定》與票據善意取得制度相抵觸
《票據法》第12條“以欺詐、偷盜或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也不享有票據權利”,也就是說《票據法》廣泛承認了票據善意取得。在《票據法》寬泛的承認善意取得的情況下,而《規定》課以付款人實質審查義務,就會出現下列不協調:如果出票人A以B為受款人簽發一張匯票,D偽造B的簽名背書轉讓給c的時候,一方面,銀行要進行實質審查,假如審查出簽名系屬偽造而拒付;另一方面,即使銀行拒付,c仍可向A追索,B的權利仍未得到保護,銀行實質審查付出的成本對真正權利人沒有任何意義。況且在持票人c向出票人A追索時,A除了要支付票據金額外,還要承擔金額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償日止的利息和取得有關拒絕證明和發出通知書的費用,那么他多支出的費用,應由何人承擔?只有善意取得在例外的情況下成立,那么上例中c不能根據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票據權利,銀行如果審查出簽名系屬偽造拒絕付款,c不能向A追索,B有權要求銀行付款,如果銀行未能審查出簽名系屬偽造而向c付款,仍然不能解除對B的付款義務,通過賦以銀行實質審查義務,真正權利人B才得以保護。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在例外情況下適用的時候,實質審查才會顯示對保護真正權利人的意義。而善意取得在我國票據法中是被廣泛采用的,在此前提下,規定銀行的實質審查義務沒有現實意義,只能導致立法上的矛盾。
(三)《規定》陷銀行于兩難境地
《規定》賦予銀行實質審查義務使銀行在辦理業務過程中處于兩難的尷尬境地。銀行負有如此嚴苛的責任。當然要認真審核。隨著偽造技術的提高,審查難度越來越大:銀行向背書人查詢,如背書人為銀行,按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必須當日回復;而對方不是銀行,一是聯系困難,二是對方不及時回復怎么辦?一張票據可能已背書十幾手,背書人在付款人處又未留印簽,憑什么予以審查?另一方面《票據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出票人在付款人處的存款足以支付支票金額時,付款人應當在當日足額付款”,第一百零五條規定“票據的付款人故意壓票,拖延支付,給持票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銀行要么冒著巨大的風險而當日兌付,要么負遲延賠償責任,陷于兩難境地,長此以往,銀行開展票據業務將面臨很大的困難。
三、我國票據法的完善建議
我國《票據法》本來是以日內瓦法系為藍本,后引進英美制度但未能很好的消化、融合以致引起疑義,形成法律條文間的矛盾。而《規定》不僅未能消除這一漏洞,反而使矛盾加劇。我們不反對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的司法解釋,“但良善之法官造法,至少必須符合兩個要件:①實踐一項實體之法律原則②所創造之規則必須與既存之法律秩序融為一體,契合無間,以維護法律秩序價值判斷的統一性”。《規定》和這一要求背道而馳,我們建議盡快修改,回到對背書形式審查的軌道上來。
從立法論上,我們認為日內瓦法系立法確有不妥不處:對出票偽造的票據,銀行識別出即不承兌或付款,最終由受款人承擔風險,如未識別出予以承兌或付款,由銀行承擔風險,風險負擔決定于不確定的事實,確非合理。受款人從偽造人處接受偽造的票據之時,損害已經發生,損害應停留在原地,沒有特別的理由不能轉嫁給別人,我們認為出票偽造的票據的受款人,已獲付款或承兌時,銀行可以撤銷承兌、索回票款;當受款人將已獲背書的票據背書轉讓給善意被背書人,為了保護被背書人的信賴,銀行不得主張撤銷背書,付款后直接向接受偽造票據的被背書人或其后手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