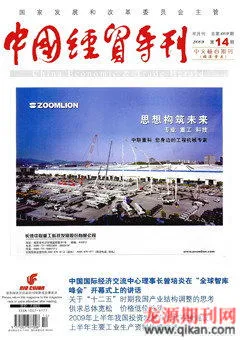論社區治理中公民參與深度
社區治理中公民參與深度是指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層次(包括參參與議題、參與決策、參與執行、參與監督、參與反饋等環節),以及參與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力、有效性和持續性。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趨勢已不可阻擋,其參與的途徑正在不斷擴展,社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應該不斷創新。
一、社區公民參與深度的內涵
社區公民參與的廣度由參與的人數和范圍來確定,即參與的普遍性。一個社區內少數人完全而有效的參與,不能構成民主。廣度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更要關注參與時是否充分、有效,即參與深度。在轉型社會中,要更新社區參與理念,將衡量社區參與水平的標準由居民參與的廣度調整到參與的深度。科恩強調:所謂參與的廣度是指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普遍性,而參與的深度則是指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有效性。美國學者亨廷頓和納爾遜認為參與廣度即指從事參與的人的比例,即有多少人參與,又有多少人置身于其外;深度即該種參與活動影響整個決策系統的程度和持續性,以及它對決策系統的重要性。因此說,社區治理中公民參與的深度是指公眾參與的層次,包括參與議題、參與決策、參與執行、參與監督、參與反饋等環節,以及參與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力、有效性和持續性。
公民參與的廣度,是衡量公民參與量的緯度;參與的深度則是衡量公民參與質的緯度。二者是矛盾統一體。社區公民參與的深度和廣度在整體上呈現負相關的矛盾關系,參與的范圍越大、人數越多,參與者感覺到的有效性反而越低;要想社區公民參與達到一定的深度,在參與廣度上又難以鋪開,參與規模受到局限。
二、影響社區公民參與深度的因素
首先,社區性質決定了社區公民參與的深度。不同的社區治理模式社區性質不同。社區治理模式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行政型社區。以行政型社會資本為主,公民參與受到行政方面的嚴格限制,參與意識和參與行為嚴重缺乏。第二類共治型社區和第三類自治型社區。參與型社會資本豐富,公民參與意識強烈,參與行為積極,參與條件成熟,參與能力較強。自治型社區徹底撇清了行政力量的介入,憑借公民自治力量承擔起社區的一切公共事務。第四類自然型社區。居民往往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無心社區的公共事務,這類社區的公民參與水平非常低。
其次,托馬斯認為社區公共政策屬性對于公民參與深度具有決定性意義。公共政策屬性包括公民參與的公共政策的性質及執行目標、政策本身涉及的公共問題的性質及解決方案。公民參與的深度取決于公共政策本身的一些性質和內在要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本質或性質約束,如技術性約束、安全性約束、規制性約束、預算約束等,它們影響著公民進入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可能性,決定著公民參與面對的各種規制與限制。公民參與的深度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專業性程度、技術含量、保密程度、規制限制程度成反比,與預算成正比。二是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接受度和認同度越高,與政策利益關系越緊密,則參與熱情越高,參與方式越積極,參與深度就越高;反之則參與程度較低。
第三,居民的參與素養是影響社區公民參與深度的關鍵因素。現代社區公民以關心社區事務、參與社區建設、承擔社區責任為基本標志,沒有現代社區公民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參與,更不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善治。社區公民影響其公共參與的主要素質有:一是參與意識。應培養積極主動地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意識,應該將參與作為公民身份和公民資格的必然要義。二是參與熱情。公民沒有付諸實踐的熱情、興趣,積極性不高,能動性不強,也不能產生深度的參與行為。三是參與能力。公民參與的能力主要是指參與的方法和技巧,其中包括討論和溝通、對話和協商、妥協和達成共識等參與手段的掌握和運用。有參與意識和參與熱情,而沒有參與能力,最終不能付諸實際,參與也只能成為空談。
三、社區公民參與的適度深度
公民參與的深度是衡量社區民主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現實中,公民參與深度存在兩種極端:一種是參與不足。公民由于參與公共事務不深,對公共決策缺乏了解,引發對社區治理的懷疑、冷淡甚至逆反心理。這樣的情緒一旦持續增長,會造成社區成員參與水平的進一步下降,最終將危及到社區民主的存在和發展。再有一種是社區局部參與深度不足,如社區公民參與主體中一個或數個重要團體受到的重視不夠,對公共決策參與的加入不多,而且這類團體對相關決策問題擁有動員能力,公民參與就可能面臨失敗的風險。另一種極端是參與過度。過度參與一般表現為社區公民對于公共事務的關注過高,熱情過盛,對于決策過程的介入過于深入、專斷,參與活動缺乏有效的組織和協調。其結果是公民自我主義膨脹或民主的失控,引發社區的不穩定甚至治理混亂,導致公共資源不必要的浪費和決策過程復雜化。
在現代化社區治理中,提倡適度和均衡的公民參與深度,它是激進參與和消極參與之間的一個平衡。通常認為,界定公民參與的適宜度主要取決于最終決策中政策質量要求和政策可接受性要求之間的相互限制。對政策質量期望越高的公共問題,對公民參與的需求程度就越小。對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問題,對吸納公民參與的需求程度和分享決策權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適度的參與深度就是在政策的質量追求和可接受性追求之間尋求平衡點。也有學者認為,公民參與的目的在于實現民主的理想,但是公民參與往往花費較多的成本與時間,影響問題處理的時效,有可能違背行政所要求的效率目標,因此適度參與實際上是尋求公共治理的民主與效率之間的平衡點。還有學者認為影響公民參與的因素應追究到公民在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公民既是社區治理的參與者,也是社區治理的服從者,適度參與就是幫助公民在這兩種身份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綜合以上三種的提法,我們為適度參與深度界定了以下三個標準:一是公共利益。任何公共政策不論它的質量要求和可接受性要求是多高,均應以公共利益為最后的目標。二是平等合作。在社區的公共議題面前,專家和公民是平等的地位,兩者之前的合作是克服公眾的專業局限,同時避免“專家獨斷”局面的最佳選擇。三是獨立自主。社區公民一方面需要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決策和實施,來發表自己的心聲,爭取傾向于自身的決策,滿足個人愿望;另一方面他們又是社區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公共決策的服從者和執行者。公民在兩種角色中的尺度和立場對社區治理是一個重要的支持。如果每個公民在社區治理上都高度積極或者都高度消極服從,很難維持治理系統的平衡。因此,公民參與必須要以公民個人自主和獨立性為基礎,這是保持公民參與適度、社區治理系統均衡的關鍵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