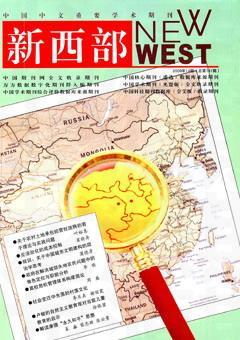論王曉鷹的導演藝術
顧秀麗
[摘 要] 王曉鷹的導演藝術特色主要體現在采用“假定性”舞臺上的敘述方式,但又超越了“假定性”舞臺的時空結構。在對新的舞臺敘述方法探索、創造出詩化的演出時空的同時,也在審美的層面上對“詩化情感和人生哲理”進行直接、深刻、強烈的表達,使戲劇的整體表現達到一種詩化的意境。
[關鍵詞] 王曉鷹;導演藝術;二度創作
導演的根本任務是排戲,就是“使劇本由抽象的、隱而不見的狀態中轉換為舞臺上具體的實際的生命”,也就是“把各種不同藝術有機地融合為一種形象”,從而把活生生的作為一種綜合藝術的戲劇呈現在觀眾的面前。戲劇導演的舞臺二度創作有自己的敘述方式,我國長期以來受到蘇聯導演學派的影響,曾經形成唯“幻覺性”再現型導演藝術獨尊的狀況,直到20世紀80年代實驗戲劇的異軍突起打破了“幻覺”藝術一統天下的局面。經過導演藝術家們20余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索,我國的戲劇導演藝術終于形成了風格多樣、形式豐富、審美多元的態勢。王曉鷹是眾多為戲劇藝術不斷創新作出卓越貢獻的導演中杰出的一位,他不僅是具有較高理論素養的學者,而且是一個具有頗多作品的舞臺實踐家,他一貫執著于探索新的舞臺敘述方式,他的戲既好看好懂極具觀賞性又耐人尋味余味無窮,既大膽運用西方新銳的舞臺表現手法又符合中國人的欣賞習慣,既堅持“舞臺假定性”又超越“舞臺假定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導演風格。
一、講述故事:“假定性”舞臺上的敘述方式
在王曉鷹的舞臺敘述方法中,盡管他運用手法很新穎,舞臺語匯很別致,但他從不 拒絕向觀眾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些故事中往往有復雜的人物關系,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戲劇沖突,有明確的思想內容和清晰的敘述脈絡,無論是90年代的《愛情泡泡》、《春秋魂》、《浴血美人》、新版《雷雨》,還是2000以后的《薩勒姆女巫》、《哥本哈根》、越劇《趙氏孤兒》,都講述了一個情節不斷推進、沖突不斷激化的完整故事,具有“講故事”的敘事風格。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探索戲劇和實驗戲劇,有的導演學習西方現代派戲劇的手法,將這些手法生硬的運用于自己的戲劇創作之中,一味追求粘貼、拼湊的碎片式的敘述方式,或把中外的故事剪輯拼貼、用游戲化的手法進行敘事(如孟京輝《思凡?雙下山》《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或直接把磚頭、豬肉、甚至農民工搬上舞臺(如牟森《零檔案》《與艾滋有關》),盡管這些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一大批青年觀眾,特別是在校大學生,但他們的種種創造也只不過是對戲劇的敘事在淺表層面上的實驗,他們對當代戲劇最大的貢獻是打破一元格局而不是創造中西合璧的真正的本民族戲劇文化。較之于80年代的探索戲劇和實驗戲劇,王曉鷹這種“講故事”的敘事方式承繼了古老的中國民族戲劇傳統,更符合中國老百姓的觀劇習慣,更切合中國觀眾的欣賞品味,這使得他的戲好看易懂,任何文化層次的觀眾都能夠接受。同時,這種探索也并不降低他的導演藝術水準,反而使他的舞臺作品贏得了更廣闊的文化消費市場和更強的生命力。
二、表現與再現:超越“假定性”舞臺的時空結構
上世紀80年代話劇革新運動以來,眾多的導演對“舞臺假定性”這一戲劇本性表示出熱切的關注,但許多導演在運用“假定性手法”進行二度創作方面還停留在較為表面的層次上,他們往往只把“舞臺假定性”作為一種更自由更靈活地展現多種多樣的戲劇外部環境時空的導演手段,對“假定性”的潛在作用沒有充分認識。王曉鷹在自己的導演實踐中不斷探索著作為導演創作手段的“舞臺假定性”的內部規律和審美特質,探索這一手段與劇作、演員、觀眾之間深層次的關系,使它真正成為溝通情感、揭示靈魂的有效途徑,運用表現與再現相結合的手法,創造出“戲劇演出心理時空結構”,通過具有象征寓意的環境時空、人物心理時空和富于表現性的舞臺意象,把過去的和現在的、現實的和非現實的、想象的和幻想的戲劇有效的呈現在觀眾面前。
王曉鷹自己曾這樣說過:“為了對詩化情感和人生哲理進行直接、深刻、強烈的表達,以不受生活表象局限的、不顧顯示邏輯制約的、非再現性的視聽藝術手段創造的舞臺意象”,在《愛情泡泡》中,舞臺上的三張病床代表了男女主人公的三個家,從局部看,病床是寫實的景觀,但從整體上看,病床已失去了寫實的意義。隨著劇情的展開,在三張病床的不同排列組合中和燈光的不同變化中,不僅可以變換出劇情所需的各種時空,而且由于導演運用非寫實的舞臺調度和演員不時采用非寫實的表演手法,致使舞臺時空完全抹掉了寫實的特征,營造出的是創作主體“心理的時空”,在這里,病床染上了象征隱喻的色彩——象征著主人公們壓抑的心情和變態的生活。《哥本哈根》所擁有的是一個只有幾張椅子的空蕩蕩的舞臺,而正是在這空蕩蕩的舞臺上,導演運用他詩人般的想象力,高度發揮舞臺假定性的潛能,演繹出各種不同的戲劇時空,在這個時空結構中,現實時空和非現實時空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不同性質的時空語匯是自由組接的,而白色舞臺背后的一片蒼翠的綠色不僅表明季節的變化,更象征著人的內心世界。
三、詩化的意境:意蘊深厚的審美風格
王曉鷹對新的舞臺敘述方法的探索,創造出詩化的演出時空,在審美的層面上對“詩化情感和人生哲理”進行直接、深刻、強烈的表達,使戲劇的整體表現達到一種詩化的意境。《浴血美人》中表達了對人性本質中固有的兩種相悖的東西——既追求美又保留惡——的深入思考,王曉鷹導演的這部作品詩化地體現了劇作深刻的意蘊。他不僅講述了一個易懂的故事,而且營造了一個詩化的戲劇演出時空結構,創造出令人心靈震顫的富有表現性審美特征的“舞臺意象”。在演出中,有兩個舞臺意象幾乎貫穿始終:一是把女主人公與她的女仆比作是同一個人物的兩個不同的化身。為了創造這個富有表現特性的意象語匯,王曉鷹首先在造型方面入手,把女主人公從衣著、化裝、造型都打扮出一個天仙般的美女,而女仆則打扮成一個惡魔般的丑八怪;其次,在色彩上,女主人公常常是披著紅色的披肩,而女仆則是從里到外都是黑色的服裝;再次,往往在一個舞臺行動到來或者結束之時讓這兩個人物進行一段舞蹈化的或者造型性的形體表演,兩人的動作一模一樣,只是方向相反而已。這種造型、色彩的極度對比,形體表演所表現出來的舞臺行動的一致性,以及同一性質的語匯的反復出現,便形成了一種寓意。這兩個人物猶如一個金屬錢幣的兩個側面,雖然圖樣不同,但確實是同一物體。也就是說,女主人公是女仆的軀殼,而女仆則是女主人公的靈魂,他們合二為一,構成貌似天仙、心如蛇蝎的女人的象征;另一個大的舞臺意象語匯,是演出進程中不斷出現的大幅紅綢以及這紅綢與人物的舞臺行動相結合而形成的象征語匯。紅綢在這里是象征被女主人公殺害后用來沐浴的少女的鮮血,它與女主人公的行動相結合,象征著女主人公那血淋淋的罪惡。因此,每當她殺人沐浴的時候,紅綢就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舞臺上。不僅如此,導演還將這些象征語匯擴展開去,把它運用到全劇的開場處和結尾之前。這樣,就創造了一種血腥籠罩下的整出戲的詩意氛圍,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情感沖擊力,撞擊著觀眾的心靈。
[參考文獻]
[1] [JP3]杜定宇編.西方名導演論導演與表演.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