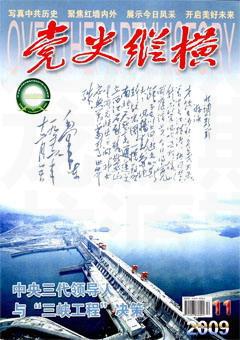給中國戰鷹一顆“中國心”
王 崇
中國航空百年,而他的生命就有93年。飛機翼下一個世紀的強國之夢,他用68載的歲月親身實踐。為了航空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生不斷奮力探索,無畏前行。從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一顆中國心承栽著他航空報國的責任與使命——
在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史上,深深鐫刻著一個簡樸而大氣的名字——吳大觀。這位我國航空發動機科研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被譽為中國“航空發動機之父”的老人,在自己93年的風雨人生中,用自己的滿腔忠誠和聰明才智,譜寫了一首振撼天地、響徹云霄、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英雄贊歌。吳大觀的外孫女梁焱說:“如果說,每個人都有欲望,那么我外公這一生唯一的‘欲望就是研制出我國自主研發的航空發動機,為祖國的戰機裝上一顆‘中國心。”
“我要學航空,不能再挨炸了!”
吳大觀,原名吳蔚升。1916年11月13日生于江蘇鎮江。很小的時候,吳大觀就樹立了遠大的志向,要為報效國家出力。從入學起,吳大觀一直品學兼擾。本來,他想報考清華大學的,但“八一三”事變爆發,導致了他清華夢的破滅,只能轉而投考長沙臨時大學。不久,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威脅武昌,吳大觀成了流亡學生。最終,他一路顛沛流離趕到了昆明,進入西南聯合大學學習。
記得還是在江蘇揚州中學讀書的時候,吳大觀初步有了“飛機”的概念:1927年,美國飛行員林白獨自駕駛飛機飛越大西洋,從美國紐約到了法國巴黎,成為名揚四海的英雄,1929年;美國海軍中校伯德乘飛機飛越南極。可在作流亡學生的路途中,他才真正了解了飛機是何物——一種能夠造成人類災難卻也可以救災濟世、為民造福的東西。一路上遭受飛機的狂轟亂炸,看到眾多被日本飛機炸得遍體鱗傷、尸橫遍野的中國人,年輕的吳大觀改變了自己的志向:吳大觀原來學習的是機械專業,他拿了成績單給航空系的主任,“我要學航空,轉學到航空系。不能再挨炸了。”
當時的西南聯合大學,群星璀璨,一大批愛國教授在艱苦的環境下帶領學生努力鉆研。這些知識分子影響了吳大觀的一生,那種愛國民主的氣質深深地融入了吳大觀的血液。若干年后,吳大觀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從西南聯大畢業后,吳大觀來到位于貴州窮山溝的大定航空發動機制造廠開始鉆研發動機。雖然他深受國民黨當局重用,被授予中尉軍銜,1944年還被選去美國參加培訓,但他完全不認同當時國民黨的那一套理念,他認為腐敗的國民黨根本無法制造航空發動機,更沒法解救中國。
1947年3月,吳大觀拒絕了美國有關單位的高薪聘任,在海上漂泊了56天,終于回到了祖國,他的全部行囊是兩個裝滿書籍和技術資料的箱子。回國后,他到北大工學院擔任講師,由于不斷接近進步人士,參與進步活動,使他成了國民黨的“反動人物”。此時,黨的地下組織找到了他,將他一家接到了石家莊。
在石家莊,他遇到了未來新中國主抓國防科技的聶榮臻同志,在吳大觀的自傳中,清晰的記述了這段特殊的經歷:
接待我的是聶榮臻,現在大家叫他聶帥,那時叫聶司令。他設宴招待我、我愛人和孩子。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話,我一直都記得很清楚。他問我,吳先生原來是做什么的啊?我告訴他,我原來是干航空發動機的,在貴州,后來到美國去學習……我告訴他,我看國民黨沒有希望,不可能搞飛機、發動機。我說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產黨、投靠解放區,希望將來造飛機、造發動機。我記得,在向聶榮臻同志說了自己的想法以后,聶司令非常高興,他大聲地對我說:“吳先生,很好啊!沒問題,你將來大有作為。”他的話給了我很大鼓勵。
從此,吳大觀堅定地走上了信仰中國共產黨的道路,至死不渝。
“搞不出新型發動機,我把腦袋掛在研究所門口。”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蘇兩大強國對我國實行封鎖,國內連續3年遭受自然災害……天災人禍使整個國民經濟處于極其困難的時期。為了打破國外的封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作出了重大戰略決策:勒緊褲腰帶,加強國防建設,搞自己的武器裝備。在這一決策的支持下,中國的航空工業開始了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發展。
幾經考察分析,在吳大觀的建議下,航空工業部決定由沈陽112廠承擔飛機制造工作,由沈陽410廠負責發動機的設計和制造工作。由于這兩個廠剛剛成功仿制了飛機和發動機,有較強的基礎,因此中國航空工業的起點就定在了這座英雄的城市——沈陽。
1956年,沈陽東郊一片出沒著野兔子的荒草地上,走進一支神秘的隊伍,領頭的人中有歷經戰火的少將、大校,有扛著中校軍銜的專家,身后是一百多個齊刷刷的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沒有喧鬧,像地里一夜鉆出的小苗,新中國第一個飛機發動機研制機構在這片草地上誕生。擔負技術總負責的便是已經40歲的吳大觀。
經過反復研究,他們決定先搞教練機,而發動機就搞噴氣式的。
在這支隊伍中,吳大觀是唯一一個見過飛機發動機的人,工作難度可想而知。吳大觀一方面努力鉆研國內外最新的研究資料,一方面指導年輕的大學生們刻苦學習,每天工作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辦公室的燈常常是從天黑亮到天明。
一次,一個研討會傳來消息,美國研制出一種新型的發動機,比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發動機轉速又提高一倍。“壞了,差距又拉開了。”與會的國內專家倍感壓力,吳大觀現場就和一位專家打了賭:“搞不出新型發動機,我把腦袋掛在研究所門口。”
經過多次分析研究有利條件和存在的難點,吳大觀決定利用410廠剛生產定型的渦噴5(蘇B—I)發動機為原準機,用相似定律縮型設計殲教-I飛機的動力——噴發-1 A發動機。這個方案可利用410廠已經有的鍛、鑄毛坯和工裝設備,不用增加任何新材料就可制造出新的發動機。這是最經濟、風險最小的研制方法,也是研制周期最短、耗資最少、較有把握的研制方法。
1958年3月,殲教-I木質樣機開始接受審查、檢驗。經過考核和研究,大家認為發動機的推力不夠,要由1200公斤增加到1600公斤。如果作這樣的改變,發動機的直徑必須相應增大。由于當時機匣、離心壓氣機、燃燒室、渦輪轉子等部件已在加工,有幾個車間的人員情緒產生了一些波動。吳大觀與當時的廠長莫文祥親自深入車間進行動員,使試制工作得以繼續進行。在全體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難,經過210天的奮戰,終于在1958年6月把4臺新發動機試制出來,通過了20小時的長期試車后,便送到沈陽飛機廠裝機。
1958年7月26日,殲教-I型飛機在沈陽飛機廠機場首飛成功。葉劍英元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等親臨沈陽出席了慶祝大會。1958年10月,裝備噴發1A發動機的兩架殲教-I飛機,從沈陽
飛到北京南苑機場,接受中央領導同志的檢閱。
“什么時候拿出你的產品獻給黨?”
粉碎“四人幫”后,61歲的吳大觀來到西航,參加從英國引進斯貝發動機的工作。在“文革”中飽受摧殘的吳大觀身患冠心病,左眼失明,但他毫無怨言地立刻投入工作。
吳大觀主要負責斯貝發動機引進專利的仿制工作。這可不是塊容易啃的骨頭——光英文圖紙資料就有127噸重!
吳大觀給技術員們下了“死命令”:早上起來補英語,晚上加班啃資料,以半年為限,每個人必須消化自己負責的圖紙并形成總結,半年后要一個一個檢查!
“‘用人民的錢買來的資料,每個技術人員都有責任鉆研學習,任何丟失資料、不認真學習的行為,都是對人民的犯罪。”吳大觀以身作則,他每天6點多到辦公室,一直呆到晚上十一二點。眼睛不好,他就拿著放大鏡查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合同資料里的130份有關設計、技術、計算和試驗報告等件件過目,一字一句對照英文,一遍又一遍驗算公式。頭四個月就看了上千份資料,記了幾十萬字的筆記。
經過半年的努力,吳大觀和技術員們邊收集、積累資料邊消化,形成了大量中文資料,為發動機成功仿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進入試制工作階段,吳大觀更忙了,每天工作都在12小時以上。發動機在英國進行高空試驗的時候,我國所有派出工作的人員全部是兩班倒,可唯獨只有吳大觀常常跟了這個班又跟下一個班,忘記了自己的作息時間。時間一長,就連現場英國的工作人員也奇怪地問:“這位老先生是你們什么人?”工作人員說:“這是我們的技術副廠長,相當于你們的總工程師。”英方的工作人員感嘆道:“你們這么大的官每天還到現場來,真是不簡單!”
1979年7月19日,離試車臺校準試車僅剩一周。此時卻出現了意外事故,本來已經做好的尼龍網進氣防護罩因導熱性能差、使用壽命短,必須改用不銹鋼制作,但這種金屬防護罩從沒制作過,重新制作至少也得10天。
吳大觀略加思索,堅定地說:“一定要在試車之前趕出來!”
這是一場和時間的賽跑,吳大觀恨不得~分鐘掰成兩半用。
要盡快做好金屬防護罩,關鍵是攻破焊接難關。吳大觀跑到老焊工姜師傅那里,吃住在一起,和他一起想辦法攻難關。經過一次次試驗,終于提前兩天趕制出了合格的防護罩,確保了試車的成功。
終于試車了,吳大觀卻暈倒了。由于長時間不眠不休、夜以繼目的工作,吳大觀發燒到39℃,但仍偷吃藥片硬頂著,終于在試車時頂不住,暈倒了。剛從醫院醒過來,他問都不問自己的病情,馬上又跑回到了試車崗位上。
熟悉航空的人都知道,沒有“斯貝”,就沒有“秦嶺”;沒有“渦扇6”,就沒有“太行”。當我國自主研制、代表著中國先進水平的新一代戰機“飛豹”和“殲10”振翅九霄、礪翼長空時,背后是吳大觀多年來默默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人生是施與不是索取。”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施與不是索取),這是雨果作品中的名言,吳老記住了,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去實踐了。
2009年元旦,吳大觀坐在電視機前,欣賞著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他拉著老伴華國的手說:“華國,我們都老了,自然規律。如果我走在前,有些事你要幫我做到。”
94歲的老伴溫柔地望著他:“你說吧。”
“第一,若有情況,不做任何治療,不要浪費國家的醫藥費。第二,后事一切從簡。第三,不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第四,代我把積蓄的10萬元錢交最后一次黨費,剩下的一半留給你生活……”
老伴認真點點頭:“我一定照辦,決不含糊!”
吳大觀抬起手,輕輕撫摸著老伴稀疏花白的發絲。半個多世紀的患難夫妻,兩顆心早就長到一起了。
多繳納黨費,是吳大觀幾十年的自覺行為。
50年代,中國普遍執行低工資制度,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二三十元,一個車間主任的工資六七十元,作為二級專家,吳大觀每月的工資是273元。他十分不安,幾次打報告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資,未獲批準。于是,從1963年開始,他主動每月多繳100元錢黨費,一直堅持了30年。“文革”期間,他被打成“特務”,工資停發,連許多年的多繳納黨費也被污蔑為“籌備特務經費”。他不作任何辯解。“文革”結束后,他把組織補發給他的6000元工資,拿出4000元再次補交了黨費。后來,當他的工資早已落人社會中下等水準,他依然沒有停止。從1994年開始,他以年為周期,每年向中組部繼續多繳納黨費4000—5000元。
除了多繳納黨費,他還積極為各種公益活動捐款。“希望工程”,他捐款;南太平洋海嘯,他捐款;四川抗震救災,他捐款;身邊的同事朋友有困難,他更是傾囊而出;及至家中的保姆生病住院,他全部買單。
2009年2月8號,93歲的吳大觀住進醫院。搞了一輩子自然科學的他,清楚地幻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拒絕一切治療。“沒有用了,不要浪費國家的醫藥費。把藥用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吧。”這是他對醫護人員說得最多的話。因肝區嚴重腹水,飲食難進,醫生給他掛吊瓶輸營養液,針頭扎進去,他堅決地拔出來。護士等他睡著了再扎針,他醒來,又堅決拔掉。醫院考慮請外院的專家為他會診,他同樣拒絕。他的慈祥、純真以及徹底的唯物主義態度,讓每一個醫護人員心懷敬意。
2009年3月18日。被喻為“中國航空工業的超級元老”、“中國航空發動機之父”的吳大觀在京去世。
百年航空報國志,仰天長嘯“中國心”。中國航空發動機之父、報國有成的黨員專家、祖國人民的忠誠兒子一吳大觀,將他一顆赤熱的“中國心”鐫刻在中華民族的百年航空史冊,伴隨著他的是一架架轟鳴著“中國心”的中國戰鷹和那震天撼地、響徹寰宇的英雄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