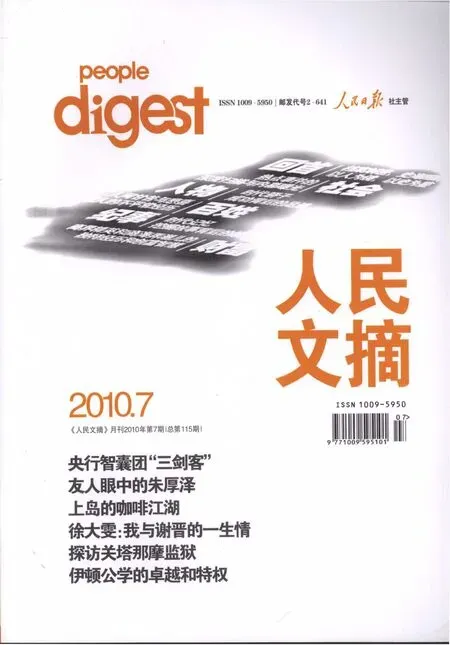中國基金經理生存報告
◎張靜

一位明星基金經理曾說過:“一百萬人里才能出一個基金經理。”沒人會質疑這個群體的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而他們自己會說:“我們是戴著光環在薄冰上跳舞。”
基金公司這兩年“吃人”的速度越來越快,國內投資界“一公一私”兩位著名基金經理先后“過勞死”,一位是年僅41歲的上投摩根原投資總監孫延群,一位是年僅44歲的私募基金元老楊駿。
由于神經系統長年高度緊張,身心健康儼然已成為基金公司最稀缺的資源。一個一個生命接踵而去,令人不由想到魯迅式的表述:難道任何人進入這個行業,都要直面淋漓的鮮血?
公募基金經理的向往
上班坐在電腦前看看圖、盯盯盤,下班后和圈里朋友應酬應酬,輕輕松松拿著百萬年薪。這是大多數人眼中公募基金經理的生活寫照,但他們卻大吐苦水:“基金經理不是人干的活,表面無限風光,實際內心很苦。每天早晨8點鐘就要上班,閱讀要聞公告、開晨會、下達交易指令,繼續閱讀、分析報告,參加上市公司路演、開會,往往連午飯都要安排成工作餐,晚上的個人時間也被工作占用,要閱讀各類分析報告或者通宵開會。”
在“業績、規模、贖回”等幾座大山中,頻繁到每周甚至每日的凈值排名一直飽受詬病。
不少公募基金經理難以忍受在“顯微鏡”下的排名壓力,紛紛投奔私募。2006年的牛市行情,也讓公募、私募基金經理的收入差距得以放大。當年收入最高的一位公募基金經理拿到了大約400萬元,同行的平均收入是50萬~200萬元。而收入最高的私募基金經理至少拿到了5000萬元,同行的平均收入也在200萬元至數千萬元之間。在短短的3年間,共有20多位大佬“公奔私”。從今年年初的出走潮看,泰達荷銀的王勇、華夏的孫建冬、東方基金的付勇,也都是無可爭議的大腕。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曹紅輝2006年旅美,當他坐在索羅斯公司的辦公室里,也曾興奮得很,不禁想起十多年前初入這個門道,從事金融交易時,對其無限景仰的心情。
然而,一位明星私募經理卻透露,其實私募基金并不是公募們想象的“凈土”,甚至更為殘酷。從2001年一直持續到2005年的4年大熊市,無數私募基金被雨打風吹去。那些幸存者,都曾像蟑螂一樣艱難生存。
私募基金經理的苦衷
2008年又是一部私募的血淚史,裁員、倒閉,比比皆是。私募基金的代言人趙丹陽被迫清盤,老牌私募李振寧的睿信1-4期虧損均超過50%。一位公募基金經理,為了實現更大程度上的財務自由,在2007年毅然“棄暗投明”,沒想到一上來就挨了熊市的一巴掌。不僅原來幾百萬的年薪成了明日黃花,他整整一年顆粒無收,加上員工薪水、租金等運營費用,自己還虧損了150萬元,連房子都抵押出去了。每當市場出現暴跌,他都難以入眠,心慌慌的,老擔心客戶打來電話。“最難熬的時候,一身一身地出汗。回想起從前的日子,悔得腸子都青了。”
就在那一年,南京共有兩位私募經理選擇用極端的方式告別人世。9月1日,34歲的周亦剛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和7歲的兒子后,從管家橋華榮大廈的21樓一躍而下。11月15日清晨,一位清華碩士研究生畢業的私募基金經理,也選擇了用跳樓尋求解脫。
同樣是把客戶的錢虧得一塌糊涂,客戶對私募,可沒對公募那么客氣。
2008年底,江湖最刺激的傳聞便是有中國巴菲特之稱的但斌被不理智的客戶“身體問候了”。他的“東方港灣”1月4日收益率為75.3%,截至6月30日,已經急劇縮水為-6.21%。
前私募基金經理侯健說過:“2001年以前,私募基金經理往往會持有基金10%~30%的份額,一旦發生虧損,將首先用這部分資金來支付,此后,私募基金經理頻頻傳出因巨額虧損而自斬手指還債或跳樓自殺事件,一部分當年赫赫有名者至今不得不隱姓埋名。”
雖然私募基金紛紛改變了運作方式,然而當客戶虧了幾百萬、上千萬,一紙合約又豈能讓他們冷靜地放過私募基金經理?
“深圳被稱為私募的天堂,市場不好的時候,那里便是煉獄。被打是家常便飯,還有更慘的。說是跳樓,實際是被人從樓上扔下去。”上文那位明星私募經理透露。“行情好的時候,你是會賺錢的神奇小子,被萬人膜拜。但只要犯了錯誤,客戶就會像扔掉死老鼠一樣拋棄你。”
“看多了私募這個行業的血淚史,我們公司定下了鐵的紀律:1.絕不為黑社會理財。2.門檻不能低于100萬元。3.更傾向與大型國企、社會組織和大機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