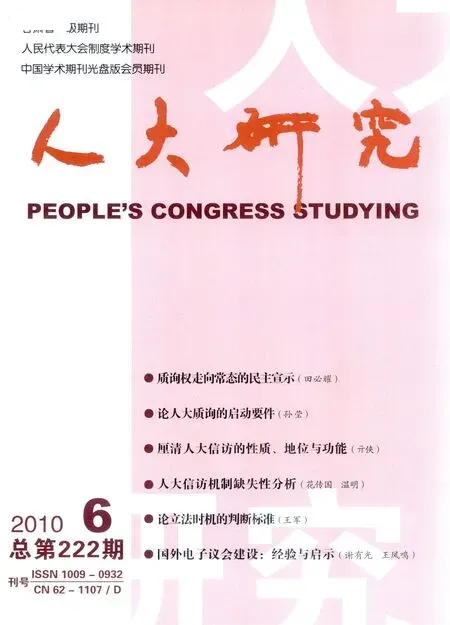論人大質詢的啟動要件[1]
□孫瑩
引言
在《權力游戲規則——國會與公共政策》一書中,作者寫道:“國會立法機關的理論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呢?首先,必須有一組明確的事實通則用以界定立法機關在政治系統中的主要功能,這些功能內涵系得自傳統與運作實務的結果……所以研究者的主要任務就在區分并說明現實運作和理想藍圖之間的差距;最后乃能提出妥適的創新建議,以縮短理論和現實的縫隙。”[2]威爾遜在《國會政體》一書中也指出,“運用中的憲法顯然與書面上的憲法有很大的區別”[3],可見,憲政理論的設計與政治法律制度的實際操作,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研究者不能對這種差距視而不見,而應積極地去探求原因,縮短理想和現實的距離。這一點對中國的人大制度研究,意義更甚。有人放言,中國當前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和人大作用的實際缺位聯系在一起的,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作用尤其發揮得不夠[4]。要充分落實人大的職權和作用,就要不斷對人大制度進行完善和修補。歷年來地方人大的建設與發展,正是“通過一些制度、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把憲法法律規定的職能在實踐中真正發揮出來,從而使文本中的權力在現實中得到實現”[5]。
人大的各項法定權力中,質詢權被認為是運用得尤其不到位的[6]。當前促進質詢權充分行使的主要途徑之一,就是完善質詢制度。由于現行質詢制度的不完善,人大沒有充分地激活質詢權。在地方層面上,“1986年以來江蘇省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質詢只有10次左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對100個縣級人大的問卷調查顯示,1991年到1994年只有12個縣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過25次質詢權……25年來有不少于80%的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沒有發生過一起質詢案。”[7]在中央層面上,全國人大迄今只提起過兩起質詢案。“就全國而言,一年質詢案超不過30起。”[8]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就代表普遍關心的問題,向國務院有關部門提出質詢[9]。人大質詢,再次吸引社會目光,成為焦點話題。
根據作者所搜集的92個質詢案例,本文提出,1979年以來中國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質詢權,在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以下幾類啟動情形,包括:(1)“一府兩院”的行為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包括違反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2)“一府兩院”違反和本級及上級人大的決定、決議,怠于執行代表提出的議案、建議;(3)本行政區域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或普遍不滿意的社會熱點問題,等等。上述質詢經驗為質詢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為填補質詢成立的啟動要件的規定,提供了立法范本。
解讀人大質詢制度
質詢,是指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在人大或常委會會議期間,對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提出質問并要求答復的一種監督形式[10]。與議案、建議、批評、意見不同,質詢是對被質詢機關的工作不清楚、不理解、不滿意的方面提出質問,要求被質詢機關作出澄清、解釋的一種活動[11]。質詢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被質詢機關必須依法答復[12]。質詢之所以有權威,就在于其強制性,被質詢的國家機關必須作出答復,被調查的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必須予以配合[13]。由于質詢是當面問答,無可推諉,因此具有剛性、快捷的特點。
我國現行法律對質詢案的規定如下[14]:(1)質詢案的提出時間為全國人大及地方人大舉行會議期間和常委會會議期間。(2)有權提出質詢案的主體:全國人大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聯名,地方人大代表10人以上聯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10人以上聯名,省、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5人以上聯名,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3人以上聯名,可以提出質詢案。(3)受質詢的機關:本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4)質詢案的成立要件:質詢案必須是書面的;必須寫明質詢對象、質詢的問題和內容。(5)質詢案的受理:人代會期間,質詢案由大會主席團決定交由受質詢機關;常委會會議期間,質詢案由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決定交由受質詢的機關。(6)質詢案的答復:人代會期間,受質詢機關在主席團會議、大會全體會議或者有關專門委員會會議上口頭答復,或者由受質詢機關書面答復;常委會會議期間,受質詢機關在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或者有關專門委員會會議上口頭答復,或者由受質詢機關書面答復。質詢案以口頭答復的,由受質詢機關的負責人到會答復。質詢案以書面答復的,由受質詢機關的負責人簽署。(7)提質詢案的代表半數以上對答復不滿意的,可以要求受質詢機關再作答復;提質詢案的或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過半數對受質詢機關的答復不滿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經委員長會議或者主任會議決定,由受質詢機關再作答復。這些規定構成了質詢案成立的形式要件。
在2007年監督法頒布實施之后,我國目前的人大質詢制度仍存在以下紕漏:(1)關于對“兩院”的質詢法律與憲法規定不一,在實踐中引起爭論[15]。現行憲法第三十七條僅規定了全國人大代表及其常委會委員有權對國務院或國務院各部委提出質詢案,并未規定人大對法院和檢察院的質詢,全國人大組織法遵循了這一規定,但地方組織法、代表法和監督法都將“兩院”與“一府”一起列為質詢對象。(2)法律未規定質詢案的啟動要件[16],即沒有規定哪些問題可以質詢,哪些不可以[17]。乍一看,不對質詢案作內容和范圍上的限制,為質詢權的行使備足了空間。但實踐中,由于缺乏具體明確的法律規定,一些代表提出的質詢案,都沒有進入質詢程序就因“質詢內容不清或者質詢的問題不是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而被轉為詢問或代表建議意見辦理[18]。(3)代表法和監督法規定了如果提質詢案的代表或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過半數對受質詢機關的答復不滿意,可以要求受質詢機關再作答復。但對于再次答復不滿意后怎樣處理,該法并未提供依據。而實踐中,第二次答復仍不滿意的情況是存在的,這種情況下法律后果如何,需要進一步的制度完善[19]。在這三個方面,本文關注的是質詢的啟動要件,即對什么樣的問題和事項,可以提出并成立為質詢案。由于質詢是對“一府兩院”工作的“質疑和詰難”,是對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不滿的表示[20],某些黨政領導對質詢這種方式不大能接受[21],認為質詢就是“批斗”[22];而一些人大的主席團或主任會議,也為著息事寧人的緣故將質詢轉為詢問、建議、意見等較為緩和的監督形式[23],以避免代表、常委會組成人員與受質詢機關負責人的正面交鋒[24]。有的地方甚至在領導講話中將人大“質詢”修飾為“咨詢”[25]。難怪坊間流傳中國的人大質詢是“多不得、少不得;深不得,淺不得;硬不得,軟不得”,其實質就是“搞不得”。
那么何種情況下或者說針對哪些問題人大可以采取質詢行動?有人指出,人大質詢要對準一個“大”字,即針對大事、大案,質詢反映的問題要嚴重、重大[26]。也有人更為具體地指出質詢針對的是涉及本級行政區的重大事項和“一府兩院”的重大違法違紀行為,而非能夠通過批評、建議、意見等形式監督的所有工作內容[27]。蔡定劍也認為,質詢案指向的是“比較重大而又帶存疑的問題”[28]。那么何謂“重大”?這個“重大”的標準如何界定呢?
盡管法律規定不盡完善,實踐中還是涌現了一系列成功行使質詢權的事例。所謂成功,就是黨政、人大、群眾三方都滿意,質詢所指向的事端也妥當解決。質詢目的“是在于獲知被質詢機關的工作情況或者對被質詢機關的工作提出批評,以監督被質詢機關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29]。質詢權的設置是為了“交流思想、溝通信息、加強合作”[30],保障人大對“一府兩院”工作的知情權,從而增進雙方的了解并成為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的途徑[31],這些成功的質詢案,就達到了這樣的目的。我國人大制度完善的一條主要途徑就是吸取實踐中成熟的做法,將其上升為立法。這些成功的質詢案為填補上述質詢制度的漏洞,提供了什么經驗與啟示呢?
人大質詢的類型化分析
筆者收集了自1979年以來的92個縣級以上各級人大行使質詢權的案例(見表1)。其中,質詢行政機關的73起,質詢審判機關的8起,質詢監察機關的1起,質詢公安機關的9起。被質詢的主要是政府及其部門(見表2)。全國人大提出質詢2起,省級人大24起,市級人大31起,區縣人大35起。級別越高,質詢權運用越少(見表3)。如圖表4所示,質詢權的行使分別在1989年、1996年、2000年,出現了三個高峰(見表4)。
從引發質詢的案由來看,主要有下列三種:
1.“一府兩院”違反憲法、法律、法規,人大因之啟動質詢
保證憲法、法律、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的遵守和執行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法定職責。當“一府兩院”出現違反法律法規的狀況,某些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會運用質詢權,有力保障了法律法規的落實。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有:1989年,山東省五蓮縣政府主要組成人員違反地方組織法不列席縣人大審議縣政府工作報告的環節,14名人大代表對此提出質詢[32]。1994年,廣東省國土廳拒不執行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廣東省城鎮房地產權登記條例》,21名委員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聯名對省國土廳提出了質詢[33]。1994年,安徽省合肥市園林局不顧《合肥市環城公園環境管理辦法》和人大的反對意見,執意在公園附近跨河蓋辦公樓,市人大常委會17名組成人員對此聯名提出了質詢[34]。1996年,廣東省河源市人大13名常委會組成人員聯名提出了對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質詢案,質疑該法院違反地方組織法和《廣東省各級人大常委會人事任免辦法》,未經市人大常委會批準擅自調整中層干部崗位[35]。等等。
“一府兩院”之所以不顧法律規定,頂撞人大權威,從上面例子來看,或是部門利益作祟,或是對人大的權威和地位認識不夠,沒有擺正人大與“一府兩院”的“主仆”關系(主人與公仆)。質詢權的行使給“一府兩院”上了一堂生動的法制教育課,使法律法規得到貫徹落實。
2.“一府兩院”怠于執行人大決議、決定,以及代表議案、建議,人大因之啟動質詢
長期以來,某些地方的“一府兩院”怠于執行人大通過的決議、決定,對代表建議、議案遲遲不落實;質詢權的使用,為其敲響了警鐘,捍衛了人大應有的地位和尊嚴。這方面的代表性范例有:1988年,貴陽市政府違反了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貴陽市城市總體規劃》,12名人大代表對此提出質詢案[36]。1996年,廣東省紫金縣17名人大代表質詢縣政府,因為縣政府違反縣人大對縣政府工作報告的審議決議,拖延公路的動工[37]。2003年,北京市人大代表質詢市法院為何拖延答復代表建議[38]。2003年,珠海市人大代表質詢市政府,督促《關于做好文物保護工作的議案》的辦理[39]。2005年,荊門市14名代表對市政府提出《關于農貿批發市場“退市進郊”決策的3號建議為何得不到落實的質詢案》[40]。等等。
3.針對本行政區域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或普遍不滿意的社會熱點問題,人大提出質詢
除了監督“一府兩院”的違法行為外,針對一些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如物價、環保、公共設施等,為督促問題的解決,人大也曾就此提出質詢。如:1998年河南省方城縣人大代表質詢縣煙草專賣局不及時兌現煙農技補費的行為[41]。1999年河南省人大代表質詢省建設廳拖延發放市民的房產證并挪用上億購房款的行為[42]。2000年,廣東省人大代表針對四會市在北江邊建電鍍城事件處理不當的問題,對省環保局提出質詢[43]。2001年沈陽市人大代表聯名提出關于加強文物保護的質詢案[44]。2008年,四川省開江縣人大代表以質詢的方式督促縣政府處理該縣物價高漲的問題[45]。等等。
結論:質詢的啟動要件
綜上所述,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三種類型的質詢啟動情形。(1)對于“一府兩院”違反國家政策、方針,違反憲法、法律、法規的行為,人大提出質詢;(2)對于“一府兩院”怠于執行本級和上級人大的決定、決議,怠于辦理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建議的行為,人大提出質詢;(3)對于本行政區域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或普遍不滿意的社會熱點問題,人大提出質詢。為了保障人大質詢權的落實,建議將這三種情形列為法定硬性條件,代表或委員提出的質詢如果符合其中任何一種,必須成立為質詢案。上述三類質詢經驗的共同特點是,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首先,質詢針對的問題有憑有據,代表和委員事前都對實際情況作了調查調研,并非基于傳聞;其次,受質詢的“一府兩院”是相關的責任方或主管方,所質詢的問題屬于受質詢機關部門的主管范圍責任范圍;第三,存在違法的現象或行為,或是“一府兩院”本身違法,或是公民或團體違法而“一府兩院”不予糾正,質詢的提出是為了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級以及上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決議在本行政區域內的遵守和執行。
質詢制度能夠有效運行是反映人大制度憲政復歸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所舉的事例表明,“有為才有位”。人大“只要想監督、愿監督、敢監督……就一定能監督出實效來”[46]。正是通過理直氣壯地行使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權力,人大才從“橡皮圖章”轉變為“鋼鐵圖章”[47]。

表1:人大質詢“一府兩院”[48]



~符號表示“一府兩院”怠于執行人大決定、決議及代表議案、建議。★符號表示“一府兩院”違反國家政策、方針,違反憲法、法律、法規。#符號表示本行政區域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或普遍不滿意的熱點問題。

?

?

?
[1]本文最初發表于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憲法青年學者論壇2010”,并經吸取深圳大學鄒平學教授的點評意見修改而成,作者謹在此表示對鄒平學教授的謝意。
[2]David C.Kozak,John D.Macartney原著,詹中原主編:《權力游戲規則——國會與公共政策》,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8頁。
[3]威爾遜著:《國會政體》,熊希齡、呂德本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0頁。
[4]《鏡報月刊》2009年4月號,第21頁。
[5]謝蒲定:《人大制度建設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探索過程——30年地方人大法治建設和制度創新的歷程及啟示(一)》,載《人大研究》2009年第5期。
[6]謝寶富:《人大質詢權的實際運用》,載《新東方》2006年第3期。
[7][8]田必耀:《對人大質詢制度設計和實踐的審視》,載《人大研究》2005年第11期。
[9]見《文匯網》《全國人大將就熱點問題質詢國務院》http://news.wenweipo.com/2010/03/10/IN1003100003.htm.
[10]劉政主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詞典》,中國檢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頁。
[11]喬曉陽、張春生主編:《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釋義與解答》,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頁。
[12]張友漁主編:《世界議會詞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敬延年、韓肇文主編:《現階段的地方人大》,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248頁。
[13]馬青紅、楊義成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簡明讀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版,第196頁。
[14]見《憲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地方組織法》《代表法》《監督法》。
[15]見童之偉:《理順關系,擺正位置——評人大代表質詢法院引起的爭論》,載《法學》1997年第9期。
[16]有人大工作者稱之為“案由要件”,見孫天富:《論質詢案成立的要件》,載《人大研究》1996年第8期。
[17]孔凡新、張守宇:《關于質詢案法律規定的疏漏及對策》,載《人大研究》1995年第10期;馬宗高:《關于加強質詢權的幾個問題》,載《人大研究》1997年第6期;秦潔、鄭連虎:《積極推行與完善有中國特色的質詢制度》,載《人大研究》2003年第10期;龐清濤:《不質詢現象引起的思考》,載《人大研究》2009年第4期。
[18]李偉:《不質詢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載《人大研究》2003年第10期。
[19]劉茂林、韋艷芹:《借鑒、剖析與完善——對人大代表質詢權的再次關注》,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云立新:《淺議我國人大代表質詢制度的完善》,載《人大研究》2003年第5期。
[20]《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詞典》,第54頁。
[21]《提質詢案豈是吃飽了多事?》,載《楚天主人》1996年第7期;黎曉武:《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應充分行使質詢權》,載《當代法學》2000年第5期。
[22]鄒立佐:《質詢權得以正常行使的關鍵是提高領導的認識》,載《楚天主人》1996年第3期。
[23]孫信成:《質詢案何其少?》,載《人大研究》1995年第6期;邵道生:《為什么質詢案難以形成》,載《人大研究》2003年第10期。
[24]孫天富:《論質詢案成立的要件》,載《人大研究》1996年第8期。
[25]黃凌:《有感于“質詢”改“咨詢”》,載《人大建設》1996年第2期。
[26]孫克江:《對一起質詢案的剖析》,載《人大研究》1998年第9期。
[27]秦潔、鄭連虎:《積極推行與完善有中國特色的質詢制度》,載《人大研究》2003年第10期。
[28]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頁。
[29]喬曉陽、張春生主編:《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釋義與解答》,第123頁。
[30]鄭允海、關珂、李秋生編寫:《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制度》,第90頁。
[31]陸宜峰:《析監督法框架下的質詢制度設計及完善》,載《人大研究》2009年第5期。
[32]資料來源:曹啟瑞、黃士孝、郭大材主編:《地方人大代表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7頁。
[33]資料來源:《廣東省國土廳被質詢》,載《楚天主人》1995年第1期;吳名響:《就部門文件與地方法規相左一事,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質詢省國土廳廳長承認做法不妥 委員對此答復不滿》,載《上海人大月刊》1995年第1期;聞言:《省國土廳廳長袁征對質詢案重新答復》,載《人民之聲》1995年第2期;《法律不容藐視》載《人民之聲》1995年第1期。
[34]資料來源:姚中元:《一起不該發生的質詢案》,載《人大工作通訊》1996年第11期 。
[35]資料來源:鄭偉華:《法院有法不依 人大依法質詢——河源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依法質詢市法院》,載《人民之聲》1996年Z1期。
[36]曹啟瑞、黃士孝、郭大材主編:《地方人大代表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8。
[37]蔡鐵強:《紫金縣人大代表質詢縣政府——政府“報告”怎能不算數 人大“決議”應該有權威》,載《人民之聲》1996年Z1期。
[38]田必耀:《人大質詢與政治和諧》,載《人大建設》2005年第8期。
[39]資料來源:《珠海:代表首提質詢案》,載《浙江人大》,2003年第3期。
[40]資料來源,朱德銀:《荊門,質詢第一案》,載《楚天主人》2005年第10期。
[41]關宏宇:《質詢,使兩千萬回到農民手中》,載《人大建設》1998年第4期。
[42]資料來源,聞雪:《房產證緣何難產?——人大首起質詢案》,載《文明與宣傳》1999年第6期。
[43]資料來源:http://gongwuyuan.kswchina.com/jichu/8161.html,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2-26/65364.html,張良:《廣州精彩質詢,針鋒相對》,載《公民導刊》2000年第10期;《人大代表質詢省環保局》,載《公民導刊》2000年第4期。
[44]資料來源,曾憲剛:《沈陽人大一起質詢案的啟示》,載《瞭望》2001年第25期。
[45]資料來源,劉志青:《決不讓物價猛于虎——四川省開江縣人大首例質詢案始末》,載《江淮法治》2008年第19期。
[46]劉錦森:《從幾件有影響的監督事件說說人大的人大監督》,載《人大研究》2007年第1期。
[47]Young Nam Cho,“From‘Rubber Stamp’to‘Iron Stamps’: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Supervisory Powerhouses," China Quarterly171(September 2002),724-40.
[48]資料來源,本表由作者根據曹啟瑞、黃士孝、郭大材主編:《地方人大代表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地方人大是怎樣行使職權的》,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地方人大監督工作探索》,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地方人大行使職權實例選編》,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等書,以及相關文章和媒體報道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