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世行為官兩年記
◎李卉 蔡怡
2010年8月18日早上八點,林毅夫從世界銀行總部華盛頓出發。下午三點抵達越南,稍事考察后,傍晚時分,他出現在了上海。“多數情況下,我在世行的一天大致如此。”他笑:“我最苦惱的就是,一天為什么只有24個小時?而世行總共有157個成員國,時間完全不夠。”
身為全球最大的國際金融機構負責人之一,“林老師”(許多人還習慣這么稱呼他)一天之內經常穿越幾個國家,“我到世行已經兩年零兩個月了,”他說:“像這樣飛來飛去,已經去過四五十個國家。”
“我一直很幸運”
2010年8月,林毅夫已經身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在國內被視為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人,并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2009年度最能影響中國的40人之一。但提起年輕時的各種傳奇際遇,他的感觸一如當年:“我一直很幸運。”
1952年,林正義(林毅夫原名)出生在臺灣宜蘭。小時候家境清苦,由于家住夜市附近,環境嘈雜,他總是晚飯后先倒頭大睡,到了午夜才起來念書,念到第二天清晨為止。
林正義的功課一直很好,最終考入臺灣大學。他從小就喜歡歷史,卻因為不服輸,選擇了當時最難考的企管研究所工商管理專業,但歷史學一直影響著他。“其實,我更想當一名歷史學家。”2008年奔赴世界銀行前夕,他還堅持這樣說。
在臺灣上大學的男生,必須參加短期軍訓。大學一年級,林正義軍訓之后,決定投筆從戎。林正義以大學生的身份從軍,很快成為軍中寵兒,他被派往金門擔任前線的連長。而此時海峽對岸頻頻出現重大舉動:1978年,中國大陸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發展時代,接著中美建交。
5個月后,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義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航道,他游過2000多米的臺灣海峽,抵達對岸的廈門,更名為“林毅夫”。此時,他的家人并不知情,第二個孩子還在妻子腹中。
“當時,我為什么會改名字?”林毅夫后來解釋道:“回來是個人的選擇,并不是因為我對臺灣有什么不滿。在臺灣,其實不管是親人、老師還是長官,對我都很好。”
“我回到大陸,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歷史所做的選擇,但我希望不傷害任何人。改了名字,就意味著過去的我人間蒸發了、消失了。”
離開臺灣時,林毅夫做了最壞的打算:“這一別,也許會像薛仁貴,與妻兒再會,大概要等上十年二十年吧。”
“但是,我還是很幸運,”他后來說,“這個時代對我很好。”4年后,林毅夫就和家人在美國團聚了。而他那時的身份,已經是經濟學大師舒爾茨的關門弟子了,后者正是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
“我長不大”
1979年的中國大陸,還不知道MBA為何物。當時的林毅夫,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很想了解這個社會體系,否則,我就無法扮演應有的角色了。那一段教育經歷對我來說相當寶貴。”
最初,林毅夫申請就讀的是中國人民大學,但校方以“來歷不明”為由拒絕了。接著,他開始申請北京大學。
那時,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張龍翔找到北大經濟系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說有一個從臺灣來的學生想到北大讀經濟,這個學生就是林毅夫。對于是否接收這個“來歷不明”的學生,陳岱孫覺得需要謹慎考慮,于是便請時任北京大學經濟系副主任董文俊出面,先和林毅夫談一談。談話的地點位于北京西直門的一家招待所,談話的結果是:董文俊發現“他是一個有理想、有上進心的年輕人”;“而且講話很有分寸,認真而嚴謹,是個想搞事業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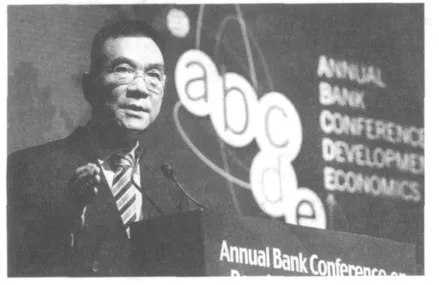
“當時我們分析,收下他最壞的結果是,最后發現他是個特務,可經濟系又沒有什么情報。”董文俊后來說。就這樣,林毅夫進了北大經濟系。
為了安全起見,對外宣稱是來自新加坡的華僑。當時,即使在北大,知道林毅夫真正來歷的,也只有幾個人而已。
那時的北大恰逢改革開放初期,校園里形成了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在一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林毅夫遇到了經濟學大師舒爾茨。通曉英文的林毅夫為舒爾茨擔任翻譯,舒爾茨對林毅夫印象深刻,主動邀請他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
“寬進嚴出”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是“寬進嚴出”的典型,每年有1/3的博士生在沒有拿到學位的情況下離開。4年后,林毅夫完成了多數同學至少5年才能攻讀下來的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更被老師舒爾茨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拿到博士學位后,1986年林毅夫又輾轉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讀完博士后。此時,北大經濟系的很多老師都猜測,“那個曾經游泳渡過臺灣海峽,到大陸來求學的林毅夫,不會再回來了。”
那時的林毅夫,已經獲得了國際經濟學界的認可。博士后畢業時,許多著名的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主動提出為他提供教職,世界銀行也向他拋來橄欖枝,但是,作為林毅夫的老師,董文俊知道,林毅夫的理想在中國:“他不是一般人。雖然他來自臺灣,但是他想的是整個中國的事情。”
1987年,林毅夫再次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他帶著30多箱英文資料回到中國,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位回國的經濟學博士。
事后,林毅夫告訴老師董文俊,關于回來的決定,他一點掙扎都沒有。“我的性格比別人更執著一點。不過,換句話說就是長不大。”
“以理服人”
世行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研究機構,在此供職的經濟學家有700多位。林毅夫認為,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和大家一起站在全球的視角,就發展中國家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進行知識上的交流。
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林毅夫覺得有點像小學生第一天上學,很興奮。不過還好,林毅夫主管的是研究部門,大家交流的是真理。
林毅夫所主管的部門里有250個學者,其中40人全都是高級經濟學家,如果把他們研究經濟的年限加起來,會超過1000年。有記者問道:“精英總是很有個性,如果大家意見不同,會不會吵起來?你會不會用權威來統一意見?”
林毅夫笑答:“我有那個權威,但是我不用。我們要以理服人,我不用職務上的便利。如果我錯了,我向你學習。如果我對了,我一定要說服你,你是錯了。知識就是力量。”
世界銀行其實和一個大公司一樣。它有執行董事會,也有管理層。一般來說,管理層不用投票的方式,而是討論,然后大家達成共識。如果沒有辦法達成共識,那么就由行長來拍板。
林毅夫說:“世行為什么會選擇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我想,最終還是因為中國這30年改革開放的成績和經驗,得到了世界的肯定;尤其是它改變了世界上很多學者對于發展和轉型問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