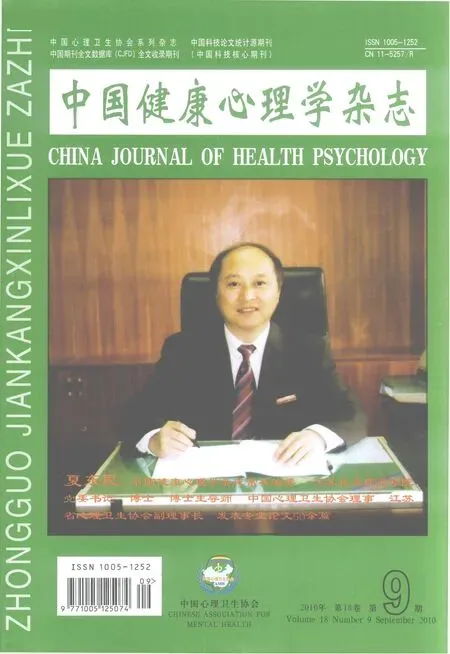生活應激與重性抑郁癥的相關研究
李 雯 文 迪
抑郁癥是一種常見易復發的精神障礙,在全世界范圍內導致殘疾的所有疾病中排名第 5,并可能在 2020年之前升至第 2[1]。美國心理學家 Aron· Beck于 1976年提出,抑郁癥的產生是由于負性認知圖式所致。大量的證據表明,早年的應激事件,如童年期被忽略、被軀體虐待或者性虐待,或早年喪失父母,是今后催患抑郁癥的重要的危險因素。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起伏代表著他們對生活中不斷的要求、成就和災難的適應性反應,并對個人社會環境的變化尤其敏感。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逆境和壓力一般會導致情緒問題,特別是抑郁癥。
1 生活應激與重性抑郁癥的定義
應激(stress)經常被看作是導致許多心理和生理問題的原因。一直以來應激反應被認為是一個適應性機制,是機體對真實或潛在的威脅有效的反應能力。據統計,目前應激的定義大約有 300多種。然而作為一個心理學專業術語,至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應激(stress)的研究最早始于 20世紀 30、40年代的醫學領域,其創始人是加拿大著名生理學家 Selye。Selye[2]在其早期著作中把這種現象稱為一般適應綜合癥。大約 10年后,他才在他的著作中提出應激這一概念。
1.1 生活應激的概念 生活應激對個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包括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眾多研究表明生活應激與某些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轉化相關。過去人們習慣將生活應激稱為生活事件或變化,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似乎對那些慢性應激與日常瑣事有所遺漏。生活應激是指由生活或與生活直接有關得因素引起的心理應激,這些因素可以稱作心理應激源[3]。生活應激源是造成人們心理應激并進而影響健康的主要應激源。關于生活應激的研究不僅是醫學心理學領域的重要課題,也是健康心理學及心理健康教育領域的重要課題。近幾年來的研究發現,不僅重大的生活變化,而且日常生活瑣事也可以導致應激反應。適當的生活變化可以激勵人們投入行動去適應新環境,但如果變化過大、過快和持續過久,就會造成適應的困難,引起嚴重的心理應激。
1.2 重抑郁癥的定義及診斷 重性抑郁癥(MDD)是以情緒低落、快感缺乏及興趣喪失等心理癥候群為主要臨床表現并伴有軀體癥狀的單相抑郁癥。是一種最常見的失能的精神狀況。目前,M DD的診斷是以美國精神病協會出版的《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4版為依據,并需要對關鍵信號和組成抑郁癥定義特征的癥狀的存在和持續時間做出臨床評價。目前的估計顯示,大約 16%的美國人在他們生活中的某個時候遭遇到了MDD,女性患病的頻率是男性的兩倍[4]。并且值得關注的一個事實是,抑郁癥常常是經常性的和周期性的,有時是慢性的。盡管這種疾病在現代社會中是高度普遍的,但它代表著一種最古老的精神病情況,且在古老的宗教文本和醫學著作中具有明確的臨床描述。
2 重性抑郁癥與生活應激的相關研究
2.1 重性抑郁癥的相關研究 周茹英,劉協和[5]運用了多種檢測手段對重性抑郁癥患者和心境惡劣患者進行檢測以期達到準確有效的結果,在對重性抑郁障礙的檢測中發現,兩種抑郁障礙均存在認知功能損害,重性抑郁癥患者的認知損害有較重且范圍較寬的認知損害,涉及雙側額葉、雙側顳葉、邊緣系統及右側頂葉。心境惡劣患者的損害多局限于額葉皮質。重性抑郁癥“伴憂郁特征”的患者較“不伴憂郁特征”的患者存在更多涉及右側半球的認知損害,同時表明精神病性抑郁癥較非精神病性抑郁癥有普遍更嚴重的認知損害。姚志劍等[6]的研究發現在明確識別喜悅表情時,抑郁癥患者右枕中回、右頂下小葉、右楔前回及雙側中央后回等腦區活動增加,而雙側頂上小葉等腦區活動降低。
賀小青、孫庚冰[7]的研究發現,西酞普蘭對于持續型重性抑郁障礙和發作性重性抑郁障礙可能存在不同的治療反應,在誘發躁狂反應的發生頻率上也存在差異,但其它副作用發生頻率的差異不顯著。薛志敏等[8]的研究發現重性抑郁癥與焦慮共病有如下特點:①共病的發生率高,與廣泛性焦慮障礙、驚恐障礙較為常見;②共病患者抑郁、焦慮癥狀及社會功能損害重;焦慮癥狀不易緩解、社會功能恢復差。因此,對于重性抑郁癥與焦慮障礙共病必須引起臨床醫師的重視。王姍等[9]的研究表明 HTR1B基因的 rs130058和 rs6298多態性可能在抑郁癥的發生中不起主要作用,而這兩個多態性所在的連鎖不平衡區域與氟西汀的療效顯著相關。
高成閣等[10]研究發現重性抑郁癥的病理機制可能與神經功能障礙、谷氨酸系統及第二信使系統異常有關,抗抑郁劑的療效可能與改善神經功能及調整第二信使系統功能失調有關。屈永才等[11]研究發現,改良電針痙攣連續兩次發作療法見效快、療效好,無明顯副作用,是治療重性抑郁癥的一種新方法。方向軍等[12]研究表明重性抑郁癥組與正常對照組在性別、年齡和受教育方面均無顯著差異,但在臨床癥狀焦慮及抑郁癥狀上差異明顯,說明兩組被試的腦功能結果具有可比性。劉軍等[13]采用基于體素優化形態測量學分析方法(Optimized voxel-based morphemetry,OV BM),分析首發重性抑郁癥患者和正常對照全腦灰質密度的改變,探討抑郁癥患者腦結構的改變,結果發現首發重性抑郁癥患者通過 OVBM方法有前額葉灰質密度的下降,與文獻報道應用 VBM方法研究結果相一致。
無論是臨床或非臨床領域,“抑郁”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已變得很普遍。在過去的幾年中,公眾對抑郁癥的接受和認可有一個戲劇性的變化,首先是在 20世紀 80年代被公眾健康方案提出 ,隨后在 1997年經 (美國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準,可在醫藥行業直接面向消費者進行藥品廣告。在歷史上沒有哪個時期,大眾對抑郁癥的研究有如此之深,對它的定義性的認可,對它的有效治療方案了解得如此之多。
2.2 抑郁癥研究中的生活應激與測量事項 批評者爭論說壓力和抑郁的聯系是因為貧乏的研究設計或錯誤的壓力測量實踐。例如,早期的使用生活事件清單自我報告的措施普遍地使生活事件和真正的抑郁癥癥狀混淆在一起了(例如飲食習慣或睡眠習慣的重大改變)或抑郁癥的結果(例如因抑郁癥患者社交或職業失能引起的職業問題和關系問題)。此外,抑郁癥可能存在潛伏期,不僅有初始癥狀還甚至會導致以后的生活壓力階段。重大損失、生活中的挫折,和其他重要的社會心理活動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嚴重抑郁癥情況的催化劑。隨著現代壓力理論和生命事件清單方法學在 20世紀 60年代末的發展,檢查生活壓力和抑郁癥的實證研究增多了[14]。
此外,經證實 ,調查對象對自我報告清單項目的解釋和回答往往很特殊[15]。自我報告清單上認同的生活事件與調查者預期的事件本質相符的占了不到 50%的時間[16]。而在基于采訪的過程中,調查對象在自我報告措施中普遍提供的資料與之前的不一致,這突出了更仔細的生活壓力的評估和實施的優點[17]。利用這些嚴格的基于采訪的方法,研究不僅支持壓力有原因的先于抑郁癥的觀點,而且也證明了獨立生活事件的因果聯系是超出個人控制的[18]。
2.3 抑郁癥與重度生活應激并非成正比
2.3.1 抑郁不總是伴隨著重度生活應激而生 雖然壓力通常在抑郁癥初期之前,但大多數經歷生活壓力的人都不會就此崩潰。產生抑郁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如遺傳基因、生活事件、人格特征、人際交往、認知等等。據估計,大約有五分之一經歷嚴重生活事件的人后來患了抑郁癥。這表明,其他因素也影響著生活壓力下的潛在抑郁傾向。例如,兒童時期受虐待和早年喪親與后期生活患抑郁癥的高風險有關系,并可能使個人對后期緊張性刺激的抑郁傾向更敏感。其次,經發現,社會支持也可在抑郁癥初期對高壓力下的個人起緩沖作用。遺傳傾向性,生物敏感性,以及個性特征都被認為可對在經歷了生活壓力后患抑郁癥的可能性造成影響[19]。
大量數據表明,抑郁癥遺傳傾向者對生活壓力的負面影響特別敏感。在最近的 1項研究中 Caspi等[20]人發現,在多態性區域轉蛋白復合胺基因(5-HTTLPR)中擁有一兩組短等位基因的人在高壓生活事件下尤其容易患抑郁癥。10多份答復和元分析審查都強調指出,僅僅在高度生活壓力的情況下基因效應會預示著患抑郁癥(例如基因和環境的相互作用)。
2.3.2 有時沒有重大生活應激抑郁癥也會發生 近些年來,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證明了應激通過多種途徑影響機體的健康,在個體的健康和疾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據引發應激的事件強度,可將應激源分為:生活事件和日常應激。所謂“日常應激”是指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刺激,包括小的煩心的事情,大的壓力,難以解決的問題和困難;這些事件可能很少發生,也可能經常發生;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長期存在。 Andrews認為,這類日常事件雖不是很嚴重,但是能造成許多人困擾,當個體沒有良好的應對方式和支持系統時,就會導致“日常困擾的疊加效應”而陷入應激狀態[21]。這些事情具有重復性、長期性、頻繁性的特點,人們難以避免,可能引起慢性的應激狀態。
對有關壓力形式的抑郁癥(如反應性抑郁癥)和無關壓力形式的抑郁癥(例如內源性抑郁癥)的爭論持續了數十年,帶來了廣泛且經常有爭議的討論[22]。迄今為止,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辦法。因此,目前重度抑郁癥的診斷做法沒有系統地評價是否有重大生活壓力的存在。
Kendler調查了 7500名雙胞胎神經質人格和生活事件,結果發現神經質和生活事件會增加重性抑郁發作的危險,而且兩者的交互作用說明在生活事件出現時,高水平神經質的個體更容易重性抑郁癥復發[23]。吳善玉,趙紅姬[24]的研究表明直接誘發大學生抑郁癥狀的應激反應來自情緒反應、生理反應、行為反應。生活應激源中的挫折、壓力、變化和沖突均可引起情緒異常反應,同時也產生應激生理反應及相應的行為反應,抑郁癥狀的發作正是與這些綜合應激反應的直接誘發有關。
重大生活事件可能會開始一個人的首次抑郁時期,但“莫名悲傷”可能是隨后復發的特點。目前的精神生物學理論假定,重度抑郁癥是一個動態過程,其中,根據前期壓力和抑郁經歷,繼續抑郁的可能性事件隨著時間增大。從理論上說,這種復發傾向的增強可包含 1個或多至 3個過程:①逐步輕微的生活壓力也能引起復發;②復發變得更加“自然”,且獨立于生活壓力(無關壓力的生物因素占上風);③無論是否有壓力,高度敏感的個人易于從一開始就經歷許多抑郁階段。評估這些可能觀點的研究表明了一生中抑郁癥的第一階段與第一次復發的區別,也為遭受疾病的團體保存了希望,能預測和管理一生中復發的周期。如果一個人經歷愈多的抑郁階段,復發的傾向就隨著時間遞增,預防抑郁癥這個主題的重要性在臨床上就變得更顯著[25]。
為確認在抑郁癥初期重大生活應激的有無同樣重要,重大生活壓力的測量方法可能對分離出典型自發性疾病有幫助,這里的自發性指的是,抑郁癥發生在生活、在不盡優越和令人羨慕但相對無壓的人群中。這一假設的以“莫名悲傷”的子型抑郁癥很可能因無處不在的表面壓力解釋被忽略,或者因復雜的壓力程度被遮蔽。這些解釋性問題和測量偏差會在使用嚴格的壓力測量程序時被最小化,這些程序包括精確的定義,操作標準,事件和起始的精確測定。
3 小結與展望
目前關于重度抑郁癥的研究仍存在爭論,問題在于有人認為生活壓力是一種有用的解釋性結構,而反對方則認為生活壓力是一種被誤導的解釋性反射作用,什么時候生活應激是促成抑郁癥的原因,什么時候確定是生活應激而不是其他病原?通過區分生活壓力所可能扮演的多重角色,并且通過討論重要的研究設計和衡量問題,我們相信生活壓力將繼續提供關于抑郁癥的來源和性質的有用信息。
通過本文我們粗略了解了生活應激的定義、重性抑郁癥的定義及診斷等,主要思考了人們如何在當前的生活和社會環境下對不安的情緒做出常規的處理。但對于可理解的心理應激和明顯的令人費解的精神病理學又將怎樣進行區分呢?從某種重要意義上說,心理上的逆境為精神病分類和診斷提供了賴以存在的基礎。由于對逆境的正常反應范圍組成欠缺確切的了解,結構性缺陷很可能通常存在于精神病理學的定義基礎上,特別是存在于重度抑郁癥上區分心理困苦和重度抑郁癥是診斷上的一個很大的挑戰。此外,生活應激這個新角色可能幫助我們對抑郁癥的理解,這也是一個挑戰。
最近有人建議,對激烈生活壓力和適應性疾病的正常抑郁反應普遍地導致了臨床人數中重度抑郁癥的錯誤診斷(例如重度抑郁癥的“假陽性”診斷問題)。此外,由于心理健康研究人員已經開始在非臨床和社區樣本上評價抑郁癥,重度抑郁癥對可能的假陽性診斷的關切可能特別涉及到它的普及度的準確估計和治療需要的評估[26]。
總體而言,關于重度抑郁癥研究,考慮生活應激的理論與實證要求正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和復雜化。無論生活應激存在與否,或是處于兩者之間,它都是掀開重度抑郁癥神秘面紗的重要話題和手段。
[1]Michaud C M,Murray C J L,Bloom B R.Burden of disease: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01,285:535-539
[2]王明輝,張淑熙.應激研究綜述 [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3(2):59-62
[3]金怡,姚本先.生活應激研究現狀與展望 [J].寧波大學學報,2007(2):33-37
[4]Kessler R C,Berglund P,Demler O,Jin,et al.The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 e disorder:Results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NCS-R)[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03,289:3095-3105
[5]周茹英,劉協和.重性抑郁癥與心境惡劣障礙的神經心理學對比研究 [J].四川精神衛生,2002,15(1):4-7
[6]姚志劍,杜經征,謝世平,等.女性重性抑郁癥患者識別動態面部表情的神經基礎的 fM RI研究 [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8,22(4):258-264
[7]賀小青,孫庚冰.重性抑郁癥持續型和發作型西酞普蘭治療的對照研究 [J].浙江預防醫學,2005,17(8):66-68
[8]薛志敏,國效峰,趙靖平,等.重性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的臨床研究[J].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5,14(12):1079-1081
[9]王珊.HT R1B基因多態性與重性抑郁癥及氟西汀療效的關聯研究[J].臨床心理衛生,2008(5):392-393
[10]高成閣,孫彥,孫親利,等.SSRIs抗抑郁藥治療首發重性抑郁癥患者前后雙側額葉和海馬 H2M RS的分析 [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8,29(6):670-673
[11]屈永才,高學軍,林頁,等.改良電針痙攣連續兩次發作治療重性抑郁癥療效分析 [J].第三軍醫大學學報,2002,24(9):1097-1098
[12]方向軍,劉軍,朱仁勇,等.首發重性抑郁癥患者面部表情刺激的腦功能磁共振研究 [J].醫學臨床研究,2008,25(10):1736-1743
[13]劉軍,湯艷清,湛紅獻,等.首發重性抑郁癥患者腦結構的磁共振初步研究 [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8,16(5):501-502
[14]Monroe S M.Modern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ing andmeasuring human life stress[J].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8,4:33-52
[15]Dohrenwend B P.Inventoryin stressful life events as riskfactors for psychopathology:Toward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intracategory variability[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6,132:477-495
[16]Monroe S M,Reid M W.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in depression:Genetic polymorphisms and life stress polyprocedures[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19:947-956
[17]McQuaid J R,Monroe S M,Roberts J E,et al.A comparison of two life stress assessment approaches:Prospective prediction of treatment outcome in recurrent depression[J].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2000,109:787-791
[18]Hammen C.Stress and depression[J].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5,1:293-319
[19]Van Praag H M,Kloet E R,Van Os J.Stress,the brainand depression[M].New York:Cambridg e University Press,2004,3:325-332
[20]Caspi A,Sugden K,Moffitt T E,et al.Influence of life stress on depression:Moderation[J].Science,2003,301:386-389
[21]姚樹喬,羅英姿.大學生神經質人格對抑郁癥狀的影響:一年追蹤研究[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9,17(2):598-600
[22]Monroe S M,Slavich G M,Georgiades K.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life stress in depression[M]//Gotlib I H,Hammen C.Handbook of depression.2 ed.New York:Guilford,2009:340-360
[23]Kendler K S,Kuhn J,Prescott C A.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neuroticism,sex,and stressful Life Ev ents in the prediction of episodes of Major Depression[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004,161(4):631-636
[24]吳善玉,趙紅姬.大學生生活應激與抑郁癥狀、自殺意念的研究[J].現代預防醫學,2009,36(15):2918-2922
[25]Monroe S M,Harkness K L.Life stress,the''kindling''hypothesis,and the recurrence of depression:Considerations froma life stress perspective[J].Psychological Review,2005,112:417-445
[26]Scott M Monroe1,Mark W,Reid.Life Stress and Major Depression[J].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