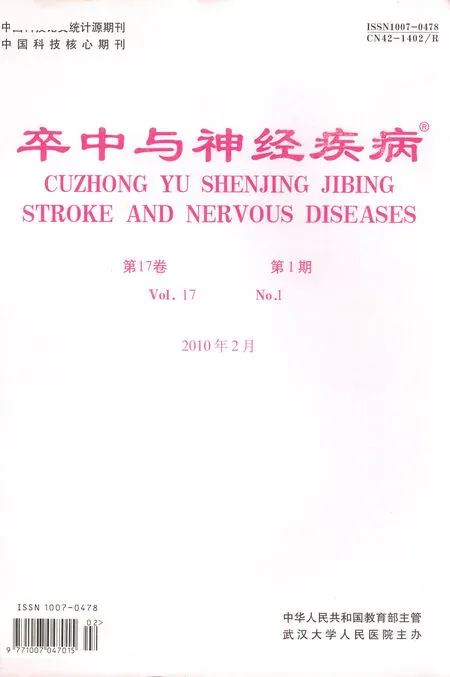肌萎縮側索硬化研究進展
曾艷平 肖哲曼 孫瑞迪 盧祖能
肌萎縮側索硬化癥(ALS)是運動神經元(MN)系統的變性疾病, 其病因、發病機制均不明確[1,2];因此也無有效治療措施。本文將主要回顧近年來有關ALS 病因、病理生理和發病機制研究方面的進展,并簡要概述臨床相關問題。
1 概 述
ALS5%~10%的病例為家族性(fALS), 90%~95%為散發性(sALS)[1,2]。sALS 的年發病率為1.5 ~2.0/100000,患病率6/100000,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易患病(1.6∶1)[2]。
1.1 臨床特征、變異型及類ALS 綜合征[1,2]
ALS 臨床特點是由從皮質到脊髓前角各水平MN 喪失所體現的。經典ALS 特指既累及上運動神經元(UMN)、又累及下運動神經元(LMN)的疾病形式。在經典ALS, 身體多個區域的MN 受累, 涉及2 個或以上水平。可累及脊髓前角和腦干的LMN、中央前回皮質脊髓束的UMN, 且常累及額葉前部的MN。LMN 喪失可導致肌肉進行性無力和消瘦(萎縮)。 皮質脊髓的UMN 喪失, 可能出現僵硬(痙攣狀態)、反射異常活躍及病理反射。額葉前部MN 的喪失,可能導致特殊形式的認知損害,其中執行功能障礙最常見。
進行性肌萎縮(PMA)是無UMN 體征的LMN 綜合征,與ALS 之間的關系一直有爭議。許多PMA 患者的病程與經典ALS 無差別,最終會發展為完全的ALS,但有些患者進展相當緩慢, 提示其為脊髓性肌萎縮(spinal muscular atrophy)(一種破壞性小得多的運動神經元病)的變異型。原發性側索硬化(PLS)是無LMN 受累純粹的UMN 疾病——該疾病實體也一直有廣泛爭議。進行性球麻痹(PBP)罕見, 疾病局限于延髓肌肉, 延髓肌肉最先受累者, 大多數會進展為經典ALS。緩慢進展且缺乏UMN 體征者強烈提示類ALS綜合征。延髓脊髓性肌萎縮(bulbospinal muscular atrophy)即肯尼迪綜合征——X 連鎖(Xq11-q12)隱性LMN 綜合征,雖然從學術上是脊髓性肌萎縮的變異型, 但可與ALS 相混淆[2]。多灶運動神經病可治療, 因此是ALS 最重要的鑒別診斷之一;無力一般累及上肢遠端肌肉, 呈不同的單神經分布,無UM N 體征,且進展得很緩慢, 神經電生理標志是有傳導阻滯。
ALS 病程殘酷、呈進展性,50%的患者起病后3~5 年死亡[1,2]。預后不良的指征包括[3]:發病時年齡大;用力肺活量低;從首發癥狀到就診時間短;以球部癥狀起病者。
1.2 診斷性評估[2]
神經傳導檢測和針肌電圖有助于證實A LS 的診斷, 并排除其他類似的周圍神經病變。在極少數病例, 當臨床或電生理均不能從其他方面顯示為LMN 受累, 運動單位數目估計可用于輔助診斷, 但不能成為評估療效的主要指標, 因為其測定過程存在固有的誤差。為了發現類似于A LS 的、可治療性疾病,必須根據臨床情況進行諸多相關的其他實驗室檢查。必須根據臨床表現進行針對性的影像檢查, 以排除可解釋早期臨床表現的結構性病變。極少數情況下需要肌活檢。ALS 功能評定量表(ALSFRS)是目前臨床試驗中最廣泛使用的量表。
1.3 診斷標準[4]
世界神經病學聯盟的El Escorial 標準[4], 旨在確定每位患者就診時ALS 的受累程度。比通常用于臨床實踐的證據要點稍加了限定,但對于疑為ALS 者而言, 該標準的確可提供有條理的評估方法, 可增加臨床實踐中的客觀性, 并使臨床研究更便利[2]。
診斷ALS 必須滿足如下所有條件, 并且必須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如下表現:①有UMN 受累的證據;②有LM N 受累的證據;③有疾病進展的證據(既有起病部位的進展,也有起病部位之外的進展)。
為了應用該標準,可將身體劃分為球(面部、嘴部和咽喉部的肌肉)、頸(頭后部和頸部、肩部和上背部以及上肢的肌肉)、胸(胸腹部以及脊柱中線部位的肌肉)、腰骶(下背部、腹股溝以及下肢的肌肉)4 個區域或水平來認識[2,4]。
當身體1 個區域既有UMN、又有LMN 受累時, 診斷為可能型。當一個區域的UMN 受累, 并且一個以上肢體顯示LM N 受累的電生理證據時,診斷為實驗室支持擬診型。當2個區域既有UM N、又有LMN 受累時, 診斷為擬診型;當3個或以上區域既有UMN、又有LMN 受累時, 診斷為確診型。
有ALS 家族史,一旦患者出現M N 疾病的證據,又不能用其他原因來解釋,不論受累范圍, 就可考慮為確診型。
2 病因、病理生理及發病機制方面的假說
2.1 fALS 病因
在fALS, 大多數病例呈常染色體顯性遺傳, 極少數呈隱形遺傳[5]。fALS 患者比sALS 平均起病年齡早10 ~20 年,不同家族之間的差異性大于家族內的差異性[2,5]。有些fALS 病例與sALS 難以區分,有些為獨特的表型[5]。
2.1.1 銅-鋅超氧化物歧化酶1(SOD1)
在有fALS 病史的某些家族,可見21 染色體的SOD1 基因突變[6]。現有研究表明, fALS 有10%~20%是SOD1 基因突變;其表型呈現為LMN 病變[1,2]。基于SOD1 突變體已發現的140 多個等位基因變異,由此決定了疾病的平均起病年齡及進展速度。 最常見的SOD1 突變為A4V 突變, 占SOD 患者的50%;可引起LMN 病變的快速進展, 起病后其平均存活期為12 個月[2]。北美SOD1-A4V 突變的遺傳來自400 ~500 年前的2 個共基者(美洲印第安人和歐洲人)[7]。
2.1.2 TAR DNA 結合蛋白(TARDBP)
亦稱TDP-43, 是一種RNA 處理蛋白。正常情況下,TDP-43 主要存在于細胞核。在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的fALS患者,基因異常也可由于調節RNA 代謝的蛋白的異常而致[2,3]。TDP-43 突變見于5%的fALS 患者[8~10]。
2.1.3 FUS/TLS(在肉瘤融合/在脂肪肉瘤翻譯)
ALS-6 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fALS 的一種類型, FUS/TLS(一種RNA 處理蛋白)的基因突變可引起ALS-6[11,12];在FUS/TLS 突變者,其細胞質包涵體所含的是FUS/TLS,而不是TDP-43。通常情況下, FUS/T LS 集中于細胞核。FUS/TLS 基因突變見于3%~4%的fALS 患者。
2.2 sALS 病因
sALS 病因未知, 但對其了解越來越接近了。目前的研究已表明,遺傳、環境及年齡等危險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觸使疾病發病。
2.2.1 遺傳因素
在sALS, 遺傳危險因素可能影響疾病起始。在ALS 患者親屬中,非ALS 神經變性疾病的發病率增高,表明其共同的遺傳傾向[13]。然而, 在易患病例(incident cases), 采用方法學上更優的基于人群的研究, 并未證實ALS 患者親屬其非ALS 神經變性疾病增多。搜尋等位基因變異的全基因組分析,已發現了一些感興趣的位點, 但不同家系存在不同位點[14]。缺乏可重復性表明, 在觸發sALS 發病方面非孟德爾遺傳形式的作用比預期的要小些,可能至多使終生危險增加50%。
2.2.2 其他因素
如神經毒素、谷氨酰胺毒性、氧化應激、病毒感染及重金屬毒性、環境和職業暴露等都可能成為ALS 病因。 關于ALS 的外源性危險因素, 僅吸煙很可能與ALS 相關(比不相關的可能性大些)(B 級證據水平)[15,16]。外傷、體力活動、居住在農村地區以及飲酒, 都很可能不是ALS 的危險因素(B級結論)[17]。
2.3 病理生理及發病機制假說及其對治療的思考
Rosen 的報告[6]之后,早期的研究差不多都尋求ALS 發病機制中自由基的潛在作用。此后, 在明顯的sALS 患者也發現有SOD1 突變, 但后來的研究表明, 這些患者中的某些人與要早得多的那一代有關(共同始創效應)[2]。Rosen 的報告十多年過去了,SOD1 基因突變與ALS 之間的聯系仍然不清。有關銅伴侶蛋白質以及SOD1 突變“毒性功能獲得”(也就是與喪失天然活性無關的毒性)假說,雖然有較深入的研究,但仍然難以捉摸[2]。在ALS, 神經元死亡是否由細胞凋亡所致,也仍然是爭論的熱點。需要記住的兩個基本問題是:①fALS 中與SOD1 有關者不超過20%, 而且f ALS 僅僅占所有ALS 的5%~10%。 ②從出生到死亡, 突變的SOD1酶在所有組織中均可表達。
ALS 是一種災難性的變性病,影響的是非常特定的神經元群體;SOD1 基因突變人群患ALS 之前, 為什么其正常壽命與健康人差不了多少(一般在60%以上)? 而患A LS 之后,為什么在不到5%的正常壽命中就會導致死亡? 一個可能的答案就在于“M N 的選擇性易損”這一概念,或許與MN中鈣結合蛋白的量減少有關, 但M N 的大小及其能量需求、MN 軸突的長度以及谷氨酸受體的分子構造可能也很重要[2]。
并非所有SOD1 突變者都會發生ALS。SOD1-A LS 被認為是功能獲得性疾病;SOD1 基因敲除鼠不發生ALS, 有1個突變基因和2 個正常基因的轉基因鼠, 比有1 個正常基因和1 個突變基因者病情更嚴重。異常(以及正常)SOD1 蛋白的錯折疊和沉淀,被認為是SOD1-ALS 病理生理機制的一部分,但尚不清楚的是:疾病為什么發生? 何時發生? 如何引起LMN ALS 表型?
最近的動物模型的研究表明, 從出生起就用RNA 沉默分子(siRNA)使突變SOD1 的表達沉默,可能預防轉基因鼠模型的疾病發病[18]。在人類SOD1 突變者,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研究方向,但需要克服的首要障礙就是證明臨床發病后該方法可有效阻止疾病的發展。
從份量上講, 編碼TDP-43 的基因突變這一致病因素在ALS 并不是最重要的, 但對于經典(Charcot)ALS 似乎是第二重要的原因——僅次于SOD1 突變。基于這個發現,一旦動物模型建立起來,通過與標準SOD1 模型比較——特別是因為SOD1 模型的有效性一直頗受爭議, 應該可描繪出選擇性MN 死亡機制中共同的致病因素。這一比較將有望給我們以展示——遺傳學對臨床和神經病理概念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因為早期的研究者們是用這些概念來定義諸如ALS等神經疾病綜合征的。對于已報道的散發性疾病患者而言,TARDBP 突變的發現也提出了基因突變的重要性[19]。
另外,fALS 也可有FUS/T LS 突變。由此, 關于ALS 大多數類型的病理生理, 已將RNA 代謝紊亂放在了當前的思考核心。 ALS-6 基因變種的發現, 為找到引發fALS 和sALS 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線索。這種新的基因提供了一種新的疑點:為什么ALS 會持續發展? 我們新的治療措施應聚焦在哪里? 這很可能給ALS 帶來新的治療方法。
在sALS 及非SOD1 突變的fA LS 者均發現TDP-43 陽性包涵體, 且均有1 號染色體編碼TDP-43 的基因突變——說明這類疾病的病理機制相似, 最后均導致了選擇性易損的、不同神經元的進行性變性[8~10]。
TDP-43、FUS/TLS 突變引發ALS 的機制與SOD1 突變不同。在sALS 患者的MN 胞質中,盡管發現了泛素化的病理性TDP-43 聚集物, 但這并非該病所特有的。因此, 形成病理性TDP-43 及其泛素化, 可能證明細胞死亡機制并非ALS 特有的, 是由上游過程所觸發, 導致的臨床病變取決于受累的細胞。
就ALS 而言,在最近有關TDP-43 和FUS/TLS 病理的觀察之前,許多信息來自于對攜帶人類SOD1 突變轉基因鼠的研究[20]。 突變的SOD1 通過“ 功能獲得”發揮作用。 在ALS,以下因素均可能介導該途經,從而引起細胞死亡[20]:①氧化損傷;②線粒體功能障礙;③caspase(半胱天冬酶)介導的細胞死亡(凋亡);④軸突運輸缺陷;⑤生長因子表達;⑥膠質細胞病理;⑦谷氨酰胺興奮毒性。
在ALS, 相對于病理生理的進展, 導致疾病起始的機制——與“發病機制” 這一術語可能要有所區別——仍然未知。
異常基因或基因產物在觸使fALS 疾病的發病有作用,并且在疾病進展中也可能起作用。然而,是否發生A LS, 有異常基因既不是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 因為家族性基因攜帶者并非所有人都發病, 而且基因正常也并不能避免sA LS 的發生。因為ALS 這種疾病并不會在出生時就顯現,因此,從出生到疾病發病之間必定有另外的因素介入, 甚至在發病的fALS 患者也是如此。不應將ALS 考慮為一種單一的疾病實體,而應是一個臨床診斷, 是不同病理生理級聯反應產生了共同的后果,優先導致MN 的進行性喪失。
將發病機制與病理生理區分開來是有其意義的, 因為每一階段的機制很可能不同, 因此,對那些機制進行干預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阻止ALS 的發生, 需要修改或去除疾病發病機制中的部分因素。首要條件是識別ALS 很可能的危險因素。當疾病本身已充分表達可得出診斷之時,再針對引起疾病進展的過程進行治療, 即所謂機制特異性治療(mechanism-specific treatments), 可能充其量也只起改善作用。相對于試圖搶救受累MN 的治療而言, 阻止疾病進展的治療可能更有效。針對疾病臨床表現的適應性治療(adaptive treatments), 是當下治療ALS 的主要手段。
疾病的病理生理與疾病的臨床表達, 其間的“紐帶”就是MN 喪失。在肌肉水平,散在的LM N 喪失,可導致各不同運動單位(M U)的失神經支配。疾病早期, 殘存的神經纖維建立聯系,對那些已死亡、失去軸突聯系的MU 進行神經再支配形成較大的M U。只要神經再支配能夠跟得上失神經, 臨床上可能就發現不了無力。然而, 隨著M U 變得越來越大,且隨著MU 數目開始減少, 結果就是受累肌肉比M U 正常的肌肉更快出現疲勞。因此,ALS 的首發癥狀之一就是起病部位的功能易疲勞性(例如, 講話的聲音越往后就變得越低沉)。隨著所支配肌肉的M U 數目進一步減少, 神經再支配就跟不上失神經;這時, 所出現的無力就是永久性的, 并且會不斷進展,隨之受累肌肉逐漸萎縮。在ALS,一般而言,皮質神經元喪失也可能導致無力, 但更常出現的是其他UMN 體征。
諸如谷氨酸鹽之類的氨基酸神經遞質當超過其生理濃度時則變得有毒, 所謂興奮毒性就是指這一過程。一般認為,興奮毒素類通過觸發M N 的鈣內流(在膜水平介導)、激活神經細胞內的級聯機制(包括自由基中間物), 最終導致神經元死亡[2]。因此,興奮毒性理論與自由基理論并不互相排斥。
動物模型(包括fALS 轉基因模型)也好, 人類的sALS也好,從中可得出的推論非常少。然而, 在sALS 以及動物模型中,目前所認識的谷氨酰胺興奮毒性作用為利魯唑的臨床試驗和批準使用奠定了基礎, 谷氨酸釋放抑制劑——利魯唑——作為疾病修飾治療的藥物,就是根據興奮毒性假說而確定的。相對而言,開發抗氧化劑治療ALS 的嘗試, 結果令人失望。其他發病機制假說一直集中于胞內失調、軸突轉運缺陷以及蛋白質聚集體[2]。
2.4 將危險因素與觸發ALS 起病相聯系
在sALS, 獲得性核酸變化可能觸發疾病發病。 最近的研究支持該假說, 即ALS 患者中身體相同部位的皮質和脊髓MN 最初同時受累, 并且疾病在皮質和脊髓水平獨立擴展[21]。這表明存在一個或多個“ 擴展因子” (agents of spread), 而且在疾病早期的擴展中皮質脊髓神經元有其作用[22]。ALS 在生物學上是局灶起病的, 擴展的確定使這一概念得以具體化。每位患者的疾病表型, 取決于起病部位以及特異性擴展因子的相對親和性,也就是特異性擴展因子對不同分級水平(額葉前部、皮質脊髓、脊髓/延髓)MN 的相對親和性[22]。擴展因子的選擇性親和甚至可能適用于一定分級水平內特定的MN,例如, 可導致以特殊LMN 為主的表型(連枷臂綜合征、連枷腿綜合征)[23]。
在患者UMN、LMN 中發現的大多數生化變化, 很可能是來自那些引發疾病并導致其擴展的下游。 有些變化可能代表了MN 死亡的過程, 而其他一些變化則可能反映了MN為生存所作的努力,即MN 對疾病進展的主要病理過程進行補償。
3 治療方面的概況
ALS 的治療可大致劃分為健康教育、機制特異性治療以及適應性治療或支持治療[24]。 國外較強調醫療保健、門診保健服務、非創傷性呼吸支持。當患者開始出現呼吸衰竭的早期表現(例如睡眠中斷),非創傷性呼吸支持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并延長生命[24]。
在75 歲以下、病程不超過5 年、用力肺活量大于60%的確診型或擬診型ALS 患者,在無需氣管切開的條件下,利魯唑比安慰劑延長生存期2 ~3 月——是目前改善sALS 病程的唯一治療措施[1,2]。
對癥治療包括(1)在有肢體僵硬癥狀者, 巴氯芬可用于緩解痙攣狀態和肌痙攣;鹽酸替扎尼定為作用于中樞的肌肉松弛藥,可用于UMN 受累為主的患者;(2)抗唾液過多可運用抗膽堿藥(阿米替林或安坦)、腎上腺素受體激動藥(例如假麻黃堿)、B 型肉毒毒素以及唾液腺放射治療,粘液溶解藥諸如愈創甘油醚(guaifenesin)可稀釋分泌物, 室內空氣適當的水化、濕化有幫助, 有時可能需要機械吸引裝置清除分泌物;(3)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例如, 西酞普蘭)可用于抗抑郁;(4)常用的抗焦慮藥是勞拉西泮,苯二氮卓類藥物有潛在的呼吸抑制作用,需注意要逐漸加量;(5)如果需要鎮痛藥,可考慮給予鹽酸曲馬多、嗎啡或芬太尼(貼劑), 阿片類可能引起呼吸抑制,需注意要逐漸加量;(6)聯合應用右美沙芬與奎尼丁已顯示對改善強哭強笑有效, 但需更多研究結果來證實[1,2]。
4 展 望
4.1 診斷性標記和疾病進展的標記
盡管對ALS 仍沒有強效的疾病修飾治療, 但仍在繼續開發各種潛在的藥物。因此, 對新的、潛在的治療,需要有能夠進行快速測定的方法學,包括疾病進展的標記。肺活量測定是一種重要的方法, 在ALS 臨床試驗中可用來評估疾病進展速度,但其可信度仍不確定, 尤其是在球部受累明顯者。目前,以鼻吸氣的鼻壓作為替代的評估方法。運動單位數目估計所需的方法學耗時、計算復雜, 而神經生理學指數易于計算,只需獲得計算運動傳導速度的常規數據即可。對于UMN 亞臨床受累的探測和量化,也描述過一些潛在的方法,例如磁共振擴散張量成像(DTI)及單體素磁共振波譜(HMRS)可作為識別UMN 受累的標記[25]。
4.2 疾病修飾治療新的送達方法
關于ALS 的疾病修飾治療, 必須確保所研究的藥物盡可能有效送達疾病過程的部位——也就是MN。口服或胃腸外給藥可能達不到這種靶向作用。在G39A SOD1 轉基因(小)鼠,以表達IGF-1 的腺相關病毒作為工具, 通過注射這種病毒到呼吸肌和肢體肌肉的方法, 從而將IGF-1 送達MN[26]。結果表明, 在這種鼠模型,即使在動物已出現ALS的臨床表現之后開始治療, 也可延長其生存期。 在SOD1 轉基因鼠,注射表達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慢病毒載體, 即使僅在出現癱瘓時開始實施治療也可延緩ALS 的起病、且減慢ALS 的進展[27]。這種載體可使鼠的預期壽命延長30%而無毒副作用——這是迄今為止動物模型中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之一。在G39A SOD1 轉基因大鼠, 鞘內注射重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也可延緩癱瘓的發病、且使生存期延長[28]。
4.3 干細胞治療
干細胞治療其潛在的恢復機制仍然不確定。除了取代喪失的細胞,其他過程包括細胞融合、神經營養因子釋放、內源性干細胞增值以及分化轉移也很重要。在ALS,植入自體間質干細胞到脊髓,其可行性和安全性已進行了試驗。沒有大的不良事件發生,但也沒有顯示療效的證據。主要是還不成熟,且存在倫理學問題。在ALS, 干細胞治療即使是作為試驗性治療,此前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4.4 未來的方向
由于缺少滿意的疾病修飾治療, 傳統意義上ALS 的早期診斷已不是那么必要了。相反,開發更有效治療的任何嘗試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令人鼓舞的是, 高通量技術的發現已顯示了潛在的蛋白質組學和代謝靶向, 有可能用作疾病特異性生物標記。在臨床試驗中, 這可為早期診斷提供機會,并且為監測疾病進展提供替代標記。在臨床試驗的方法學方面,顯示UMN 亞臨床受累的可靠方法也將是重要進展[25]。
ALS 有效的疾病修飾治療可能包括經病毒載體和鞘內注射的方法送達藥物。也可運用病毒載體完成基因轉移, 目的旨在使突變的基因沉默、干預RNA 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這些干預手段在動物模型的研究正在進行中。未來的治療可能還包括多模式方案,正如抗結核以及癌癥化療方案就是最好的例證。
ALS 是一種進行性、且致命的疾病,即使不是數十年, 在數年中可能仍然如此;正因為這樣, 更進一步研究姑息療法(病痛緩解護理)和癥狀控制,以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質量,將會成為頭等大事[24]。過去25 年間,我們對這個疾病的認識已經有了重要進展, 盡管如此, 要達到運動神經元病協會的目標——“遠離ALS 的世界”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 Row land LP, Shneider NA.Am 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N E ngl J M ed, 2001, 344(22):1688-700.
2 Mitchell JD, Borasio GD.Amy 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Lancet,2007, 369(9578):2031-41.
3 Haverkamp LJ, Appel V, Appel SH .Natural history of am 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in a database population:validation of a scoring system and a model for survival prediction.Brain, 1995,118:707-19.
4 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y Research Group on Motor Neuron Diseases.Revised criteria fo r the diagnosis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myotroph Lateral Sc Other Motor Neuron Disord,2000, 1(5):293-300.
5 Pasinelli P, Brow n RH.Molecular biology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insights from genetics.Nat Rev Neurosci, 2006, 7(9):710-23.
6 Rosen DR, Siddique T, Patterson D, et al.Mutations in Cu/Zn superoxide dismutase gene are associated w ith familial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Nature, 1993, 362(6415):59-62.
7 Saeed M, Yang Y, Deng HX, et al.Age and founder effect of SOD1 A4V mutation causing ALS.Neurology, 2009, 72(19):1634-9.
8 Kabashi E, Valdm anis PN, Dion P, et al.TARDP m utations in individuals w ith spo radic and familial amy 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Nat Genet, 2008, 40(5):572-4.
9 Sreedharan J, Blair IP, T ripathi VB, et al.T DP-43 mutations in familial and sporadic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Science,2008, 319(5870):1668-72.
10 Del Bo R, Ghezzi S, Corti S, et al.TARDBP (TDP-43)sequence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familial and sporadic ALS:identification of tw o novel mutations.Eur J Neurol, 2009, 16(6):727-32.
11 Kw iatkow ski T J, Bosco DA, Leclerc AL, et al.Mutations in the FUS/T LS gene on chrom osome 16 cause familial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Science, 2009, 323(5918):1205-8.
12 Vance C, Rogelj B, Hortobagyi T , et al.Mutations in FUS, an RNA processing protein, cause familial amy 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type 6.Science, 2009, 323(5918):1208-11.
13 Fallis BA, H ardim an O.Aggregation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in ALS kindreds.Amy otroph Lateral Scler, 2009, 10(2):95-8.
14 Valdmanis PN, Rouleau GA.Genetics of familial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Neurology, 2008, 70(2):144-52.
15 Sutedja NA, Veldink JH , Fischer K, et al.Lifetim e occupation,education, smoking, and risk of ALS.Neurology, 2007;69(15):1508-14.
16 Gallo V, Bueno-De-Mesquita HB, Vermeulen R, et al.Smoking and risk f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nalysis of the EPIC cohort.Ann Neurol, 2009, 65(4):378-85.
17 A rm on C.A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ex ogenous risk factor s in sporadic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Neuroepidemiology , 2003, 22(4):217-28.
18 Saito Y, Yokota T , Mitani T , et al.Transgenic sm all interfering RNA halts am 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in a mouse model.J Biol Chem, 2005, 280(52):42826-30.
19 Ludolph AC.2008 Round-Up.Neuromuscular diseases:new hopes for alleviation and elimination.Lancet Neurol, 2009, 8(1):16-7.
20 Rothstein JD.Cur rent hypotheses for the underlying biology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nn Neurol, 2009, 65 Suppl 1:S3-9.
21 Ravits J, Paul P, Jorg C.Focality of upper and low er motor neuron degeneration at the clinical onset of ALS.Neurology, 2007,68(19):1571-5.
22 Armon C.From clues to mechanism s:understanding A LS initiation and spread.Neurology, 2008, 71(12):872-3.
23 Wijesekera LC, M athers S, Talman P, et al.Natural history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flail arm and flail leg ALS variants.Neurology, 2009, 72(12):1087-94.
24 Miller RG, Jackson CE, Kasarskis EJ, et al.Practice param eter update:The care of the patient w 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m ultidisciplinary care, symptom management,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im pairm ent (an evidence-based review):report of the Quality Standards Sub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Neurology, 2009, 73(15):1227-33.
25 Turner MR, Kiernan MC, Leigh PN, et al.Biomarkers in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Lancet Neurol, 2009, 8(1):94-109.
26 Kaspar BK, Llad J, Sherkat N, et al.Retrograde viral delivery of IGF-1 prolongs survival in a mouse ALS m odel.Science,2003, 301(5634):839-42.
27 Azzouz M , Ralph GS, Storkebaum E, et al.VEGF delivery with retrogradely transported lentivector prolongs survival in a mouse ALS m odel.Nature, 2004, 429(6990):413-417.
28 Storkebaum E, Lam brechts D, Dew erchin M, et al.Treatment of m otoneuron degeneration by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delivery of VEGF in a rat model of ALS.Nat Neurosci, 2005, 8(1):8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