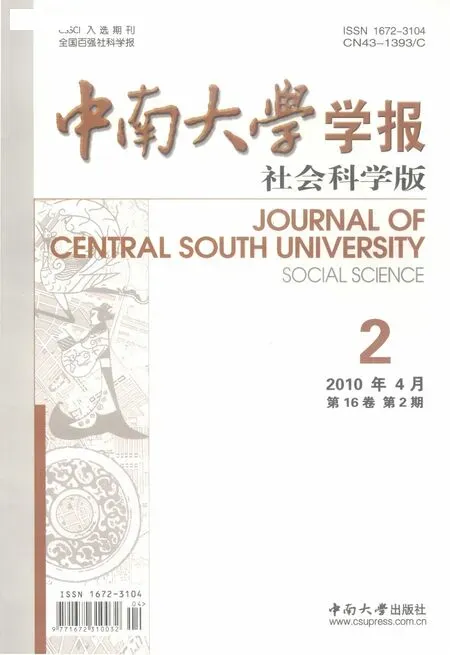被害人認識能力的刑法意義研究
黃瑛琦,張洪成
(東南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1189;中國刑警學院刑偵三系,遼寧沈陽,110854)
被害人認識能力的刑法意義研究
黃瑛琦,張洪成
(東南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1189;中國刑警學院刑偵三系,遼寧沈陽,110854)
被害人的認識能力是刑法學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被害人不具備相應的認識能力,那么其承諾在刑法學上可能就難以成立,這在行為人與被害人存在互動關系的犯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整體而言,被害人的認識能力屬于構成要件的范疇。如果被害人不具備認識能力,那么,在我國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認識能力的一系列罪名就因為不符合構成要件,而無法展開對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追究。而被害人認識能力的判斷,必須結合民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
被害人;被害人的認識能力;被害人的承諾;刑法意義;西方刑法理論
被害人的承諾是刑法學研究的一個熱點,但人們在探究該問題的時候卻很少追問被害人的承諾以什么為前提。而對這一問題的正確回答必須歸結于被害人的認識能力。如果被害人不具備相應的認識能力,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承諾的可能,被害人的承諾也就沒有探究的必要。當前,我國及國外的相關刑法理論對該問題的研究均局限于詐騙罪這一具體罪名上,而對于其他類似的牽涉被害人認識能力的罪名卻沒有展開應有的研究,這就使得司法實踐中沒有一個統一的可供操作的標準。筆者擬從我國現行刑法中涉及的被害人認識能力的罪名群出發①,對該問題進行全面研究,以期歸納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操作標準,為司法實踐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被害人認識能力之刑法意義概述
(一) 被害人認識能力刑法意義的濫觴
肇始于西方的近現代刑法學,深受羅馬法中私法主導地位的影響,其基本特征即在于個體權利的保護、意思自治思想的貫徹等。這樣,在法律上(包括傳統的私法,如民法等;也包括公法,如刑法、行政法等)就非常注重對被害人的個體意思的保障。其根源,通過羅馬著名法學家烏爾比安的法律格言“對意欲者不產生侵害”就能得到全面的體現,即行為人實施某種侵害行為時,如果該行為及其產生的結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為與結果,那么對被害人就不產生侵害問題。[1]對于出于被害人自身真實意思表示的場合,就不會產生權利侵害問題,也就無由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因此,“現代的法是建立在國家對各種群體和個人的充分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之上的,建立在國家對‘強制的壟斷’之上的法。”[2]對于個體權利,國家更加注重對公民個體意思的保障,對于其在正常意思表示下所作出的行為,國家承認其為最高的權利,有凌駕于國家刑罰權之上的效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刑法在對西方刑法理論充分借鑒的同時,也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傳統刑法中的“重刑輕民”觀念得到一定程度的軟化,人們從法律的客體逐漸變成了法律的主體,個體權利得到彰顯。當前,我國《刑法》也充分賦予了國民以自我處置權,即對于公民出于其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自損或者他人在一定范圍內的損害行為,刑法一般均不將其納入打擊范圍,除非這種損害行為超越個人承諾權限的范圍,而侵害了國家、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國民的利益,否則,刑法不會主動介入。但對于行為人欠缺認識能力、并進而影響其辨認能力的情形而言,我們就應當全面分析,因為被害人的認識能力欠缺可能直接導致行為人的損害行為構成犯罪、或者構成與被害人承諾的損害表象無關的其他犯罪。這樣的情況在刑法中并非罕見,我們認為完全有必要對之展開討論。
(二) 被害人認識能力刑法意義的研究現狀
國外及我國刑法學界針對被害人認識能力對行為定性之影響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被害人承諾的范圍內,即被害人承諾的有效要件是什么,這中間就涉及到被害人的承諾能力問題。而要正確地判斷被害人的承諾能力,就必然要探究被害人對承諾事項的認識能力,因為被害人具備相應的認識能力,是其作出有效承諾的前提。目前學界探討最多的就是詐騙罪中被害人的認識能力問題。②在該罪中,被害人的認識能力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多數學者均認為,詐騙罪中被害人必須具備認識能力,否則,將直接影響到對行為的定性。③該定性直接牽涉到的爭議就是詐騙罪與盜竊罪的界限問題,即對于沒有認識能力的被害人,如果行為人實施了詐騙行為,學界基本上將之認定為盜竊罪。其原因是千篇一律的“從無行為能力人如幼兒、高度精神病患者手中騙取財物或者從限制行為能力人處騙取該限制行為能力人無權處分的財產時,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應當認定為盜竊罪。因此,僅有處分事實而無處分意思的,不能認定為詐騙罪”。[3]筆者認為,這樣的論斷基本符合我國的司法現狀,但論者卻沒有從根本上對該問題展開討論。筆者以為,在該罪中,如果行為人確實明知被害人為沒有認識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那么對行為人認定為盜竊罪是沒有疑問的。其原因在于,該行為可以直接認定為是侵害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的代理人或者其財產的實際占有人的財產權,在行為人實施該行為的時候,于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的代理人或者其財產的實際占有人而言,該行為屬于“秘密”手段,即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的代理人或者財產的實際占有人根本不知道行為人所實施的侵害其財產權利的行為。這樣,該行為就完全滿足了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從而阻卻了詐騙罪的成立。
在英美刑法中,犯罪構成的雙層結構賦予了行為人可以將被害人的同意作為正當的辯護理由的權利,但這種同意以被害人出于自愿為必要,即被害人出于自由意志所承諾的行為才能成為正當的免責事由,“自由意志是達到一定年齡,心理成熟,精神正常的人的一種心理能力。因此,精神病患者和未達法定年齡的人是不能表示法律‘同意’的”[4](93)。而被害人因為欠缺認識能力,在行為人的欺騙下實施了一定的承諾行為,并不能成為行為人免責的理由,“‘欺騙’雖常常影響人的真實意志,所以一般認為,‘同意’應當排除‘受欺騙’。但是,‘欺騙’情況復雜,需要具體分析。從犯罪構成角度看,欺騙可分為‘事實欺騙’和‘動機欺騙’兩類。前者導致被害人對被告人‘行為事實’的誤解,后者僅僅涉及對‘引起行為發生的有關情況’的誤解。例如,醫生同女患者性交,而她不知道正在發生什么事,她以為這就是醫生對她說的進行特殊檢查與治療。這是事實欺騙,該婦女不能被認為是‘表示同意’,因為她沒有表示同意性交,同意的是接受治療,所以被告人醫生不能免除強奸罪的責任。”[4](94)這樣,在被害人沒有認識能力的情況下,其承諾行為并不影響對行為人侵害行為的定性。
以上研究表明,目前學界的研究視角僅限于個別罪名中,而對刑法中大量的涉及被害人認識能力的罪名,即涉及到行為人隱瞞真相、虛構事實,從而引起被害人認識錯誤,并作出一定處置行為的罪名中,被害人的認識能力問題并沒有被展開專門的研究,也沒有能夠形成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本文擬從刑事犯罪的相對方,即被害人的角度出發,并以其認識能力為立足點,來探討被害人的認識能力,亦即從其認識能力具備與否這個角度來探究其意思表示對權利侵害人的行為的法律性質的意義。
二、我國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認識能力的罪名之概況
從最廣義的角度講,被害人的范圍非常寬泛,既包括狹義的自然人,也包括非國有單位、國家,甚至社會。[5]但筆者傾向于將被害人限定在狹義的層面上,即被害人專指其財產權利或者人身權利受到侵害的自然人。
從我國現行刑法體例的設置來看,涉及上述狹義被害人認識錯誤的罪名主要集中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和第六章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章節中,其涉及的罪名主要有:強奸罪,詐騙罪,招搖撞騙罪,強迫他人吸毒罪,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引誘他人賣淫罪,引誘幼女賣淫罪,引誘未成年人聚眾淫亂罪等。此外,其他章節中涉及該研究問題的罪名還有集資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等。這些罪名均無一例外地涉及到被害人的認識錯誤問題,即只有被害人具備正常認識能力,且在其認識范圍內作出了錯誤的決定,才能滿足這些犯罪的構成要件。
從目前的研究實踐來看,刑法學者是從積極角度來解釋這些問題的,即認定這些罪名的時候均假定了被害人是具有正常認識能力的‘人’,而對于欠缺構成要件要求的被害人的認識能力,則完全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因此,導致在實際的司法操作中,人們往往很容易認為被害人的認識能力根本就不是該罪的構成要件,從而導致罪名適用上的不當。因此,這些罪名當中涉及的被害人的承諾,無疑均要求以被害人對于行為人欺騙的事情或者事由存在正確的理解、認識為前提。如果這個基本性的前提不具備,那么就可以說,這些犯罪的構成要件根本就不齊備,因此,無由在這些罪名范圍內認定行為的性質。故要求被害人應當具備與這些罪名要求的基本的認識能力,否則,其作出的所謂承諾完全不具備法律上的效力,從而可能從根本上影響行為的定性。
三、對刑法中行為的“認識能力”的理解
從現行的刑法規定來看,在刑法中涉及“他人認識錯誤”等的罪名,主要集中于侵犯公民個人法益的罪名中,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因為只有這些罪名才涉及“他人”(即被害人)對自身權利如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處分行為,也才存在被侵害的危險。
縱觀現代法制社會的發展進程,筆者認為,一方面,現代社會公民個人權利意識的復蘇,一定程度上給個人自由處置自己的財產或者其他權利打開了方便之門,但另一方面也給刑法在判斷行為人意思的表示真實與否時設置了障礙。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人”的是否具備相應的認識能力的判斷成為問題。
從法理的角度,明確將刑法中所要求的“他人陷入錯誤”等罪狀中規定的“他人”限定為具有一定的認識、控制能力的人,不具有這一能力的人不能理解為刑法意義上的具有正常承諾能力的被害人,也就不存在“陷入認識錯誤”的問題,就更不存在構成以這些認識錯誤為基本構成要件的罪名。
筆者認為,凡刑法中規定的行為的客觀方面要求被害人對具體行為產生了錯誤認識,從而作出錯誤意思決定的時候,其前提就必須存在被害人對具體事實存在認識的可能性。如果行為人本身由于智力障礙或者其他心理、生理原因,導致其不能認識虛假的“事實”本身,質言之,行為人沒有認識能力,則毫無疑問應當將之排除出該罪名的領域,至少不能成為認定特定罪名中的客觀方面的依據。如,詐騙罪中的被害人基于犯罪人的欺詐而陷入認識錯誤,就必須以被害人本身存在認識可能性為前提,否則,就不能認定為詐騙罪,而只能以盜竊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典型的情形為:犯罪人詐騙脫離監護人監護的精神病人或者沒有獨立判斷能力的未成年人,從而獲得其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對此情形,目前理論界、司法界的一致觀點均認為,此行為應該構成盜竊罪。其原因即在于犯罪人實施的所謂欺詐行為,在這些特定人的面前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價值,從而阻卻了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的成立,故不能盲目地將其界定為刑法意義上的詐騙行為。
同樣,可以列舉的典型情形是:行為人多次教唆、引誘、欺騙不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吸毒,或者教唆、引誘、欺騙多名精神病人或者沒有獨立判斷能力的未成年人從事吸毒活動。在此,我們從刑法的用語和立法本意也可以看出,這類行為本身沒有成立教唆、引誘、欺騙他人吸毒罪的余地。究其原因,我們認為,刑法設立教唆、引誘、欺騙他人吸毒罪,本身就暗示了被害人本身對于教唆、引誘、欺騙行為應該有概括的認識,即基于犯罪人的教唆、引誘、欺騙行為陷入錯誤,如果行為人本身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那么,對這類行為如果還是僵硬地套用這個條文,無疑是不正確的。筆者更傾向于將這一行為歸類為強迫他人吸毒罪。因為行為人在主觀惡性的指導下,實施了上述行為,于被害人而言,實則相當于強迫行為,只不過其行為的方式為與暴力、脅迫相并列的其他方法,而且事實也表明,對行為人科以這一罪名,完全與其社會危害性相適應,不會導致罪行適用上的不均衡問題。
另外,我們也可以參照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強奸罪的罪狀進行考察。在我國刑法中,強奸罪中有一種表現形式,即與不能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的,即使事先已經得到了被害婦女、兒童的同意,也不影響強奸罪的成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在該罪所涉及的這幾種情形中,其實都存在被害人的承諾問題,但因為被害人欠缺認識能力,即缺乏對性行為的意義的正確認識,從而陷入錯誤,導致自己的承諾行為無效。否則,具有正常認識能力的成年婦女,其作出的同樣承諾行為,就直接排除了行為人行為的犯罪性。這可以說是被害人承諾行為無效的典型表現。即立法者預設的情形就是這些人沒有認識能力,其本身不存在承諾的可能性,故對之必須與無承諾甚至反對相等同。
四、對被害人缺乏認識能力的處理
(一) 被害人認識能力之判斷基準
被害人的認識能力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但又必須給予正確認定的概念,否則,就無法正確判斷被害人是否存在認識能力。被害人的認識能力不能單純地依靠固定的模式來判斷,而要采用客觀的標準,即從正常人的角度來看,從被害人所處的地位及其智力的程度來判斷其對于行為人所實施的欺詐行為有無認識的可能性。如果其本來就沒有這樣的認識可能,對于處分自己的權利沒有了解能力,那么就不存在所謂的陷入認識錯誤、處分自己財物的問題。正如有學者在論述詐欺罪(即中國刑法中的詐騙罪)時所指出的那樣:“完全缺乏處分財產的意思的幼兒和高度的精神病人等,不能說會作出財產性處分行為,所以,欺騙這種人、奪取其財物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為了能夠說存在處分財產的意思,需要處分行為人自己了解其處分行為的意義。”[6]
被害人的認識能力所涉及的對象,即被害人對什么內容具有認識才是本文所討論的認識能力。筆者認為,認識的內容應該限定在被害人對自己行為的社會意義具有認識的基礎上,換言之,被害人能了解行為人所編造的虛假事實,并且對于自己的處分行為具有認識,而且對虛假事實與處分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能夠認識,但在自己的錯誤認識下,處分自己的權利。如果欠缺上述內容的認識能力,那么被害人就屬于典型的欠缺認識能力,其所作出的行為可能就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在個人作為被害人的場合,只要被害人具備相應的認識能力,并在該認識下作出正確的承諾即可。對于被害人的承諾行為的有效年齡,我國的澳門地區刑法典對之作出了明確規定,其第37條第3款:“同意之人必須滿十四歲,且在表示同意時具有評價同意之意義及可及范圍之必要辨別能力者,同意方生效力。”[7]如果行為人要具備基本的承諾能力,那么其必須首先具備認識能力,即正確認識自己行為性質的能力。
我國在“排除社會危害性行為”中對相關被害人的承諾能力或者認識能力并沒有涉及。這樣,關于被害人認識能力的問題,從刑法角度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規范標準。但根據法規范的統一性原理,可以從民法的角度找到其規范的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2條規定:“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第13條規定:“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由這些相關規定可以知道,被害人的認識能力應當參照其基本的民事行為能力。因為在涉及到的詐騙罪、欺騙他人吸毒罪等犯罪中,被害人所承諾的均是行為人對其基本的財產權、健康權等的侵害行為,這些承諾行為均建立在被害人對這些基本的民事行為的錯誤認識基礎上。因此,參照這一民事法上規定的認識能力標準是完全合理的,即對于10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及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一概否認其具有相應的認識能力,對于10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及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的認識能力則存有疑問。筆者認為,對于這一群體的認識能力,可以參照正常的社會觀念上的普通人對相應的行為的認識能力來認定其有無認識能力。但對于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對于損害其較大利益的侵害行為,筆者更加傾向于認定其為無認識能力。④這也是出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上的考慮。
(二) 被害人缺乏認識能力的處理
關于詐騙罪中被害人的認識錯誤問題,我國已經有學者對之進行了全面的探討,如張明楷教授曾指出:“欺詐行為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或者說,對方產生錯誤認識是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所致;即使對方在判斷上有一定的錯誤,也不妨礙欺詐行為的成立。在欺詐行為與對方處分財產之間,必須介入對方的錯誤認識;如果對方不是因欺詐行為產生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就不成立詐騙罪(但有成立詐騙未遂的可能性)。”[8](776)該論點就直接指出,在詐騙罪中,必須存在行為人的認識錯誤,并且也只有存在行為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的情形下,才有詐騙罪(一般指既遂狀態)存在的余地,否則,詐騙罪的基本構成要件就無法滿足。在此存在明顯的不能認定為詐騙罪的就是對機器、沒有處分能力的幼兒、高度精神病人實施的所謂“詐騙”行為。如張明楷教授指出:“機器不可能被騙,因此,向自動售貨機中投入類似硬幣的金屬片,從而取得售貨機內商品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只能成立盜竊罪。再如,行為人從沒有處分能力的幼兒、高度精神病患者那里取得財產的,因為談不上行為人的欺詐與被害人的處分,故不成立詐騙罪,只成立盜竊罪。”[8](779?780)
關于信用卡詐騙罪,我國理論及實踐界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共識,而且相關的司法解釋也為我們立足于被害人必須具備相應的認識能力提供了充分的依據。如《刑法修正案》(五)的第2條就規定了信用卡詐騙罪的基本形式就是:“(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惡意透支的。”同時該條的第3款對于盜竊未廢棄的信用卡并進行使用的行為,明確定性為盜竊罪:“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該立法例的基本立場與上述列舉的從機器中騙錢的行為完全一樣。有學者立足于行為人無視使用信用卡的場合上的差異而主張對該行為進行統一認定的觀念:“如果行為人沒有取得信用卡相關的證明,則行為人必須采取一定手段才能夠實際對信用卡上的財產取得支配權。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區分行為人行為的對象。如果是 ATM之類的機器,應當按照盜竊罪定罪處罰;如果是特約商戶或者銀行,按照信用卡詐騙罪定罪更具有合理性。”[9]筆者認為,這樣的區分存在問題的,因為既然盜竊的信用卡仍然需要具備其他條件才能使用,那么我們不如將之作為修正案(二)第一款中的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從而排除對《修正案》(五)第2條第3款的適用。從立法本意來看,第3款所指之信用卡,應該是有效且不需要任何偽造的信用卡,對盜竊這樣的信用卡并且利用的,才可能屬于其文字的應有含義。
以上我們列舉的兩個典型的涉及被害人認識能力的罪名,目前在理論及實踐界已經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對于其他涉及被害人認識錯誤的罪名,卻并未展開深入的探究。筆者認為,對于涉及被害人為個人、并且其系處分個人財產的場合,可以視為無承諾,即可以將行為人的行為方式視為刑法意義上的“秘密”等。如在詐騙罪等犯罪中,如果被害人欠缺相應的認識能力,則宜定性為盜竊罪,行為人所實施的詐騙等行為,可以視為是以未經財物所有人或者法律意義上的占有人的承諾,且這里直接實施交付的主體本身沒有詐騙罪等犯罪構成要件所要求的被害人資格,欠缺相應的承諾能力。
對于針對沒有認識能力的被害人實施的侵害其人身權利的犯罪行為,筆者認為,這完全可以參照我國刑法對行為人與未滿14周歲的幼女,或者嚴重精神病患者發生性關系的認定方法,即將這樣的承諾行為認定為無效,而視之為無承諾行為,以“強制”的概念取代之。因此,對于涉及侵害個人權利的罪名,如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引誘他人賣淫罪,引誘幼女賣淫罪,引誘未成年人聚眾淫亂罪等,宜將之分別定性為:強迫他人吸毒罪、強迫他人賣淫罪、強奸罪等。⑤因為這些罪名中雖然并未涉及到強迫的手段問題,但是,因為行為人實施的這些行為對于無認識能力,并且不能正確認定行為的社會意義的人來講,其危害性類似于刑法中的“強制”。而且,該欺騙、教唆、引誘等行為本身也完全等同于刑法中在該類犯罪的構成要件中所要求的“以其他方法”,故從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刑事政策角度考察,我們也應當以后果更為嚴重的處罰方法取代相對溫和的處置措施,從而達到遏制此類犯罪的目的。
五、結語
總之,刑法中涉及到被害人認識能力的罪名還是相當多的。在這些罪名中,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作出承諾的行為均是此犯罪成立的必備要件。如果被害人因為欠缺相關的認識能力而不具備認識的可能性,那就可能使行為人的行為無法滿足特定的犯罪構成,從而導致犯罪性質上的直接轉變。對于這些情況,我們不能盲目地把所有的行為通過原來的構成要件進行分析,而要對欠缺認識的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在行為人欠缺認識能力的前提下,所有涉及被害人認識錯誤的罪名均被阻卻。這實質上是說,該行為中并不存在實際的被害人承諾,類似于直接違背了被害人的真實意思,且被害人對該行為欠缺相應的認識。因此,我們在對該類罪名進行認定時,必須具體分析案情,根據刑法規定的相關犯罪的犯罪構成進行具體的分析,確認其具備什么樣的犯罪構成要件,以做到準確定性。當然,本文研究的視角僅僅局限在被害人為自然人的角度,對于被害人為單位、國家或者社會等的問題,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注釋:
① 所謂罪名群,是一個沒有嚴格刑法界定的詞語。筆者為了方便概括涉及被害人認識能力的所有罪名而臨時使用這樣一個概念,其正確性值得探討,但這樣便于稱呼。
② 關于詐騙罪等犯罪中涉及被害人認識能力的相關內容的研究,主要見諸于張明楷教授著的《刑法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而在趙秉志教授主編的《新刑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中,就沒有涉及到被害人認識錯誤的內容。可見,該問題的突破性研究還是最近幾年的事情,這也說明該問題的研究處于不斷的發展、完善過程中。
③ 有關被害人承諾的內容,現在各國的刑法均將之納入違法性排除事由。而在我國的刑法中,則將之作為排除犯罪性事由,具體可以參見刑法學相關教科書。如張明楷:《刑法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而關于詐騙罪中被害人應當具備相應的認識能力等,也有大量的論文、著作對之展開了討論,具體可以參見張明楷《機器不可能成為詐騙罪的對象》,載劉憲權主編:《刑法學研究》2006年第2卷。
④ 有關被害人承諾的年齡,有學者從刑法關于特殊犯罪的形式責任年齡出發,并結合民法的相關規定認為,作為被害人,對于自身的重要人身權利的認識年齡為14周歲。因為對于重要的人身權利,14周歲的未成年人具有了完全的認識,而且這種權利僅限于生命權、身體健康權等一些重要的人身權利,而其他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還應當以刑法中的16周歲為準。參見徐岱、凌萍萍:《被害人承諾之刑法評價》,《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6期。但筆者認為,這其實是本末倒置了,因為正是出于對未成年人的全面保護,才應該將被害人的認識能力的標準定為對生命權、健康權的認識能力的年齡等于或者高于對財產權的認識年齡。
⑤ 如有人在論述被害人在定罪量刑中的意義時,就對引誘幼女賣淫罪作了專門的研究,并指出,刑法第301條第2款規定,在聚眾淫亂行為中,如果被引誘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該行為成立引誘未成年人聚眾淫亂罪,而不成立一般的聚眾淫亂罪。參見杜杰靈:《刑事被害人在定罪量刑中的意義》,《達縣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4期。但筆者認為,這樣的看法實際上存在很多問題,如果將未成年人理解為年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其論斷是正確的,但如果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就應該認定為強奸罪。
[1] 張明楷. 刑法格言的展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253.
[2] H·科殷. 法哲學[M]. 林榮遠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4: 114?115.
[3] 王作富. 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下)[M]. 北京: 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3: 1275.
[4] 儲槐植. 美國刑法[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5] 劉生榮. 犯罪構成原理[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119.
[6] [日]大冢仁. 刑法概說(各論)[M]. 馮軍譯. 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3: 247.
[7] 肖敏. 被害人承諾基本問題探析[J]. 政法學刊, 2007, (3): 15?19.
[8] 張明楷. 刑法學[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9] 黃京平, 左袖陽. 信用卡詐騙罪若干問題研究[J]. 中國刑事法雜志, 2006, (4): 36?40.
Crim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HUANG Yingqi, ZHANG Hongcheng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The Third Department of Crime Investigation, China Crime Police College, Shenyang 110854, China)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riminal law. The crimes related to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are not minor. If the victim does not ha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then it is impossible to explore the victim’s promise, whi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victims. On the whole,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belongs to the element of criminal constitute. If the victim does not ha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a series of charges relating to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may not be handled, nor can they be carried out on the perpetrator,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do not meet the elements of constitute. We should combinate the civil law and other laws to judge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victim; cognitive ability of victims; promise of victims; criminal significance; western theories relating to criminal laws
book=16,ebook=158
D924
A
1672-3104(2010)02?0015?06
[編輯:蘇慧]
2009?06?23;
2009?12?15
黃瑛琦(1980?),女,安徽涇縣人,東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法學;張洪成(1978?),男,江蘇新沂人,中國刑警學院講師,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