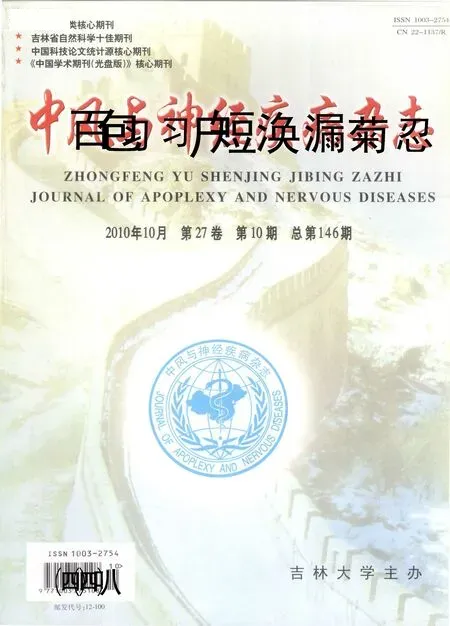PET/CT在老年期癡呆中的應用研究進展
陳艷霞, 石江偉, 于 濤, 韓景獻綜述, 于 濤審校
老年期癡呆泛指 60(65歲)以上人群中發生的各種類型癡呆,最常見的是阿爾茨海默病(AD)和血管性癡呆(VD)。國外的流行病學資料表明,65歲以上老人中,癡呆的患病率為 15%,其中 9%為 AD,4%為 VD[1]。我國在≥65歲的人群中,AD的發病率達 4.8%,VD的發病率為1.1%[2],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出現,老年期癡呆的發病率及其嚴重性日益增加,給家庭、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和人力負擔,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PET/CT作為一種新型功能成像技術,能夠根據需要選用不同的顯像劑,從分子水平研究腦組織的血流、代謝、受體分布、基因表達及功能變化,從而反映腦組織的生物化學過程和功能情況,是研究腦功能及探索疾病早期改變的敏感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神經精神系統疾病研究中。本文就近年來PET/CT在老年期癡呆中的應用情況綜述如下。
1 反映老年期癡呆的病理改變
1.1 組織病理學改變 β淀粉樣蛋白沉積和神經元纖維纏結(NFT)是老年性癡呆的最主要的病理改變。研究發現患者的這種改變早在臨床癥狀出現前幾年甚至幾十年就已經出現。而早期依賴的腦組織活檢和組織病理學檢查使得患者和家屬難以接受,正電子顯像劑18F-FDDNP和11C-PIB的應用,可以無創地反映老年斑 SP和 Aβ蛋白在腦內沉積的部位和密度,使在體觀察癡呆的病理改變變成了現實。18F-FDDNP可通過血腦屏障與AD腦內的 SP及 NFT結合,并在病變較重腦區滯留時間延長,滯留時間最高的腦區是海馬區[3],并且高攝取區與大腦內低代謝區的部位相一致,除此之外患者的認知程度與腦內F-FDDNP結合量二者之間呈負相關[4]。11CPIB也可以通過血腦屏障與腦內淀粉樣沉積物結合,并在額葉滯留量最高,其次是顳葉、頂葉、海馬和枕葉,這些結果與病理結果一致,尸檢病理發現淀粉樣蛋白沉積也主要發生在上述腦區,以額葉為主[5]。Li[6]等研究發現輕度認知障礙MCI、正常對照組NL也存在 PIB的攝取,但 AD的 PIB攝取量最大,且最明顯的腦區集中在額中回,與 MCI和 NL有顯著差異。血管性癡呆也存在AD樣神經變性改變,其 SP與NFT出現頻率遠高于正常老年人[7],只是這種病理學改變一般只限于海馬,如果 SP和 NFT超出 Thal和 Braak界定的Ⅲ期標準,則應歸類為混合性癡呆[8]。
1.2 神經遞質改變 利用適當的顯像劑進行PET研究,發現老年期癡呆患者腦內膽堿能、5-羥色胺能、多巴胺能等多種神經遞質系統均發生了異常改變。Nagaya等[9]發現,VaD患者的認知障礙程度與ACh合成減少和AChE活性相對增高有關。應用PET對乙酰膽堿受體顯像發現無論是AD還是VD患者的中樞神經系統內都存在膽堿能神經的減少,只是VD區別于AD的膽堿能神經密度減低部位集中在室周白質[10]。Meltzer等[11]用18F-altanserin PET顯像檢測 AD患者的5-HT2A受體,發現扣帶前回、額前葉、感覺運動皮層受體結合力顯著降低。Kemppainen等用 D1受體拮抗劑18CNNC756和 D2受體拮抗劑11C-raclopride(雷氯必利)對 AD患者和正常人進行 PET掃描,結果發現 AD患者D1受體拮抗劑平均攝取率在殼核和尾狀核下降,而 D2受體未受影響[12]。
1.3 腦代謝的異常 老年期癡呆患者認知障礙還與腦組織的低代謝相關,且癡呆的嚴重程度與低代謝的范圍成正相關。研究發現 AD和 VD局部腦組織葡萄糖代謝率(rCMRglu)、腦氧代謝率(CMRO 2)、局部腦血流(rCBF)都存在一定的減低區域,只是 AD的低代謝分布較 VD有一定的規律性,而 VD低代謝的分布和受損血管走行相一致。雖然PET/CT在癡呆病理機制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但是它改變了以往人們對癡呆分子學水平的研究局限于尸解和動物實驗,無法進行在體試驗的局面,為完善癡呆的病因、病理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2 老年期癡呆的早期診斷和鑒別
2.1 早期診斷,預測高危人群 老年期癡呆的早期診斷有助于指導臨床采取有效的治療手段,減輕和逆轉病情的發展。然而只有當神經元發生不可逆的損傷時,結構成像才能檢測出 AD,此時往往已經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傷,錯過了潛在修復的可能性[13]。用FDG-PET對AD的觀察者顯像發現在臨床癥狀尚未出現時,低代謝區域即可見于后扣帶回和楔前葉。馬云川[14]認為早期AD病灶局限在后頂葉、顳葉,一般不累及額葉,額葉受累與否,可作為鑒別早期 AD的診斷標準。應用PET顯像還可以檢測出無癥狀和癥狀發生前的人群存在的異常,并能預言癡呆的進展。研究認為扣帶回后部、頂葉、額葉前部、內嗅區、和顳區低代謝預示著正常年齡會出現認知減退[15]。載脂蛋白 Eε4等位基因(Apo Eε4)是一種AD易感基因,Apo Eε4攜帶者比非攜帶者出現上述區域低代謝的比例要高很多,一旦出現上述區域的低代謝,則其發展為 AD的危險性將大大增加[16]。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輕度認知障礙患者最終進展為 AD的和沒有發生變化的區別是存在右側顳頂葉皮質的低代謝[17]。
2.2 癡呆嚴重程度分級 無論是 AD還是 VD患者的臨床病癥嚴重程度與葡萄糖代謝減低程度均直接相關,低代謝區域和臨床表現一致。張新卿等[18]依據PET顯示的代謝降低程度和認知功能損害基本成正比的特點,以腦葉/小腦代謝比值作為參考指標,根據比值劃定了癡呆的嚴重程度分級:大于 1.1時為正常;1.0~0.9時為輕度癡呆;0.9~0.8為中度癡呆;小于 0.8為重度癡呆。王鐵柱等[19]采用腦皮質分區法,在目視法基礎上,結合腦皮質/小腦計數比值半定量分析對 AD進行研究,認為輕度 AD最易受累的腦區依次是下頂葉、中顳葉、上頂葉、額葉均未受累。中度AD最易受累的腦區依次是下頂葉、中顳葉、上頂葉、上額葉、上顳葉、中額葉、下顳葉。重度 AD所有患者的所有腦區都累及。AD患者大腦皮質放射性減低區的范圍隨癡呆程度加重而擴大。
2.3 鑒別診斷,針對性治療 由于老年期癡呆發病機制不盡相同,因此鑒別癡呆類型對于針對性治療癡呆有重要作用。PET-CT腦功能顯像在癡呆中的應用發現,不同原因引發的癡呆均可出現腦內放射性減低區,但是不同的癡呆出現的代謝減低區分布的特征有所不同。老年性癡呆低代謝區的分布特征較為明顯,而血管性癡呆低代謝分布是多發性,不對稱低代謝。Salmon等[20]采用18FDG-PET對 65例AD以及 64位相關性疾病患者進行研究發現,雙側或單側顳頂葉(伴有或不伴有額葉)低代謝是AD區分其他類型癡呆的特征性影像,診斷靈敏度可達 94%,李德鵬[21]認為 VD的低代謝分布與患者的腦內病變血管部位相一致,可累及基底節和丘腦。Kerrouche等[22]應用了基于像素的多變量分析技術分析18FDG-PET圖像,以鑒別VaD和AD可到達 100%的準確率,鑒別癡呆與對照組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達到72%和 96%。賈建軍[23]等分別對 7例 AD、6例 VaD及 6例智能正常老年對照者進行18F-FDDNP腦 PET顯像,受試者分別在藥物注射后 5min、25min和 45min采集圖像。結果AD患者 3個時段放射性清除情況與其他兩組圖像有明顯的不同,通過目測就可以鑒別出AD。
3 干預措施的療效評定
臨床評價癡呆治療效果時除根據臨床表現外,大多依靠心理學量表等工具,但使用量表受檢者語言表達能力及配合程度的影響較大,PET/CT作為一種靈敏的顯像技術,可以進行定量和半定量計算,越來越多的用于癡呆干預措施的療效評估中。Levy-lanad E等[24]對 AD患者用中樞選擇性 AchE抑制劑艾斯能治療 6個月,PET顯像發現治療有效者記憶相關皮層腦葡萄糖代謝顯著增加,尤其是海馬葡萄糖代謝率治療后較治療前增加了 32.5%,而治療無效者和安慰劑組海馬代謝率分別下降了 6.4%和 4.1%,表明該藥能有效阻止臨床病情惡化,顯著增加患者的腦代謝活性。朱蔓佳等[25]觀察頭電針治療 6例 VD 1個月,對患者治療前后分別進行腦PET顯像,結合PET前、后對照,發現針刺能夠增加葡萄糖的代謝量,腦功能改善程度與臨床改善情況呈正相關。黃泳、賴新生等應用 PET顯像技術,分別研究針刺加用水溝穴、百會穴、神門穴對血管性癡呆(VD)患者不同腦區葡萄糖代謝的影響,結果表明水溝穴治療 VD的方向性特點,與其改善額葉、豆狀核、顳葉的葡萄糖代謝有關;百會穴主要改善患腦額葉、健腦顳葉及雙側豆狀核區的葡萄糖代謝;加用神門穴后患者患頂葉、丘腦、尾核以及頂葉的葡萄糖代謝升高幅度大于常規針刺治療組,而扣帶回略有降低,與常規針刺組的變化比較也有顯著差異(P<0.05)。PET/CT成像檢查還可作為預后評估手段用以檢測患者掃描成像后一段時間內的精神狀態的惡化狀況。最新數據顯示,在神經核醫學的成像中所觀察到的代謝低下程度與大腦認知功能下降速度相關。此外,由于 PET/CT所用的正電子核素 C、N、O、F等均為短壽命核素,可安全、多次進行體內研究,直觀觀察示蹤劑在活體內的動態分布,從中獲得藥物或體內原有物質的各種信息,因而還可以應用于癡呆藥物的作用部位、藥代動力學、毒理學等的研究中。
4 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PET/CT作為一種新型的影像技術,能在同一個體進行多時間、多空間的腦功能重復定量觀察,有助于癡呆的病因病理、診斷以及作用機制和療效評價等方面的研究,但由于目前這項檢查費用昂貴尚不能替代常規應用良好的包括各項生化指標的實驗室檢驗及大腦結構性成像的應用,只有在常規臨床評定不能做出準確診斷時方可考慮使用。另外,由于歐美等國老年期癡呆中,AD占了首位,其次才是VD,所以國外有關VD的研究相對較少;國內關于VD的研究相對較多,但也多數是與 AD的對比觀察,因此應用PET/CT對于 VD的觀察和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神經受體、轉運體和基因表達以及新的示蹤劑的研究,PET/CT會更廣泛地應用于老年期癡呆的研究中。
[1]黃明生.阿爾茨海默病與血管性癡呆的關系和鑒別[J].中華全科醫師雜志,2006,5:331-333.
[2]Zhang ZX,Zahner GE,Roman GC,etal.Dementia subtypes in China[J].Arch Neurol,2005,62:447-453.
[3]Agdeppa ED,Kape V,Liu J,etal.2-Dialky Lamino-6-acylmalononitrile substituted naphthalenes(DNP analogs):novel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tools in Alzheimer's disease[J].Mol Imaging Biol,2003,5(6):404-417.
[4]Shoghi-Jadid K,Small GW,Agdeppa ED,etal.Localization of neurofibrillary tangles and beta-amyloid plaques in the brains of living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J].Am JGeriatr Psychiatry,2002,10(1):24-35.
[5]郭 喆,張錦明.阿爾茨海默病的放射性分子顯像探針研究進展[J].國際放射醫學核醫學雜志,2006,30(4):199-202.
[6]Yi Li,Juha O,Rinne.Regional analysis of FDG and PIB-PET images in normal aging,m 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nd Alzheimer's disease[J].Eur JNucl Med Mol Imaging,2008,35:2169-2181.
[7]閆福嶺,管學能,洪 震.Alzhe imer病和血管性癡呆的病理學關聯[J].國外醫學腦血管疾病分冊,2005,3(7):524-528.
[8]Kalaria RN,Kenny RA,Ballard CG,etal.Towards defining the europathological substratesofvascular dementia[J].JNeurol Sci,2004,226:75-80.
[9]Nagaya M,Endo H,Kachi T,etal.Recreational rehabilitation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in vascular dementia[J].JAm Geriatr Soc,2005,53:911-912.
[10]Henry N.WagnerJ.Nuclearmedicine for all the world-from molecular imaging tomolecularmedicine[J].JKorean Med Sci,2007,22:595-597.
[11]Meltzer CC,Price JC,Mathis CA,etal.PET imaging of serotonin yype 2A receptors in late life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J].Am J Psychiatry,1999,1856:1871.
[12]Kemppainen N,Ruottinen H,Negren K,etal.PET shows that striatal dopam ine D1 and D 2 receptors are diferentially affected in AD[J].Neurology,2000,55(2):205.
[13]Susanne G,MichaelW,Leon J,etal.Ways toward an early diagnosis in Alzheimer's disease[J].Alzheimers Dement,2005,1(1):55-66.
[14]李德鵬,馬云川,劉 力.PET顯像在阿爾茨海默病(AD)診斷與研究中的應用[J].CT理論與應用研究,2006,2(15):1-4.
[15]De Leon MJ,Convit A,Wolf OT,etal.Prediction of cognitive decline in normal elderly subjects with 2-[(18)F]fluoro-2-deoxy-D-glucose/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FDG/PET)[J].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1,98:10966-10971.
[16]Gary W,Susan Y,Paul M Thompson,etal.Current and future uses of neuroimaging for cognitively impaired patients.[J]Lancet Neurol,2008,7(2):161-172.
[17]Chetelat G,Desgranges B.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Can FDGPET predictwho is to rapidly convert to Alzheimer's disease[J]?Neurology,2003,60:1374-1377.
[18]張新卿,馬云川,閔寶權,等.不同癡呆程度阿爾茨海默病患者腦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的研究[J].中華醫學雜志,2001,81,499-500.
[19]王鐵柱,王 寧,馬云川.PET腦皮質分區法在 AD診斷中的應用[J].中國臨床醫學影像雜志,2007,1(18):1-4.
[20]Salmon E,SadzotB,MaquetP,etal.Differentialdiagnosisof Alzheimer disease with PET[J].JNucl Med,1994,35:391-398.
[21]李德鵬,馬云川,蘇玉盛,等.老年性癡呆與血管性癡呆的 18FFDG PET顯像分析[J].中風與神經疾病雜志,2001,18(4):213-214.
[22]Kerrouche N,Herholz K,Mielke R,etal.18FDGPET in vascular dementia:differentiation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voxel-based multivariate analysis[J].J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6,26:1213.
[23]賈建軍,湯洪川.阿爾茨海默病的18F2FDDNP腦斷層掃描顯像[J].中華老年心腦血管病雜志,2006,8:377-379.
[24]Levy-lanad E,Wijsman EM,Nemenns E,etal.A familial Alzheimer's disease locus on chromosomel[J].Science,1995,269:970.
[25]朱蔓佳,張 虹,趙 凌.頭電針治療血管性癡呆對腦功能成像的影[J].海南醫學院學報,2008,4:644-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