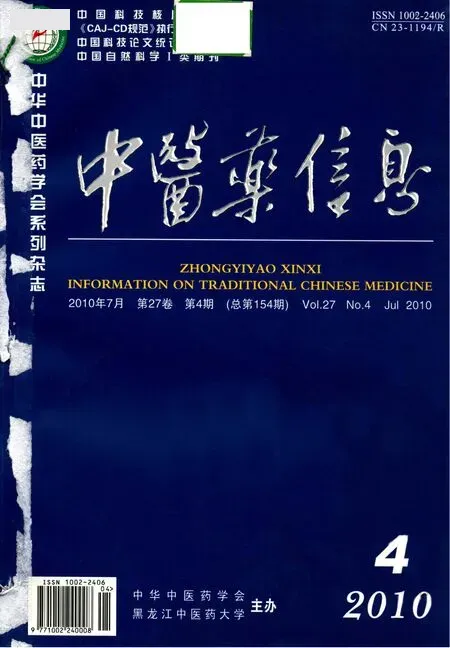近代中醫教育的反廢止努力——以課程教材建設為例
周鴻艷,李志平,李和偉
(1.哈爾濱醫科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1;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
世界文明史中,“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是不容忽視的,在疾病記載方面,在許多文明中,中國幾乎是唯一的擁有連續性著述傳統的國家”[1],中醫學在古代中國乃至世界都是較為先進的。然而到了近代,伴隨著西方醫學的傳入,中醫一統天下的地位被逐漸撼動。正如丁福保所說:鴉片戰爭以后,“西人東漸,余波憾蕩,侵及醫林,此又神農以后四千年以來,未有之奇變也”(丁福保歷代醫學目錄表)。中醫學是否還應該存在,能否繼續傳承下去,成為中醫近代史上爭論的核心問題。李約瑟所贊譽的“連續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此,中醫的教育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有中醫教育則中醫興,無中醫教育則中醫亡”。爭取中醫教育合法化一直是近代中醫界反廢止的主要內容。在爭取中醫教育合法化過程中,中醫界除了重視加入學制外,更重視中醫教育的內涵建設,尤其是在課程教材建設方面進行諸多嘗試。
1 對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重要性的認識
在清末頒布的壬寅癸卯學制中,壬寅學制沒有規定醫學的具體課程,也沒有真正實行。在癸卯學制中醫科又分醫學及藥學兩門。醫學門30門課程中只有1門中醫學課程,而且沒有分科、沒有名稱,只是籠統地稱之為“中國醫學”。藥學門16門課程中只有1門中國藥材。癸卯學制中醫科雖有中醫、中藥內容,但分別僅有1門。之所以造成這一局面,固然和清末的改良派強調引進西學、模仿日本有關,同時也與中醫學的課程教材建設欠完備不無關系。即使當時中醫學能夠加入學制,也很難像西醫學那樣列出完整的課程體系。因此,1904年,何廉臣在最早的中醫雜志《醫學報》上撰文說:“今日中醫開智莫若仿歐美治科學之法,先編定教科書,將中醫之缺者補以西法”。對于中醫教育向近代的轉型,當時的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
至民初壬子癸丑學制,大學醫科課程51門,藥學課程52門。已經完全沒有中醫、中藥學方面的內容。壬子癸丑學制頒布后,引起了中醫界的警覺,遂導致近代醫學史上首次中醫抗爭救亡運動。北洋政府在各界輿論壓力下,強調“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但在事關中醫教育的學制問題卻說:“厘訂中醫學校課程一節暫從緩議”。此語雖有搪塞之嫌,但以當時之條件,短時間內編訂中醫學課程,確實難度較大。1915年,丁甘仁為興辦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上書申請立案,雖獲備案,但教育部批復中也特別指出“惟中醫學校名稱,不在學堂系統之內,本部醫學專門學校規程內,亦未定有中醫各科課程”。內務部則強調“俟該校課程擬定后送部核查可也。”
由此可見,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私人辦學,都沒有較為完備的中醫學課程體系,教材建設更是無從談起。這一局面也是中醫學被摒棄于學制之外的一個內在因素。認識到這一問題,中醫界的有識之士開始重視中醫學課程教材的建設,以期為中醫教育的合法化奠定基礎。
2 對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的不懈努力
希冀中醫教育加入學制,一直是中醫界反廢止的重要內容,但每每功虧一簣。在這一過程中,中醫界的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中醫教育若要加入學制,就必須改進和完善中醫教育自身,使之規范化,符合近代教育模式。基于這一思路,從清末到民國,中醫界在課程教材建設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2.1 清末對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的嘗試
清末的中醫社團往往附帶有中醫教育的功能。如周雪樵等人創辦的“中國醫學會”就附設醫學講習所,開列有解剖、生理等12門課程。并于1909年起陸續編寫教材,《素靈講義》即是該會公開發行使用的第一部中醫教材。上海的另一中醫社團“上海醫務總會”也特別重視教育,在第一次議員會議上,編寫中醫教科書被列為首要任務。
2.2 北洋政府時期的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
由于中醫界對壬子癸丑學制“漏列中醫”的反抗,“北洋政府對中醫基本上執行放任、觀望政策”。從而給中醫教育造成了一個較寬松的發展環境,興辦了多所私立的中醫學校,為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的探索提供了平臺。在課程建設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共開出生理、本草等18門課程。而地方興辦的山西醫學傳習所共開出內經、解剖等20多門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時任“黃墻朱氏私立中國醫藥學校”教務主任的張山雷非常重視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撰寫了《黃墻朱氏私立中國醫藥學校編制課程商榷意見書》,這是民國時期有關中醫教材編寫、課程建設的重要歷史文獻。在“意見書”中張山雷對于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與中醫學的關系有較為正確的認識:“謹按吾華醫學,未入耕堂,編制課程,茫無成法,向來俗尚,止有李氏《必讀》、汪氏三書,似為學子問津之初步。此外則各不相謀,隨意自擇,從未有通行規則,以何者為必備之書,必由之道,此吾邦醫學所以紛別淆雜而莫可究詰也。”[2]
鑒于1925年加入學制的再次失敗,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李平書、夏應堂等人積極組織中醫課本編輯館,制定計劃以求統一全國教材。由于條件所限,這一計劃并未得以貫徹,但統一教材問題受到中醫界的廣泛認同。1928年,全國各地中醫教育界人士齊集上海,研討統一教材問題。各地代表提出自己不同的學術見解,因意見不統一,最終未能就課程、教材、學制等問題達成統一的意見。但神州醫藥總會委員蔣文芳提出的“整理固有醫學之精華,列為明顯之系統,運用合乎現代的理論,制為完善之學說”成為其后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的指導原則。
2.3 南京政府時期的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
北洋政府對中醫教育的不作為,喚醒了中醫界的覺悟,遂有各種辦學的努力和嘗試。20年代末,各地中醫學校已漸趨成熟。因而,為爭取中醫加入教育系統,迫切需要集合全國的力量,總結各地辦學的經驗教訓,并采取務實積極的方針,首先統一全國的中醫教材和課程。
1929年7月7日至7月15日,中醫藥界在上海召開教材編輯委員會會議。該次會議由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出面召集,到會者有上海中醫專校、中國醫學院等9所學校的教務負責人。均系我國近代中醫教育界著名人物。這次會議上議定了中醫學校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學說采用標準,并確定了29門課程及教授時數。審定通過了五年全日制中醫專門學校應開設的各門課程及教學時數和各年度的教學安排。這次的全國中醫教材編輯會議,是近代中醫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標志著我國中醫教育已經開始成熟,其對近代乃至現代的中醫教育均有深遠影響。
3 近代中醫學課程教材建設的啟示
課程與教材建設是近代中醫學反廢止、求生存努力的重要內容。以圖通過自身符合近代教育規律的變革,能夠加入學校系統得以存亡續絕。這顯然是一種開創性工作,它不同于西醫的課程教材可以直接從外國翻譯借鑒,因此也就決定了中醫學課程教材的建設需要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比較顯現的矛盾就是如何處理好中西醫的關系,包括中西醫課程比例如何分配?教材中中西醫內容如何體現等問題。應該說,對這一問題的處理,近代中醫教育家們的做法還是較為恰當地。
如1928年的統一教材會議,中醫界對教材編輯的指導思想意見分歧很大,《傷寒今釋》作者陸淵雷先生與《包氏醫宗》作者包識生先生各持一端,爭論三日而不能決。陸淵雷是采用西醫理論之激進派,包識生是力主中醫體系保持完整之正統派。但最終還是達成了“整理固有醫學之精華,列為明顯之系統,運用合乎現代的理論,制為完善之學說”的基本原則。
近代中醫課程教材建設的不斷探索,主流是溝通中西。與西醫對待中醫的態度截然相反,中醫藥界的主流并沒有拒絕西方醫學。近代史上沒有一個著名的醫家辦教育時主張完全脫離西醫,搞所謂的純中醫教育。中醫名家謝利恒、惲鐵樵、包識生、張山雷、蔣文芳、陸淵雷、時逸人等先生,大多參與了中醫課程建設和教材編撰。在具體學術觀點上,他們的認識可能有所不同,但在溝通中西醫學上是一致的。
總之,近代中醫界克服政府阻礙、辦學經驗不足等困難,先后興辦了70多所中醫學校。在課程設置上,普遍開設中、西醫學課程;教材建設上,共編寫170多種教材,并進行了統一教材的努力。中醫教育通過自身的變革,逐漸接近近代的教育模式,為建國后中醫藥高等教育的迅速勃興奠定了基礎。
[1] 潘吉星.李約瑟文集[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996.
[2] 張山雷.黃墻朱氏私立中國醫藥學校編制課程商榷意見書[J].中醫教育,198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