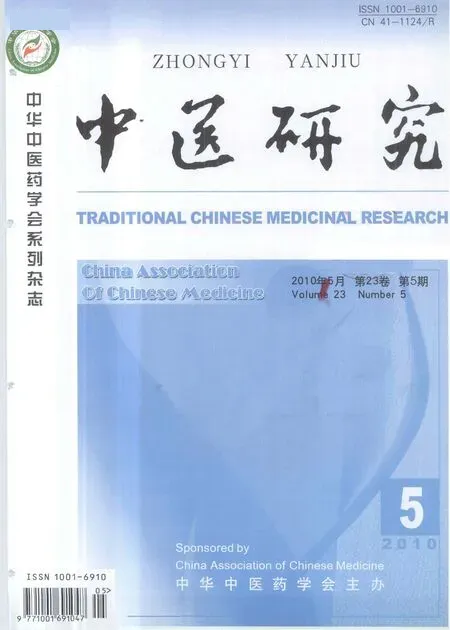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中醫的傳承
潘志麗,潘艷麗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 100700)
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中醫的傳承
潘志麗1,潘艷麗2
(1.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2.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 100700)
田野工作是文化人類學標志性研究方法之一,出現不過百余年時間,卻被廣泛應用于各學科,可見其方法的普適性及原理的實用性。本文通過論述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中醫的傳承,認為文化人類學必將以其整體、客觀的研究方法為推動中醫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文化人類學 田野工作 中醫傳承 /發展趨勢
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由哈登博士最早提出。19世紀末哈登在劍橋大學極力主張有必要依靠有能力的觀察者對各種具體社會進行實地的、系統的和“深入細致”的研究。他提出:為了認識一個原始社會中的任何一個習俗或信仰,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由訓練有素的社會人類學研究者進行田野工作研究,他們的任務不僅僅是簡單地記錄那個社會的生活特點,還包括分析這些特點之間的相互聯系,并解釋它們。哈登組織了劍橋大學赴托雷斯海峽的考察,此次活動被視為人類學田野工作的開始。馬林諾夫斯基為田野工作確立了新的準則,堅持為切實理解當地人的生活而參與他們的生活,并用自己在特羅布里恩德島的工作來證明這一方法。自此田野工作成為人類學家首要的同時也是必須的基本功。如今,田野調查法已經得到社會的認可,并被廣泛應用于各類研究,可以說人類學藉空想起家,由田野發達。
1 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1.1 文化人類學
作為人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人類學“是一門研究、理解人類文化相似性及差異性,進而探討人類文化本質的學科”[1]。文化人類學利用系統的方法觀察或分析文化現象,進行闡釋性的研究,文化人類學正以其兼容并蓄和勃勃生機為愈來愈多的人所重視。中醫學與其努力走實證主義路線期待被西方自然科學研究所承認,不如從自身的歷史出發,找出適合的方法來證實自己的價值,而文化人類學對中醫的發展和完善是有百利的。
1.2 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就是經過專門訓練的人類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 (研究對象),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住居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2]。田野工作是文化人類學最有特色的方法之一,也是搜集資料的基本方法。其實質就是親身實踐,獲取資料。這種資料不是文獻上記載過的,也不是別人已經發現了的,而應是調查者獨自占有的。
2 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比較
2.1 習醫者與田野工作者的必備條件
古代中醫擇徒是有條件的[3],正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為人類學家一樣。《素問·氣交變大論 》中說 :“傳非其人 ,慢泄天寶。”必須得德、才、智兼備之人方能傳授醫術。《史記》載扁鵲“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乃傳其禁方。長桑君因重扁鵲人品教其醫術,而人類學家也必須先贏得土著居民的信任才能進行其工作,這是兩門學科對從業者德行的高標準、嚴要求。《素問·氣交變大論》引《上經》“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久長”言,提出非才高識妙,不能探及中醫的理致。田野工作者首先應具備理論社會學最近發展的全部知識;其次,他應該學會田野工作的技術;再次,他還應該掌握他將去工作的那個文化區到目前為止有關那個文化所能得到的全部知識[4]。可以肯定,優秀的中醫學家或社會人類學家其文化底蘊必是深厚的。
徐大椿在《醫學源流論·醫非人人可學論》中表明醫學之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學。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來,社會人類學家最終的工作是靠歸納形成通則,而這關鍵的一步非伶俐之人不能完成。
2.2 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要素
筆者認為“參與生活”作為主要要素貫穿于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始終。“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生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5]。故中醫學傳承歷來以師徒授受和家傳為主。想學醫必須拜師或順承家技,也就是說學醫者必須先接近醫生,找到高明的老師,并參與其生活。田野工作最初也只是研究非歐洲民族,特別是那些沒有文字記載歷史的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為了研究,學者們要克服困難,融入當地人的生活。所以二者的共同要素是:要獲取資料和信息就必須身體力行,必須去參與實踐。
2.3 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途徑
古代中醫名家在學有所成后多著書立說闡明己見、述至精至妙之理以啟示后人。如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為《傷寒雜病論》,創六經辯證,開臨證先河;李時珍漁獵群書,搜羅百氏,并親臨藥材生長實地,歷時 27載,終成《本草綱目》,集 16世紀以前我國藥物學之大成,造福人民。愛德華·B·泰勒爵士的“泛靈信仰”與 R·R·馬雷特的“泛生信仰”,可以很好的解釋“信仰超自然存在和力量”;列維·施特勞斯在其著名的《野性的思維》中對“理性”概念進行了批判。優秀醫家和人類學家的成就通過其作品體現,著書立說是他們學術觀點的闡述,也是他們對自己工作的總結,從而指導后學。
3 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關系
3.1 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步驟
通過比較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可知,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步驟為:學習——實踐——總結。中醫學對古文造詣要求比較高,高明的醫生其古文功底必深厚無疑,在中醫古籍之外于經史子集均有涉獵,而人類學家在開展田野工作之時也必須進行艱澀的土著語言的學習,此外還要梳理調查地區的歷史,可見“學習”為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首要的、最基本的步驟。“中醫是實踐性醫學,所有的理論經驗都是從臨床實踐中提煉出的,也是為臨床診治疾病服務的”[6],因此中醫傳承離不開臨床實踐,田野工作是較長的時間內人類學家對研究對象的參與觀察與住居體驗,故實踐為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上升為理論精華必經的步驟。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最終結局都是通過思考總結有所體現,習醫者經過前期的學習、實踐得出自己的思想經驗,從而足以名家,另立門戶。人類學家歸納自己的田野工作經歷,著書立說,為自己一段時間內的田野工作畫上完滿句號。
3.2 中醫傳承與田野工作的共通性
美國人類學家 R·M·基辛說:“田野工作是對一社區及其生活方式從事長期的研究。從許多方面而言,田野工作是人類學最重要的經驗,是人類學家搜集資料和建立通則的主要依據。人類學者撰寫的文章和書籍就是在提煉出這些經驗積累的精華,而終究是要指涉到某一民族的特殊經驗。”[7]從這段經典的概括和本文全篇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田野工作與中醫傳承有諸多的共通性:強調前期的學習積累、中期的實踐觀察、后期的歸納總結。
4 結 語
“文化人類學屬于闡釋性研究,目的不是發現真理,而是分析文化現象”[8]。文化人類學要求學者進行田野工作時必須從整體的角度,對其所研究的某種文化元素進行考察。在此過程中必須保持“價值無涉”,不能主觀臆斷“是”與“否”、“科學”與“迷信”,相信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藉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最后由自己觀察的積累做出正確的歸納推理。人類學方法對研究中醫文化現象和中醫理論本質有很大的應用價值,借助于世界上各著名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借鑒他們得出的科學結論、原理,可以重新理解、闡釋中醫文化的根結與中醫理論的本質,從而在剝啄出中醫理論的科學內核同時,建構起中醫學現代化的新的理論體系[9]。
中醫學是古代中國文化的一朵奇葩,造福了我們的祖先,造就了我們的今天,可以說現世的每一位中國人都或多或少的受惠于這門古老的學科。我們有理由、有責任將其發揚而不是摒棄。通過論述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中醫學的傳承,我們可以看到,文化人類學與中醫有太多的交集,文化人類學必將以其整體、客觀的研究方法為推動中醫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1]蔣立松.文化人類學概論 [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7:1.
[2]田兆元.文化人類學教程 [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23.
[3]王東坡.馬燕冬.李宇航.古代中醫傳承師徒標準文獻研究 [J].中醫教育,2008,27(1):64-66.
[4]拉德克利夫·布朗.社會人類學方法 [M].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2:69.
[5]李零.中國方術考 [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27.
[6]趙宏利.從個體角度談中醫 [J].中華中醫藥學刊,2007,25(7):1452-1456.
[7]R·M·基辛.當代文化人類學 [M].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80:21.
[8]馮珠娣,艾理克,賴立理.文化人類學研究與中醫 [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1,24(6):4-9.
[9]馬伯英.人類學方法在中醫文化研究中的應用[J].醫學與哲學,1995,16(2):57-61.
R22
A
1001-6910(2010)05-0009-03
2009-12-10
(編輯 張大明)
·醫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