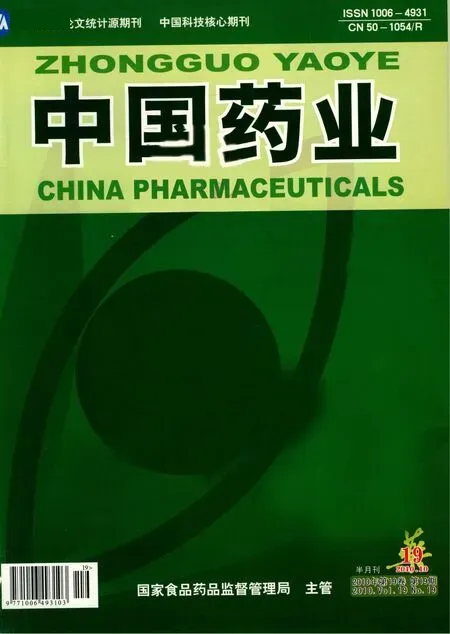甘草酸二銨脂質復合物預防酒精性肝硬化患者抗結核治療致肝損害20例
邱邦東
(四川省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感染科,四川 宜賓 644000)
抗結核治療需要聯合和長療程用藥,且主要抗結核病藥都有肝毒性,治療中常出現肝損害,甚至發生藥物性肝衰竭。我國酒精性肝病的發病率及其在所有肝病中的比例均逐年增加[1]。酒精性肝病患者服用抗結核病藥時肝損害的發生率明顯增加[2],可導致治療不規律,從而引起耐藥和治療失敗。筆者用甘草酸二銨脂質復合物預防酒精性肝硬化患者抗結核治療所致肝損害,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住院的酒精性肝硬化合并肺結核患者37例,診斷符合《肺結核診斷和治療指南》[3]、《急性藥物性肝損傷診治建議(草案)》[4]和《酒精性肝病診療指南》[5]的臨床診斷標準;其中男33例,女4例;年齡29~78歲,中位年齡45歲;均為肝硬化代償期。將37例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17例,治療組20 例,平均年齡分別為(44±16.3)歲和(46±18.1)歲。兩組的年齡、病情及肝功能相似(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及觀察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2HRZE/4HR方案抗結核治療,即異煙肼(H)0.3 g,利福平(R)0.45 g,吡嗪酰胺(Z)1.5 g ,乙胺丁醇(E)0.75 g,均每日1次。對照組加服肌苷片0.2 g,治療組加服甘草酸二銨脂質復合物150 mg,均每日3次。于治療前、治療1個月內每周、治療1個月后每2周檢查肝功能,如出現癥狀及時就診查肝功能。在出現肝損害的患者中,當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或天門冬酸氨基轉移酶(AST)在3倍正常值上限(ULN)以下者,繼續服用抗結核病藥;當患者出現明顯肝損害相關的臨床癥狀,ALT或AST不小于3倍ULN或血清總膽紅素(TBIL)不小于2倍ULN者,則立即停用抗結核病藥。對肝損害的患者均立即加強保肝治療,同時縮短肝功能監測時間,并密切觀察臨床表現。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3.0統計軟件分析,計數資料采用 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 t檢驗。
2 結果
兩組在治療過程中均未見明顯不良反應發生。抗結核治療后,對照組和治療組肝功能損害發生率分別為52.94%(9/17)和20.00%(4/20),ALT或 AST不小于 3倍 ULN的發生率分別為35.29%(6/17)和 5.00%(1/20),治療組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
3 討論
近年來,由于我國對藥物肝毒性的危險性缺乏足夠認識,以及受其臨床表現和診斷的非特異性等因素影響,藥物性肝損害的發病呈上升趨勢,而使用抗結核病藥是主要原因之一[6-7],尤其是對于合并酒精性肝病的患者[8]。其機制可能主要與過敏反應和毒性反應有關。過敏反應所致肝損害與藥物劑量無明顯關系,主要是免疫性損傷。毒性反應與藥物劑量有關,主要是藥物本身或其代謝產物導致肝細胞的變性、壞死或膽汁排泄障礙。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會促進肝損害的發生。同時,在肺結核患者中肝結核的發病常被臨床醫生忽視,而肝結核本身可引起肝細胞的變性、壞死[9-11]。厲有名等[12]對浙江省流行病學的調查結果表明,酒精性肝病的發病率為4.30%,其中酒精性肝硬化為0.68%,由于患者肝臟的各種儲備功能明顯下降,因而在抗結核治療中肝組織負擔加重,促使了肝損害的發生。
甘草酸二銨是甘草有效成分的提取物,具有較強的抗炎、降酶、解毒、促進膽紅素代謝及改善肝功能等作用,其體內代謝產物甘草次酸與類固醇代謝酶親和力大于類固醇,阻礙了體內皮質醇的滅活,從而具有抗過敏以及免疫調節等類皮質激素樣作用,多年來已廣泛應用于肝病的治療。但甘草酸二胺是高極性、親水性大分子物質,口服時腸道吸收較少,生物利用度較低,故影響其療效。甘草酸二銨脂質復合物(商品名天晴甘平,江蘇正大天晴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甘草酸二銨和磷脂酰膽堿形成的復合物,而磷脂酰膽堿不僅是體內必需的磷脂,而且是生物膜的重要成分,與肝細胞膜有較高的親和性,從而提高了甘草酸二銨的生物利用度,同時又具有保護肝細胞膜的作用。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酒精性肝硬化合并肺結核的患者在抗結核治療中使用甘草酸二銨脂質復合物,可預防和減輕肝損害的發生,療效確切,安全性好。由于此類患者抗結核治療中肝損害的發生率較高,而且缺乏特異性治療措施,故需要預防其發生。抗結核治療前,應常規檢查肝炎標志物及肝臟影像學等,并評估肝臟儲備功能;詳細詢問既往肝病史、藥物過敏史以及可引起或促進肝損害的基礎疾病等。對于酒精性肝硬化,在抗結核治療時即使肝功能正常也應同時給予保肝治療,并密切觀察臨床表現以及監測肝功能,特別是在抗結核強化治療階段;應盡量選用肝毒性較小的聯合治療方案;有條件者可行肝活檢,了解肝組織學改變以指導臨床;避免其他加重肝臟負擔的因素;并讓患者知情同意,了解抗結核病藥的不良反應,一旦出現應及時就診。
[1]莊 輝.酒精性肝病的流行病學[J].中華肝臟病雜志,2003,11(11):698.
[2]Fernandez-Villar A,Sopena B,Fernandez-Villar J,et al.The influence of risk factors on the severity of anti-tuberculosis drug-induced hepatotoxicity[J].Int J Tuberc Lung Dis,2004,8(12):1499 -1505.
[3]中華醫學會結核病學分會.肺結核診斷和治療指南[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1,24(2):70 -74.
[4]中華醫學會消化病學分會肝膽疾病協作組.急性藥物性肝損傷診治建議(草案)[J].中華消化雜志,2007,27(11):765 -767.
[5]中華醫學會肝臟病學分會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學組.酒精性肝病診療指南(2006年2月修訂)[J].現代消化及介入診療,2007,12(4):268-270.
[6]許 彪,何衛平,張愛民,等.兩種國際診斷標準對230例藥物性肝損害診斷的分析比較[J].中華肝臟病雜志,2007,15(12):926-929.
[7]劉曉燕,王慧芬,胡瑾華,等.47例藥物性肝衰竭患者臨床分析[J].肝臟,2008,13(5):368 -371.
[8]邱 鳴,杜榮輝.酒精性肝病抗結核方案的選擇[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3,26(9):572 -573.
[9]曹兵生,張 蕊,黎曉林,等.肝結核超聲動態造影表現及其病理基礎[J].中國超聲醫學雜志,2008,24(7):657 -660.
[10]王洪林,陳 翔,李 堅,等.13例肝結核臨床分析[J].中華肝臟病雜志,2006,14(2):108 -113.
[11]常家聰,劉 戈,戚士芹,等.肝結核的病理特征與臨床相關問題探討[J].中國綜合臨床,2003,19(10):928 -929.
[12]厲有名,陳衛星,虞朝輝,等.浙江省酒精性肝病流行病學調查概況[J].中華肝臟病雜志,2003,11(11):647 -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