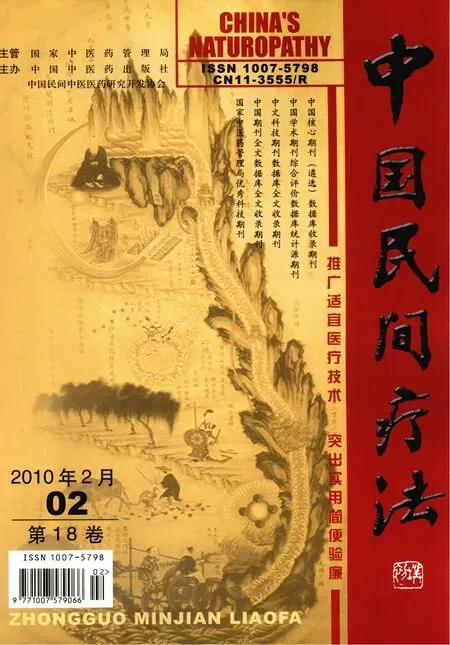活血化瘀法的臨床應用舉隅
劉永軍
(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婦幼保健院,014400)
中醫學認為瘀血是血不歸經,溢于脈外,或停滯于臟腑、體腔,或積留于皮膚、肌肉的一種病理變化,即凡屬于血脈運行不暢或局部瘀血停滯所致的有關病癥均屬于瘀血的范疇。瘀血古亦稱之為惡血,它不但失去血液的功能,而反以為害。
瘀血常見癥狀如下:①疼痛固定,有錐刺感,持續時間較長或有外傷史;②肢體胸腹有異常腫塊,經久不消;③皮膚顏色形成的變化,如紅腫、黯黑、斑塊、粗糙或蛛紋絲縷等;④唇舌的變化,如唇舌青紫或舌面舌邊紫色、紫斑、瘀點;⑤脈象多細澀等;⑥排除:外感,必有發熱、惡寒之表證;積熱,必有舌干口渴;氣虛,似痛不痛及痰飲等癥。
瘀血的治療,《內經》云:“結者散之”,“留者攻之”,“血實者決之”等。醫圣張仲景為活血化瘀的具體應用開創了先河,如《傷寒論》及《金匱要略》中載有不少活血化瘀的方劑:桃核承氣湯、抵當湯治蓄血證;鱉甲煎丸治瘧母;桂枝茯苓丸、當歸芍藥散治婦人病癥;下瘀血湯、大黃蟲丸治腹中干血及經水不利等。又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的失笑散治心腹痛;金代李杲《醫學發明》復元活血湯治從高處墜下,惡血留于脅下,痛不可忍;明代龔廷賢《壽世保元》活血湯治死血腹痛,痛處不移;清代《醫宗金鑒》桃紅四物湯治血瘀所致的月經不調和痛經;陳修園《時方妙用》丹參飲治氣滯血瘀導致的心腹胃脘痛。王清任提出“百病不離乎氣,不離乎血”,著《醫林改錯》,勇于創新,對活血化瘀學說有了重大貢獻,制定了通竅活血湯、血府逐瘀湯、膈下逐瘀湯、少腹逐瘀湯、補陽還五湯等22個治瘀方,其中血府逐瘀湯、補陽還五湯至今仍廣泛應用。唐容川在出血性疾病中有離經未出之血的看法,總結出止血、消瘀、寧血、補血等治療血證的四步之法,為活血化瘀法做了進一步完善和補充。近代名醫張錫鈍繼承發揮前人的經驗,創立了活絡效靈丹,擴大了臨床治療范圍。
在臨床實踐中,我們根據歷代醫家的理論,運用活血化瘀法與其他治則相結合,治療一些確有血瘀的疾病,往往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舉例如下。
溫經止痛與活血化瘀治療絕育術后遺癥
患者,女,32歲,初診日期:1998年 8月 20日。半年前做絕育手術,術后月經半月一行,量多,色黑,有塊,小腹痛拒按,其他醫院診斷為“術后粘連”,經住院治療癥狀緩解,出院后每逢經期腹痛欲死,喪失勞動能力,多方服藥無效,求診。查主癥如前,自述小腹冰冷,舌質紫暗,苔白滑,脈弦。辨證為宮冷血瘀,處以少腹逐瘀湯加減:川芎10g,炮姜10g,延胡索 10g,五靈脂 10g,赤芍、白芍各10g,小茴香10g,蒲黃10g,肉桂 5g,當歸 10g,沒藥10g,牡丹皮10g,烏藥10g,益母草15g,澤蘭葉10g。服上方3劑,諸證明顯好轉,繼服3劑,經停后仍有輕微腹痛,后經上方與歸脾湯加減調治半年,諸證悉除,正常參加勞動。
和解少陽與活血化瘀治療顱腦外傷后遺癥
患者,男,25歲,初診日期:1995年 6月 25日。于1988年因外傷人事不知,5日后始蘇醒,但后遺頭暈、頭痛、煩躁等癥,經中、西醫治療不效,來診。近時犯頭暈、頭痛,頸項拘急且有上沖感,頭痛如刺,常煩躁,心下堵,手足冷,眠差,大便干,舌苔白根膩,舌尖紅,脈弦滑數。辨證屬病在少陽陽明且病久有瘀血,處以大柴胡湯合桂枝茯苓丸加味:柴胡12g,半夏9g,黃芩 9g,枳實9g,大棗 4 枚,生姜 9g,茯苓 9g,桔梗 9g,白芍 9g,大黃 6g,牡丹皮9g,桃仁 9g,石膏 45g。上藥服 3劑,頭暈、頭痛減,心煩躁減,心下堵已,大便如常,上方減石膏為30g,又服3劑,諸癥已。
舒肝解郁與活血化瘀治療精神癥狀
患者,男,48歲,初診日期:2006年6月。因車禍全身多處骨折,住院治療1個多月,出院后全身不適,忽寒忽熱,活動掣痛,動彈不得,心煩失眠,食而無味,悵然不知所措,舌苔少津,不渴,脈細數。辨證屬肝郁血虛血瘀,處以血府逐瘀湯加減:柴胡10g,枳殼10g,生地黃15g,桃仁 10g,當歸10g,赤芍 15g,川芎 10g,紅花10g,川牛膝15g,穿山甲10g,桔梗 8g,生大黃6g。6劑水煎服。藥盡劑復診,患者面帶笑容訴:服藥3劑后,全身如釋重負,再服3劑,上述癥狀若失。
補氣益腎與活血化瘀治療腎病綜合征
患者,男,7歲,初診日期:1993年3月15日。患兒2日前感冒后引起眼瞼浮腫。尿常規:尿蛋白(),白細胞3~5個/HP,經西藥治療后好轉,停藥后化驗尿蛋白如前,經某市醫院診為“腎病綜合征”。服潘生丁、強的松、消炎痛、VC等藥,治療時好時壞,要求中醫診療。當時強的松20mg/日口服。患兒面色白,輕度浮腫,尿蛋白(),舌質淡,脈弦細。辨為腎陽不足,氣虛不能攝精,初以補腎益氣之藥,服10余劑不效。沉思良久,細查舌邊紫暗,應有血瘀,調整處方如下:山茱萸10g,蓮須 10g,山藥 15g,牡丹皮 10g,丹參 20g,赤芍10g,茯苓 10g,生黃芪 15g,白茅根 15g,澤瀉 10g,熟地黃15g,陳皮10g,紅花 10g,坤草15g。上方加減服藥 2月余,同時撤減強的松用藥,前后調治半年,一切如常,隨訪5年未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