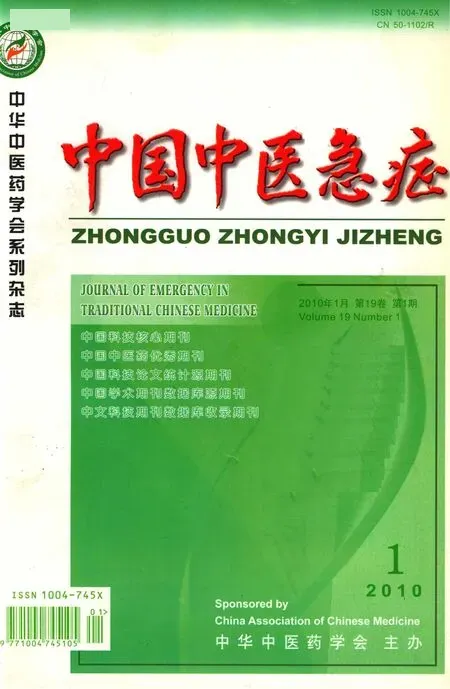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治驗1則
宋聯進 王宗仁 馬 靜 郭炳華
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西安 710032)
1 病例
患某,女性,67歲,退休。因“口腔、鼻腔及皮下出血1d”為主訴,于2007年11月26日入住血液科。血常規示:血小板8×109/L;骨穿確診為特發性血小板減低。入院后予丙種球蛋白沖擊,白介素11、長春新堿等治療,血小板無顯著回升,出血傾向明顯改善,遂出院。2008年1月患者再次出現皮膚粘膜、口腔內廣泛出血,高熱39.5℃,伴有頭痛、咽痛、輕微咳嗽,刷牙時牙齦出血明顯,血常規示:紅細胞、白細胞、血紅蛋白均正常,血小板5×109/L,遂再次入院。予抗感染、止血、大劑量丙種球蛋白、激素等治療,血小板稍有回升,出血傾向再次改善。停用丙種球蛋白、激素減量后,血小板再次降低,出血傾向加重,遂再次予丙種球蛋白沖擊,白介素11、長春新堿、環孢素等藥物治療,出血傾向得到明顯改善,遂出院。出院后每日口服強的松40mg、環孢素A100mg維持治療。后又因血小板反復減低(最低為3×109/L),多次住院行沖擊治療,血小板可稍升高,但停用沖擊治療后,血小板即急劇下降,后轉入中醫科。
癥見面如滿月,四肢針尖大小瘀斑,色澤鮮紅,壓之不褪色,五心潮熱,咽干口燥,渴喜冷飲,尿黃便干,脈弦數,舌紅絳苔薄黃。辨證為血熱妄行。在治療上予以甲強龍80mg靜脈滴注,丙種球蛋白20g靜脈滴注,連續7d,并輸入200mL新鮮血小板等,但均未有效升高血小板計數。予犀角地黃湯、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加味,血小板回升至60×109/L,但不穩定,其間因不明原因血小板又驟降至6×109/L,伴隨手、足、胸腹部皮下出現散在紫癜,壓之不褪色;遂予新鮮柿子葉30g,山藥30g,枸杞15g,每日煎湯3次,服用半月后血小板漸增,并逐漸激素減量服用1月后,血小板回升至75×109/L,遂出院,繼服上述中藥,并停用一切與治療血小板減少相關的藥物。繼服上方1月,于2008年11月復查,血小板穩定于95×109/L,期間血小板最高回升至127×109/L。隨訪2月,復查血小板正常,2009年1月27日血小板為133×109/L。
2 體會
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ITP)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自身抗血小板抗體致血小板在脾臟等部位破壞過多而引起骨髓巨核細胞成熟障礙、外周血小板減少的出血性疾病,其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明了,目前認為,主要與體液免疫紊亂和細胞免疫紊亂有關。臨床以全身皮膚、黏膜或內臟廣泛出血為主要表現。目前國內外仍無特效治療方法,激素療法、丙球療法等對部分病例有效,或者用藥時化驗指標上升,減量或者停藥時化驗指標下降,甚至用藥時也不上升且副作用大,藥價昂貴。
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屬中醫學“發斑”、“血證”范疇。本病可因外感邪氣,絡脈受傷,致血不循經;或熱邪傳里,胃熱熏蒸以及過食辛辣酒漿致胃中伏熱,熱邪擾動陰血,血液溢于肌膚;亦可因勞倦內傷,病后體虛而脾氣受傷,血失統攝,溢于絡脈之外。病因系素體陽熱偏盛,飲食辛辣,情志內郁,或兼感陽熱之邪,以致熱迫損絡而發斑者,此屬實證;抑或內熱傷陰,虛火損絡,或勞倦傷脾,氣不攝血而致血溢絡外者,此屬虛證。虛實之間可互相轉化。病因有外感、內傷之分。一般以出現在溫熱病當中由熱郁陽明迫及營血所致者稱“溫病發斑”。然亦有因內傷所致者,如明·李梃在《醫學入門》中所述“內傷發斑,輕如蚊跡疹子者,多在手足,初起無頭痛身熱,乃胃虛火游于外”與本病相類似;《血證論》亦謂“血證,氣盛火旺者十居八九。”
本例患者長期獨居復加抑郁,心肝火熱內熾,迫血溢于肌膚,發為紫癜。此外,患者接受半年多糖皮質激素治療亦是本病血熱辨證的重要依據。多數學者認為,皮質激素乃 “純陽之品”、“陽熱之品”、“燥烈之品”,可鼓舞人體陽氣[1];激素的副作用與其陽剛之性有關[2]。激素對于陽虛者治療有效率遠高于陰陽兩虛及陰虛者,這亦可反證出激素乃為陽剛燥熱之品。因此患者雖用清熱方藥,但效果不明顯。查閱文獻及方書,結合患者病情,以鮮柿子葉、山藥、枸杞煎服,用后顯效明顯。柿葉具有下氣平喘、止渴生津、止血、療瘡等功效,并具有止血和免疫調節功能[3]。臨床上應用柿子葉治療血小板減少性紫癜亦有報道[4];山藥具有益氣養陰、補脾肺腎之功,能提高淋巴細胞轉化功能,對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功能有較強的促進作用;枸杞為滋補肝腎、養血補精之良藥。三藥合用,初診即有顯效,繼續服用原方,逐漸停用激素,紫癜告愈,追蹤患者3月,病情穩定。
[1]張文康.中西醫結合醫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0:711.
[2]葉任高.腎病綜合征的中西醫結合治療[J].江蘇中醫,1999,20(11):3~4.
[3]王樹松.柿葉的研究進展[J].河北中醫,1998,20(1):63~64.
[4]郭玫,董曉萍,徐文萍.柿葉的研究概況[J].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000,17:78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