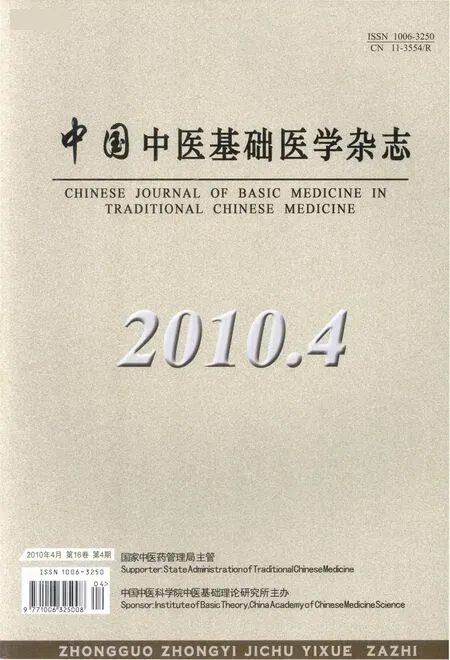近二十年對中醫脾生理功能的現代研究進展*
陳素美
(河南中醫學院,河南鄭州 450008)
中醫的脾在具體臟器上一直沒有明確的定義,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現在解剖學上的脾臟、胰臟或脾與胰。中醫的五臟強調的是功能集團,與神經、內分泌、血液循環、免疫、泌尿、生殖、運動等各系統均有密切聯系,目前還不能一一對應到形態學上,但是關于中醫脾生理功能的研究仍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中醫概念的脾之生理功能包括主運化水谷精微和水濕、統攝血液、主四肢和肌肉等,現代研究又提出了脾主藥動力學的觀點。筆者查閱了近20年的相關文獻,現根據脾的生理功能分述于下。
1 脾主運化
脾主運化包括運化水谷和運化水濕,而研究的主要方向在運化水谷方面。從以往的研究來看,脾運化水谷在現代醫學中主要有4個方面:消化、吸收、胃腸運動代謝、胃腸道激素。徐華[1]等認為,在消化方面,中醫學的脾和西醫學胰的功能密切聯系。胰外分泌部分分泌的胰液含有水解食物中3種主要成分糖、脂肪和蛋白質的消化酶,因此在所有的消化液中是最重要的1種。臨床和實驗均證明,當胰液分泌障礙時,即使其他消化腺分泌都正常,食物中的脂肪和蛋白質仍不能完全被消化,從而影響其吸收。胰腺外分泌功能異常,可引起胰源性腹瀉、消化功能不良、腹水、腹痛、黃疸、發育遲緩、消瘦等與中醫脾陽虛癥狀相似:泄瀉或完谷不化。胰腺內分泌功能異常,可引起食多、飲多、小便多、身體消瘦等糖尿病癥狀及心悸、出汗,這與中醫脾陰虛中癉者消渴相似。脾與胰臟的病理對應在現代研究中亦得到印證。金敬善[2]等實驗表明,脾虛患者胰功肽試驗低于正常,尿淀粉酶活性亦降低,提示脾虛患者胰腺功能下降。吸收方面,王建華等[3]發現,脾虛患者結腸黏膜上皮細胞微絨毛稀疏、倒伏,長短不一,排列紊亂,相互黏連,部分微絨毛退變,末端腫脹呈鼓槌狀,有的甚至溶解、斷裂、脫落而成為足狀突起,微絨毛表面的細胞衣大部分脫落,部分微絨毛軸心微絲及基底部終末網消失。胃腸運動代謝方面,王建華等[3]進行了390例胃電圖及282例微電腦胃電頻譜分析,結果表明脾虛患者餐后胃電波幅參數(胃電圖波幅、胃電優勢頻率相應幅值、胃電頗譜慢成分活動量)明顯低于正常對照組。同時連至誠等[4]還開展了體表結腸電的研究,發現脾虛患者空腹結腸電圖頻率范圍都低于正常人,提示空腹結腸非推進性運動和升結腸逆蠕動減弱。另外,脾虛患者的X線表現[5]以胃腸功能紊亂的X線征象為其特點,還表現為胃下垂、胃張力低、蠕動弱等X線征象。胃腸道激素方面,張桂珍[6]等通過免疫細胞化學及體視學定量分析方法,觀察了89例胃十二指腸病脾虛患者的胃竇G細胞變化,與空腹血清胃泌素含量進行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脾虛氣滯型患者胃竇G細胞數密度及空腹血清胃泌素含量明顯高于脾胃氣虛組和正常對照組,胃竇G細胞數目與空腹血清胃泌素含量呈顯著正相關,脾胃氣虛組空腹血清胃泌素值雖稍高于對照組,但變化不明顯。鄭揮年等[7]亦發現,脾虛組患者G細胞數較實證組明顯減少。同時還發現,脾虛組患者D細胞(生長抑素產生細胞)數亦較實證組明顯減少,但C/D比值明顯增高。張忠兵等[8]用放射免疫技術對30例脾虛泄瀉患者回腸末端、橫結腸和乙狀結腸黏膜中P物質(SP)和血管活性腸肽(VIP)進行測定,發現脾虛泄瀉組回腸末段SP含量較無腹瀉組和非脾虛泄瀉組顯著增加,脾虛泄瀉組乙狀結腸黏膜VIP含量較無腹瀉組也顯著增加。
因從食物可被人體吸收的營養物質和各種酶參與其中,陳繼業[9]等提出脾不主運化、酶主運化的觀點。在血液中葡萄糖等流過組織時進入胞液中,再經過多種酶的作用變為丙酮酸,最后在氧存在下在線粒體內,同樣通過酶的作用生成 ATP、H2O、CO2;其他參加能量轉換的脂肪酸及氨基酸進入三羥酸循環亦依靠酶,轉變為丙酮酸亦依靠酶進行能量轉化。而已知微量元素鋅與人體80多種酶的合成和代謝有關,銅是生物體內40多種酶的活性成分,所以鋅銅對糖類、脂類、蛋白質和核酸的代謝過程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也與脾主運化的功能密切相關。人體缺銅引起的皮膚色素減少、厭食、腹瀉、精神發育遲緩等癥狀以及缺鋅出現的食欲減退,甚而厭食和因營養不良而呈現的一些臨床癥狀,與脾虛納化失職所出現的食欲不振、神疲微言、面色不華、大便溏泄等癥狀表現也十分類似。焦君良[10]等測定了41例脾胃虛寒患者血清鋅銅含量和50例正常人相比,可見脾胃虛寒證血清鋅銅顯著降低,在應用溫陽健脾藥治療后,隨著脾的溫運功能提高,脾胃虛寒癥狀的改善,患者血清鋅銅的異常也得以糾正,提示這些微量元素在生理病理變化及治療轉歸等方面均與脾的健運功能有密切關系。
2 脾主統血
中醫學的脾主統血是指脾具有使血液在脈中正常運行并防止血液向脈外溢出的統攝(制約)作用,脾是否能統攝血液,全賴于脾氣固攝作用。“脾主統血”理論源于《難經》“脾裹血”的論述。可能古人在祭祀或解剖人或動物脾臟時,發現脾竇富含血液,由此推理而來。從現代解剖學角度來看,脾內血管豐富,血液充盈,“脾裹血”是從脾的解剖形態結構特征方面來描述的。近年研究發現,脾主統血的功能與凝血因子及微循環密切相關。
2.1 凝血因子
在止血機制中起著最重要作用的血小板有1/3位于脾臟,脾臟腫大時大約有90%停留于脾臟。徐重明[12]對脾虛、脾不統血者進行了血小板功能及超微結構形態的觀察,發現這類病人的血小板數量基本正常,但由于機體能源物質不足及利用障礙,特別是蛋白質代謝障礙,使血小板的膜糖蛋白Ⅰ、Ⅱ、Ⅲ及骨架收縮蛋白中的d-輔肌動蛋白和肌動蛋白結合蛋白生成減少,結構變異,造成血小板黏附、聚集、收縮功能下降,血小板對毛細血管的支持、營養作用降低,毛細血管脆性增加,導致出血。沈迪[13]亦發現,脾不統血證反復出血的發病機制,半數病例可能與血小板聚集功能缺陷有關。由于脾虛、脾不統血者多正氣虛,故亦有不少以免疫為角度的研究。章梅等[14]對利血平造模的小鼠進行腹腔巨嗜細胞吞噬功能和紅細胞免疫功能的測定。發現脾虛時紅細胞C3b受體水平下降,提示紅細胞介導的清除循環免疫復合物及免疫黏附功能下降,造成循環免疫復合物增多,沉積于很多組織器官,固定血小板、補體并與其受體發生炎癥反應。危北海[15]對ITP(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患者的免疫功能進行觀察,發現患者的免疫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通過對治療前后抗血小板抗體IgG的動態觀察,并對其全血淋巴細胞轉化進行測定,發現其治療后的抗血小板抗體水平及淋巴細胞轉化率均顯著改善。田維毅[16]發現,脾不統血型ITP模型小鼠的紅細胞免疫功能明顯低于正常,加減歸脾湯大劑量組能使其紅細胞免疫功能恢復正常。楊宇飛[17]認為,ITP多見于育齡期女性,且發病率男女比例為1∶3,推斷本病因此時婦女雌激素水平較高,“亢則害”,抑制胸腺分化,減弱對脾免疫系統的抑制,使脾體液免疫亢進,產生過多抗血小板抗體而發病。張朝陽[18]等對97例ITP患者(包括脾不統血、血熱妄行、脾氣虛弱型)進行了PAIgG、PAIgM、PAIgA 3項免疫學指標的測定。結果顯示,同為 ITP,脾不統血組 PAIgG、PAIgM 2項指標明顯高于脾氣虛弱組,說明脾不統血致脾氣虛弱的發展和加重,從免疫學角度驗證了脾統血的生理功能是通過氣攝血來實現的。
2.2 微循環
出血相關因素除了凝血因子之外,還有血管本身的因素。馬宗林等[19]對44例脾虛證患者進行了健脾方藥治療前后的甲襞與舌微循環對比觀察。結果表明,脾虛證存在明顯的外周微循環障礙,脾陽虛與脾陰虛組的甲襞與舌微循環加權總積分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0.001)。其主要表現為:①管袢形態方面的改變。包括清晰度下降,管袢數減少,異形管袢明顯增多;②血液流速減慢,有輕至中度紅細胞聚集;③袢周可見輕至中度明顯滲出,甲襞有少數管袢出血。經健脾方藥治療后,外周微循環復查表明,甲襞與舌微循環障礙亦得到明顯改善,而以甲襞微循環的改善更為明顯。楊建華等[20]報告了34例脾陰虛證患者的血液流變學有關指標及微循環狀態檢測結果,表明脾陰虛證患者的血液流變學主要改變為全血比黏度、血漿比黏度、紅細胞硬化指數增高、血沉增快,處于濃、黏、聚的狀態;而脾陰虛患者的甲襞微循環改變與馬宗林報告結果一致,揭示了脾陰虛與宏觀、微觀血瘀證的關系。瞿德[21]綜合文獻報道發現,脾氣虛證和脾不統血患者較正常人和實證患者普遍存在紅細胞壓積減低、血沉增快現象、血液呈低黏性和低壓積狀態,且脾不統血組較脾氣虛組改變更為明顯。包力等[22]觀察了利血平與飲食失調型脾虛大鼠模型的腸系膜微循環,并對其腸系膜微血管進行了電鏡形態學觀察,發現其超微結構出現了明顯的異常改變,主要表現為內皮細胞圓形腫脹,突出于血管內壁;內皮細胞基底層可見多數大空泡形成,內皮下基底膜結構破壞消失;血管壁平滑肌細胞腫脹。提示脾虛大鼠的腸系膜微動脈內皮細胞出現缺氧、細胞損傷的現象,提示可能是脾虛證微循環障礙的前趨表現。喻寧芬[23]報道過敏性紫癜患兒存在明顯高黏滯血癥,其形成可能與高免疫球蛋白和炎性介質的釋放有關,導致了組織缺氧,PGI2/TXA2平衡失調,從而使血管強烈收縮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強,最終表現為出血。
3 脾主肌肉及四肢
脾主肌肉及四肢是說明人體肌肉的豐滿以及四肢的正常活動,都與脾的運化功能有密切的關系。廣州中醫藥大學劉友章教授[24]早在80年代,就率先提出了脾主肌肉與細胞線粒體有密切的關系。在進行研究中發現,六君子湯對受損傷的線粒體有保護作用,在進行國家“七五”攻關課題“脾虛證候機理研究”中,對脾虛證患者胃黏膜細胞線粒體變化進行電鏡觀察,首先報道了脾虛病人胃黏膜壁細胞線粒體數目減少、超微結構受損、能量代謝障礙,提出了中醫脾-線粒體相關學說。指出中醫脾主運化不僅僅是指食物在胃腸的消化吸收,更重要的是營養物質在線粒體的生物氧化產能過程,首先把脾胃研究深入到亞細胞水平。線粒體通過三羧酸循環和氧化磷酸化、氧化三大營養物(水谷精微)生成ATP(氣),并且還利用琥珀酸單酰CoA與甘氨酸合成血紅素(“血”),因此線粒體(脾)是“氣血生化之源”。現代研究表明,線粒體是細胞凋亡的重要環節,有人甚至認為它是細胞凋亡的充分和必要條件。如果大量細胞的線粒體腫脹、破潰,則引起該器官或系統功能的衰竭,即所謂的“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之后對脾主運化、脾主肌肉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脾氣虛時具有骨骼肌的形態變化特點。楊維益[25]等研究發現,脾氣虛大鼠骨骼肌肌纖維明顯變細。根據Ⅰ型纖維和Ⅱ型纖維骨骼肌細胞的平均截面積(A)測量,脾氣虛組大鼠兩種肌纖維的A均下降,其中Ⅰ型纖維較對照組下降了33%,Ⅱ型纖維下降了67%。通過服用健脾益氣類藥物復健后,肌纖維A增加,說明肌纖維的蛋白質分解以Ⅱ型纖維為著。骨骼肌蛋白質的分解增強,反映了在脾氣虛狀態時,機體的代謝異常不僅表現在能量代謝方面,也影響到蛋白質的物質代謝,使肌肉組織的蛋白代謝呈負平衡狀態。骨骼肌的上述病理改變,是脾氣虛時肌肉不耐疲勞和劇烈運動的原因之一。而線粒體是細胞生物氧化的主要場所,骨骼肌收縮活動所需能量與線粒體密切相關。李樂紅[26]研究發現,脾氣虛動物模型的骨骼肌線粒體的形態與數量發生異常改變:伴隨著肌原纖維間線粒體的數密度減少,線粒體的體密度增加;線粒體數量減少,大小不一,腫脹(可為正常線粒體的數倍),嵴部分或全部消失,基質透明,甚或溢出線粒體外,線粒體外膜結構破壞等;經健脾益氣類藥治療后,其結構恢復接近正常對照組,說明“脾氣虛”所致肌肉失養的病理機制之一為骨骼肌線粒體結構損傷,從而影響骨骼肌的有氧代謝,也顯示了健脾益氣類藥物具有縮短脾氣虛證時損傷的線粒體修復時間的作用。王淑娟[27]研究發現,脾氣虛大鼠小終板電位、乙酰膽堿電位的振幅明顯低于正常大鼠,但其小終板電位頻率及乙酰膽堿電位時程無明顯變化,提示脾氣虛時神經-肌肉接頭傳遞障礙,其障礙可能發生在神經-肌肉接頭的觸突后膜。
一些研究表明,脾主肌肉與一些微量元素密切相關。當今生物學的研究證明,肌肉的生成和鋅銅關系密切。人體內的鋅主要是通過參與DNA聚合酶、RNA聚合酶、胸腺嘧啶核苷激酶、乳酸脫氫酶等重要酶的合成來影響肌肉組織的生長和再生;銅參與細胞色素氧化酶、賴氨酞氧化酶的合成和代謝。缺銅后這些酶的活性降低,彈性蛋白與膠原纖維中共價交聯形成障礙,膠原及彈性蛋白成熟遲緩,從而影響組織的修復和再生,而“脾主肌肉”功能的發揮是以鋅銅的生理作用為基礎的。周平禎[28]對臨床135例病人研究發現,脾虛肌瘦乏力組低鈉、低鉀明顯高于脾虛無肌瘦乏力組,而脾虛無肌瘦乏力組低氯則高于脾虛肌瘦乏力組。認為鉀、鈉、氯可能是脾與肌肉之間聯系的一種物質基礎,低鈉可能是脾虛產生肌乏力的主要內在因素,也是脾胃氣虛、肌肉消瘦、疲乏無力可供參考的客觀指標。
4 脾主藥動力學
在脾主運化的基礎上,黃熙[29]等進一步提出脾主藥物動力學假說,即假定中醫的“脾”主管藥物的吸收、分布、代謝和排泄(PK),也包括脾失健運下的PK。1991~1995年期間研究發現,脾虛大鼠與非脾虛大鼠的川芎嗪(TMPP)PK特征不同,前者表現為TMPP在體內的空間處置狀態由雙室變為單室模型,藥物濃度值增加,血藥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增強,且與脾虛時所表現出的血液流變學、腸道菌群等異常改變有關。1997年又進一步發現脾虛大鼠異常的TMPP的PK特征與脾虛大鼠血漿和腸組織中胃動素(MOT)的含量異常有關,補脾經典方四君子湯對此有調整作用。胃腸動力學、腸道菌群及酶系統等是影響PK的主要機體因素,而這些因素與脾虛失于健運的關系尤為密切。脾虛失于健運存在著的胃腸動力學障礙、腸道菌群失調、酶系統的改變等,都將影響藥(食)物在體內的吸收、分布、代謝與排泄過程。需要指出的是,此假說仍在驗證中,尚不能下定論。
5 結語
中醫脾作為十分重要的臟器——后天之本,其生理功能的發掘從古至今被不斷地研究和發展著,在現代醫學中,不僅找到了相關聯的生物學基礎,更從新的角度加以升華,盡管研究還在進行中,一些結論的提出尚需時日,但筆者相信,隨著新技術的發展,中醫脾的功能將被更深刻而清晰地認識。
[1]徐華,等.現代醫學對中醫脾的認識[J].中醫藥通報,2008,7(6):17.
[2]金敬善,等.老年人和脾虛患者消化系統功能的觀察[J].中西醫結合雜志,1994,4(3):164.
[3]王建華.脾主運化的現代研究進展與展望[J].廣州中醫學院學報,1991,8(2-3):248-249.
[4]連至誠,等.體表結腸電檢測分析方法的基礎及應用研究[J].廣州中醫學院學報,1990,7(3):170.
[5]孟慶學,等.脾胃虛證的X線分析[J].陜西中醫,1995,16(4):192.
[6]張桂珍,等.脾虛證患者胃竇G細胞體視學定量分析[J].中西醫結合雜志,1989,9(12):711.
[7]鄭揮年,等.脾虛證胃痛與胃竇黏膜G和U細胞關系(摘要)[J].中西醫結合雜志,1990,10(1):33.
[8]張忠兵,等.脾虛泄瀉患者腸黏膜中SP和VIP初步探討[J].中西醫結合雜志,1991,11(3):144.
[9]陳繼業,等.脾主運化,抑酶主運化?——論中醫藏象理論脾的功能[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6,15(15):2029-2030.
[10]焦君良,等.試論中醫的“脾”與微量元素鋅、銅的關系[J].陜西中醫學院學報,1993,16(1):11-12.
[11]金容辰,等.對脾生理功能的中西醫學比較研究[J].天津中醫藥,2006,23(1):76-77.
[12]徐重明,等.脾虛證與血循環關系研究[J].河北中醫,1997,19(3):2-3.
[13]沈迪,等.脾不統血證血小板聚集功能的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01,9(1):5-7.
[14]章梅,等.脾虛小鼠紅細胞免疫和腹腔巨噬細胞吞噬功能改變的實驗研究[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9,22(3):26.
[15]危北海.脾胃學說研究思路和方法[J].中醫雜志,1985,26(5):69.
[16]田維毅,等.加減歸脾湯對脾不統血型ITP小鼠紅細胞免疫功能的影響[J].貴陽中醫學院學報,2002,24(4):53.
[17]楊宇飛,等.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動物模型組織病理學改變性別差異的探討[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6,2(2):19.
[18]張朝陽,等.紫斑脾不統血患者血小板相關抗體的實驗研究[J].中國中醫急癥,1996,5(3)131.
[19]馬宗林,等.脾虛證外周微循環對比觀察[J].遼寧中醫雜志,1995,22(10):437.
[20]楊建華,等.脾陰虛證與微觀血瘀證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1996,16(2):94.
[21]瞿德,等.脾不統血證的現代研究概況[J].河北中醫,2001,23(8):640.
[22]包力,等.脾虛大鼠模型的腸系膜微循環及微血管超微結構改變[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5,1(2):31.
[23]喻寧芬.過敏性紫癜的預后及治療進展[J].國外醫學·兒科分冊,1994,(21):74.
[24]周俊亮,中醫脾與線粒體關系探討[J].遼寧中醫雜志,2006,33(3):287.
[25]楊維益,等.脾氣虛證大鼠骨骼肌的形態學和形態計量研究[J].中國運動醫學雜志1993,12(3):157.
[26]李樂紅,等.“脾氣虛”大鼠骨骼肌細胞化學研究[J].中國醫藥學報,1990,5(5):1.
[27]王淑娟,等.脾氣虛大鼠肌電圖及運動神經傳導速度的變化研究[J].遼寧中醫雜志,1998,25(9):441.
[28]周平禎,等.脾主肌肉與.K+、Na+、Cl-關系的探討[J].江西中醫藥,19956(增刊):4-5.
[29]黃熙,等.論“脾”主藥物動力學[J].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2000,2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