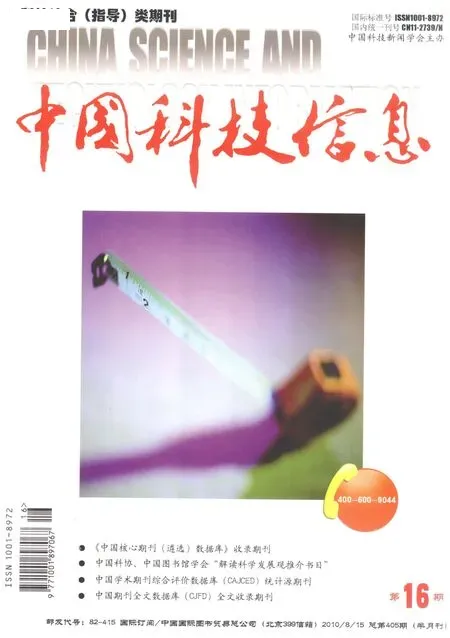中國和歐洲文化中對山羊內涵的認知差異
曾俊敏 廣州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510006
中國和歐洲文化中對山羊內涵的認知差異
曾俊敏 廣州中醫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510006
文化負載詞如動物詞匯的內涵差異研究一向是跨文化交際研究中的關注點之一。本文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對山羊這一較少為人所關注的動物形象在中、歐兩大文化認知體系中的內涵意義進行統計研究,并試圖探討其差異背后的原因,力求能進一步充實、豐富跨文化動物類詞匯文化內涵差異之研究。
山羊;文化內涵;差異;中國文化;歐洲文化
一、緣起
“祥和如意”等五只小山羊是2010年即將在“五羊城”廣州召開的第16屆亞運會吉祥物。然而,不少人大約并不清楚山羊在跨文化交際中其實是一個容易引起誤會的角色。
眾所周知,文化負載類詞匯如動物類詞匯一向為跨文化交際學所關注,因為各異的文化背景往往賦予了同一種動物迥乎不同的文化內涵。所謂內涵(connotation),是Leech所列的七種語義類型之一,指的是附加性的尤其是與情感相關的意義,而文化內涵是內涵義中與文化背景關聯密切的一類(參Xu 2004:129),可以定義為詞匯指稱意義之外受文化背景制約產生的附加(情感性)意義。常見文化內涵有別的詞匯例如中文的“狗”與英文的“dog”在褒貶暗示上就大相徑庭。但實際上動物類文化負載詞的研究多局限于龍、狗、喜鵲、馬、牛等幾種,而從跨文化交際來說,其實需要對所有常見的動物名詞都進行窮盡式研究,使其系統化,因此仍有不少漏網之詞值得深挖,山羊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本文不提“中英”而提“中歐”,是因為歐洲盡管由日耳曼、斯拉夫、拉丁等幾個子文化系統組合而成,但由于歷史、地理、宗教等原因,歐洲文化實際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共核。隨著歐盟的角色越發重要,歐洲整體作為一個跨文化交際參與方的情況日益增多,因此本文將對比雙方定位為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
二、文獻回顧
目前未見研究山羊在中、歐文化中內涵差異的專文,但有部分論著零星提及山羊在某一文化中的含義。
歐洲方面的論著大多與宗教相關,如埃及學家M. Murray(1933)提到歐洲在前基督時期存在“角神”(Horned Gods)崇拜,山羊神即其中之一。而角神崇拜在基督教傳入歐洲之后被妖魔化了。R. D. Levy(1998)則討論了圣經中作為邪惡方的阿撒瀉勒(Azazel)與山羊之關系及其象征。歐洲文化中的山羊內涵往往和宗教負面意義相關,民間故事也透露了這一點,如巴斯克傳說Izaro和Lanjoo的故事中就提及女巫們到Akelaro山朝拜撒旦的情景,而撒旦的形象正是一只寶座上的山羊(Boulton 1993:205-210)。
中國方面的研究多從圖騰、語言文字學等方面切入,典型應推劉毓慶(2002:316-332)。劉文對中國文化中“羊”圖騰及其內涵意義的發展有詳細描述,從中可看出中國文化中“羊”多具有吉祥意義。但劉文并不區分山羊、綿羊,這是國內同類研究的典型特點,因漢語中往往以上位概念“羊”統攝兩者,而“羊”概念于歐洲語言中并不存在,這使得國內外這方面的研究對象有所出入,影響了結果的準確性。不過其他文獻也多傳達出山羊的正面信息,比如裴氏《廣州記》和宋代《太平御覽》中都記載了著名的五仙人乘銜穗之山羊降臨廣州的傳說。
概言之,中、歐文獻中雖對山羊的內涵已有論及,但未見從跨文化角度進行比較研究的,且多為文獻梳理,未見實際調查。因此本文擬以問卷方式對中歐山羊內涵差異作一初步調查并探究其成因。
三、方法論與數據收集
基于相關文獻中山羊含義的統計收集,問卷設計假設中國方面山羊具正面含義,而歐洲文化中正相反。問卷中共羅列了33個特定的內涵義項,均系根據已有研究材料及各類歐洲語言詞典中相關條目統計而來。調查對象除從中選擇自己認可的項外尚可補充未曾列出者。
調查對象方面,中方主要為各地非外語專業的漢族學生,而歐方主要為非中文專業的學生,歐方受調查族群包括日耳曼(英、德、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佛蘭芒語區)、拉丁(法、意、西、葡、羅馬尼亞)和斯拉夫(俄、烏克蘭、波蘭)三大塊,此外尚有愛爾蘭、布列塔尼、立陶宛等小點。由于調查對象語言的復雜性,問卷分為中文、英文和Esperanto三種版本,中文版直接由國內各目標點聯絡人復制后進行調查,兩個外文版本交由各受調查點聯絡人譯成當地語言再進行,如波蘭由J. Myzik負責對華沙一帶的學生進行隨機調查。聯絡人對調查結果整理后發回給筆者進行匯總。問卷調查系于2009年11月發放,2010年5月基本回收完畢。
四、調查結果及比較分析
中國方面共回收177份問卷,結果顯示排在前七項的內涵意義分別是(括號內百分比為選擇該項的人數與問卷回收總數之比):善良(78.53%)、誠實(70.62%)、溫柔(62.15%)、正直(52.54%)、堅韌(40.68%)、吉祥(42.94%)、年高德劭(18. 64%)。
歐洲方面共回收168份問卷,其中50份來自日耳曼地區,62份來自斯拉夫地區,47份來自拉丁地區,余下9份來自其他地區,基本覆蓋歐洲文化主要的子文化區。結果顯示排前七項的內涵意義分別是:壞人(60.71%)、好色(60.12%)、替罪羊(57.14%)、愚蠢可欺(52.38%)、愛破壞(43.45%)、與邪惡的撒旦魔鬼相關聯(40.48%)、執拗固執(35.71%)。
由上可見,中國文化中山羊的內涵確實傾向于正面積極的意義,而歐洲文化中則多為負面意義。具體來說,中國文化中山羊的正面涵義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與優良品格相關如善良、誠實、溫柔等,二是與長者相關如年高德劭,三是與幸運相關如吉祥。而歐洲文化中山羊的負面涵義也可分為三類,一是與性欲有關如好色,二是與不良品格相關如壞、愚蠢、固執等,三是與宗教相關如魔鬼撒旦、負載人類罪惡的替罪羊等。
調查結果也顯示,山羊的內涵意義其實也在變化之中,如中國五羊傳說中隱含的山羊與仙人相關這一內涵僅有7.34%,無法進入前列;歐洲“山羊”曾具有的濃厚宗教內涵也已有所淡化,甚至有2.98%受調查者直接聲稱山羊就是一種動物而已,否認其具有任何內涵意義。
五、中歐山羊內涵差異成因探討
中國文化中山羊的正面內涵成因復雜,筆者認為首先應歸因于中國文化“比德自然”“比類取象”思維模式的影響。這兩種模式反映的是建立在類比推理基礎上的中國式認知與評價體系。儒家通過將“天”與“人”在外在形貌與內在道德上進行類比,建構起天人一體、天人相應的宇宙觀,因此中國文化中屬于大自然的動物每每獲得道德層面的評價,如“烏反哺,羊跪乳”“狐死首丘”等皆此類;具有相似外形特征的物與人也常相援引類比,這在中國傳統十分常見,如山羊因其胡須而與老者“比類”,華夏尊老敬老的文化因而連帶影響了人們對山羊的情感;在道教傳統中,山羊更因其胡須而與龍相聯系,進而賦予其吉祥、神圣的意蘊。
其次,中國上古時期的山羊崇拜及其在語言文字中的印記強化了山羊的正面含義。炎帝神農氏的“姜”姓及上古族群“羌”都是山羊崇拜的標志,至今傳為炎帝后裔的羌族、苗族、瑤族,納西族、侗族等都還有相似的傳統,如侗族古歌中就說其始祖姜郎和姜妹本是山羊。這一上古山羊崇拜體現在語言文字中就是一系列帶“羊”的字多有正面含義,如美、祥、洋之類;而“羊”和“陽”的同音也使得“陽”所具有的意義部分映射到了“羊”身上。
再次,中國文化中對于山羊與綿羊多統稱為羊而不加細分,這使得有時候兩者之間會互相影響,比如本屬綿羊的溫順等內涵會轉嫁到山羊身上,從而使得山羊的積極意義來源更加復雜。
歐洲文化中山羊以負面形象為主,其因由亦有數端。其歷史可追溯至前基督教時期歐洲古文化中對角神的崇拜。山羊神就屬于角神之一,如希臘神話中的潘神(Pan)和薩梯(Satyr)。它們多與性欲象征有關,源自印歐語人群對山羊旺盛繁殖力的崇拜,這也是山羊在西方色情類內涵的源頭。后來基督教傳入歐洲,在取代異教的過程中,角神等的異教神祇被基督徒貶斥為魔鬼撒旦的化身而打入另冊,從而奠定了西方語境中山羊代表魔鬼的符號意義。
當然,基督教中山羊的魔鬼形象也并非無所本,圣經傳說中罪惡的阿撒瀉勒就具有山羊的形體,這一形象的源頭其實是共同閃含文化中具有山羊形體的破壞者風暴神。屬于閃族的也門人至今保留了宰殺山羊的儀式,象征戰勝風暴、破壞之神(Baldick 1997)。這一破壞者形象通過同為閃族的猶太人引入了基督教,進而演變為罪惡和魔鬼之象征,并隨著基督教對異教的戰勝影響到歐洲各地。
再者,歐洲人對山羊和綿羊的截然二分也使得山羊身上的負面因素被放大,這種二元對立顯然植根于古老的印歐傳統中,范疇間界限分明,非此即彼。基督教傳入后,綿羊羔(lamb)成為耶穌的象征,山羊則相應變為撒旦的符號。二者間的善惡對比于是越發被強化了。
六、結論
本次調查數據證實了研究假設,即中歐文化中“山羊”一詞內涵的認知有顯著差異,其在中國偏向于積極正面含義而在歐洲則有負面不良暗示。該歧異現象可以在中國、歐洲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中找到根源。
顯然,若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忽略了“山羊”內涵的認知分歧,便可能帶來負面效應。比如將銷往歐洲的“五羊牌”產品譯成Five Goats,自然很容易遭遇類似昔年白象牌(White Elephant)、雄雞牌(Cock)等的尷尬。因此在翻譯中,譯者應持功能對等理念,采取回避或調換策略,如中文的羊年被有意處理成Year of Sheep,回避了Goat;廣州別名“羊城”則變成Ram City而非Goat City。諸如此類策略都是為了避免發生文化交流中不必要的誤會。
不過,隨著各國之間文化交往益發頻繁,相信在未來,原先異文化間的諸多內涵差異將隨相互理解的加深而逐漸消失,山羊自然也不例外。
[1]Baldick, J. Black God: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the Jewish, Christian and Muslim Religions[M].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7.
[2]Boulton, M. Faktoj kaj Fantazioj[M]. Rotterdam: UEA, 1993.
[3]Levy, R.D. The Symbolism of the Azazel Goat[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ress, 1998.
[4]Xu, Lishe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劉毓慶. 圖騰神話與中國傳統人生[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0.3969/j.issn.1001-8972.2010.16.085
曾俊敏(1983-),男,廣東揭東人,助教,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研究方向為翻譯學、認知語言學、中西文化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