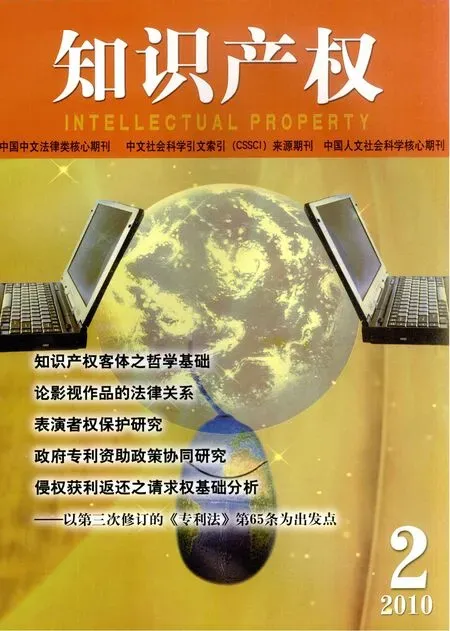技術標準的著作權問題辨析
■ 周應江謝冠斌
技術標準的著作權問題辨析
■ 周應江*謝冠斌**
標準可以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但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是具有立法、行政性質的正式官方文件,不應受著作權法的保護。與強制性標準一樣,推薦性標準也不在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內。標準制定機關對標準不享有著作權,標準出版者也不能取得著作權法上的專有出版權。標準出版者獲準發布標準,本質上是行政行為而不是經營行為。法律沒有設置經營標準的行政許可制度,出版者經營標準的權益可受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
標準 著作權 專有出版權
有關標準特別是國家標準的著作權問題,一直存有爭議。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1998]知他字第 6號和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的權司[1999]第 50號函件,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們的認識;而實踐中一些標準的既得利益者提起訴訟、主張標準的著作權的行為,更加劇了人們在此問題上的分歧。標準的著作權問題,不僅關涉標準制定者、出版者的利益,更關涉使用標準的公眾的利益,有必要根據《著作權》、《行政許可法》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規定的精神予以辨析和探討。
一、關于標準在著作權法上的定位問題
按照國際標準化組織的定義,“標準”是指由一些技術規范或其他明確的準則所組成被用作規則、指南或特征的定義的文件,其目的是要求產品、工藝及服務等達到一定的要求。1990年 7月23日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條文解釋》第一條第二款中,將“標準”界定為: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統一規定。可見,從其內容和功能上看,技術標準實質是表達一定技術要求的文件。
作為表達一定技術要求的文件的技術標準,雖然其內容是以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的綜合成果為基礎,但其草擬制定并不是對這些成果事實的簡單重述,而是需要進行整理和綜合,需要有人付出創造性勞動。因此,標準一般都是具有獨創性的智力成果,從著作權法的角度看,可以構成著作權法上的文字作品等作品形式。我國《標準化法》上規定的各種標準都可以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
標準可以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但并不一定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我國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都是國家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立法、行政性質的文件,屬于正式的官方文件,依《著作權法》第五條規定的精神,它們不應該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企業標準,是企業自己制定并只適用于企業自身的標準,不具有官方文件的性質,因此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在國際上,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等標準化國際組織制訂的標準受到版權法保護。一般認為,這些國際標準組織屬于非政府組織,其標準之所以能得到版權法保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標準制定者不具有公權力,如發達國家中有些標準的制定者就是公司或協會。1沈強:《淺析非政府國際組織的技術標準的版權保護》,載《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08年第 7期,第 10-15頁。根據《著作權法》第二條關于保護外國人作品的規定,這些國際組織的標準是可以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的。
我國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之所以具有官方文件的性質,原因在于它們是由政府機關依法定職責而組織制定、審批、發布和組織實施的,屬于法定標準,具有普遍的適用效力。與其他正式官方文件一樣,這些標準是全社會的公共資源,國家要鼓勵公眾盡可能地加以復制、傳播和使用。著作權作為一種壟斷權,它意味著未經許可,他人不得復制、傳播或者以其他方式利用相關作品,這與官方文件的性質是截然相反的。2王遷:《著作權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 7月版,第 45頁。因此在我國法律上,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不能成為著作權法的保護對象。
值得提及的是,《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關于標準著作權糾紛給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復》(權司[1999]50號)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關于中國標準出版社與中國勞動出版社著作權侵權糾紛案的答復》([1998]知他字第 6號函)均認為,強制性標準是具有法規性質的技術性規范,不受著作權法保護;而推薦性標準是不具有法規性質的技術性規范,應納入著作權法保護的范圍。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欠妥。
從我國《標準化法》第十四條等的規定看,推薦性標準與強制性標準的差異,主要在于執行和實施方式上的不同:推薦性標準由企業自愿執行,政府鼓勵實施,而對于強制性標準,企業必須執行,政府強制實施。我們認為,這種執行和實施方式上的不同,并不能導致兩者在性質上的差異,不能以推薦性標準由企業自愿執行為由而否認它的法規或規章的性質,更不能因此而認為推薦性標準不具有普遍的適用效力。
眾所周知,法律法規中可以有大量的任意性規范,強制實施是貫徹法律法規的方式和途徑,自愿實施也同樣是貫徹法律法規的途徑和方式。與強制性標準一樣,推薦性標準同樣是國家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按照法定程序而制定、審批和頒布的。與合同法保護當事人的約定的效力類似,企業采用推薦性標準,同樣也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當事人約定以推薦性標準為產品的質量標準,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同樣要承擔法律責任。既然沒有人因《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由任意性規范所構成而否認其的法律性質和適用效力,我們也沒有理由因推薦性標準由企業自愿執行而否認它的法規或規章性質。在實際中,政府機關制定的諸多標明為推薦性標準的標準中,也有不少條款被指明為強制性條款,并被要求予以強制執行。如果否認這些推薦性標準的法規或規章性質,那么這些強制性條款將何以執行?顯而易見,上述兩機關的函件,將規范性文件的實施方式混同于規范性文件本身的效力,并由此否認推薦性標準的法規或規章的性質,這種認識是不妥當的。在我國,與強制性標準一樣,推薦性標準 (包括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也不應該納入著作權法保護的范圍。
二、關于標準制定機關和標準起草者的權益問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標準的制定機關享有對標準的著作權,其理由是,標準是由標準制定機關組織制定、代表了制定機關的意志并由制定機關承擔責任,屬于《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的法人作品;標準的制定機關是標準的作者,依法對標準享有著作權。3凌深根:《關于技術標準的著作權及其相關政策的探討》,載《中國出版》2007年第 7期,第 48-50頁。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也是不妥當的。
首先要明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雖然法律規定政府主管機關有編制計劃、組織草擬、統一審批、編號、發布、實施標準等職責,但實際中,標準往往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由政府主管機關自己草擬,而是由政府機關委托或者組織其他公民或者法人起草的。按照《著作權法實施條例》關于“為他人創作進行組織工作,提供咨詢意見、物質條件,或者進行其他輔助工作,均不視為創作”的規定,組織制定甚至提供了一定經費的政府主管機關,并不構成其批準發布和實施的標準的作者。因此,認為標準制定機關是標準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標準制定的實際的。
其次,要區分“標準草案”或者“建議草案”與“標準”在性質上的不同。正如法律在立法機關決定通過之前,有主管機關起草的法律草案或者專家學者的建議草案一樣,標準在獲得審批之前,也往往存在標準草案或者建議草案。獲得審批之前的標準草案或者建議草案,可以被認為是起草者的法人作品或者個人作品,法律也可以承認法人作者或者自然人作者對其草案或者建議草案享有著作權。但是,標準草案或者建議草案被批準為標準之后,其作者就不能對這個“標準”享有著作權了,因為此時的標準已經成為正式的官方文件,成為具有普遍適用效力的規范性文件,不再在著作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內。所以,即使承認標準制定機關起草的標準草案是法人作品,即使承認標準制定機關對標準草案享有著作權,也不能認為標準制定機關對標準享有著作權。
值得關注的是,標準中凝結著標準草案或者建議草案的起草者或者作者的創造性勞動,由于法律不保護標準的著作權,這些起草者或者作者不能通過行使對標準的著作權而獲得利益,因此政府需要建立相應的機制或者措施,對標準的實際起草者進行補償或者獎勵。當然這種補償或者獎勵,并不適用于組織制定標準的政府主管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因為這本身就是其應承擔的法定職責。
三、關于標準出版者的權益問題
國家技術監督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署于 1997年 8月聯合制定發布的《標準出版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根據上級主管部門的授權或同標準審批部門簽訂的合同,標準的出版單位享有標準的專有出版權。”不少論者特別是獲得授權的標準出版部門往往以這個規定為依據,主張標準出版者享有著作權法上的專有出版權。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欠妥。
著作權法上的專有出版權,是根據著作權人的授權而產生的一項民事權利,需要以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和作者對出版者的合法授權為基礎。前文的分析已經表明,國家標準 (以及行業標準、地方標準)不屬于著作權法的保護對象,沒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著作權人;組織制定標準的政府主管機關或者部門,本身并沒有著作權可授予他人。因此,標準的出版者盡管與標準的制定機關訂立了合同或者取得了這些部門的授權出版標準,但并不能依據《標準出版管理辦法》這個行政規章而獲得著作權法上的專有出版權。
事實上,對于上述所謂“專有出版權”的性質問題,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與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認識并不一致。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的權司[1999]50號函件認為,標準由國家指定的出版部門出版,是一種經營資格的確認,排除了其他出版單位的出版資格,“這種出版資格是一種類似特許性質的行政權,是權力,而不是著作權性質的民事權利。”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1998]知他字第 6號函件則認為,標準化管理部門依職權將強制性標準的出版權授予出版單位,“應認定為一種民事經營權利的獨占許可。其他出版單位違反法律法規出版強制性標準,客觀上損害了被許可人的民事權益。”可見,版權局認為出版者的所謂專有出版權是一種行政權力,而最高人民法院則認為是一種民事權益。我們認為,應該從兩個不同的層面來認識出版者出版標準的行為及其權益的性質:第一個層面是標準的發布;第二個層面是標準的經營。這兩種出版標準的行為,都是對國家制定的標準的復制和傳播,但兩者的性質和出版者因此而享有的權益的性質也是不一樣的,需要區別處理。
第一,出版者獲得授權而發布標準的行為,是標準管理部門行使對標準的行政管理權力的體現或者延伸,標準出版者不能據此獲得民事權利。
以出版物等形式發布標準,是標準制定機關的法定職責,目的在于告知公眾標準已經存在和生效這個事實,同時也為公眾傳播和使用標準提供“標準的”或者說“權威的”、“可靠的”標準文本。2008年 5月施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條更是明確規定:“行政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是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應當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因此,發布標準既是政府進行標準化管理工作的必要環節和組成部分,也是政府的一項法定義務。
從傳播標準和便利公眾出發,標準制定部門可以在自己的出版物或者相關平臺上發布標準,也可以授權其他出版單位或者媒體進行發布。獲得制定機關的指定或者授權而發布標準的出版者,其出版標準的行為構成了政府發布標準這項行政工作的具體途徑和方式,本質上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權力的具體形式。因此,出版者獲得的這種授權,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特許性質,甚至可以是獨占性或者專有性的,但這種特許權本質上是行政權力的行使或者延伸,不是以獲得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經營性權利,更不是基于著作權而產生的民事權利。出版者的這種出版行為應該受到行政法的規制,而不是由民法著作權法等給以保護。
《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行政機關依申請提供政府信息,除可以收取檢索、復制、郵寄等成本費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費用。行政機關不得通過其他組織、個人以有償服務方式提供政府信息。”因此,獲準發布標準的出版者,不能從向公眾提供標準文本的活動中漁利;標準制定機關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保障標準發布的順利進行,規范發布標準的出版者的出版發行行為。
第二,出版者經營標準的行為,無需政府的行政許可,其權益可受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
依據《行政許可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的決定和省級人民政府的規章可以設定行政許可,除此之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設定行政許可。《標準化法》等法律賦予了標準制定機關以組織制定、審批、發布、實施和監督標準實施的職責。《標準化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標準的出版、發行辦法,由制定標準的部門規定。”《出版管理條例》第六條規定“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負責全國的出版活動的監督管理工作。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國務院規定的職責分工,負責有關的出版活動的監督管理工作。”從法律的這些規定可以看到,雖然標準制定部門對標準的出版發行負有監督管理的職責,但法律并沒有對經營標準的行為設定行政許可制度。因此可以認為,在現有法律上,出版者經營標準是不需要獲得標準制定機關的行政許可的。
實際中,一些人士主張出版者經營標準需要經過標準制定機關許可,主要的依據是國家技術監督局和新聞出版署于 1997年 8月發布的《標準出版管理辦法》。該《辦法》第三條規定“標準必須由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批準的正式出版單位出版。國家標準由中國標準出版社出版;工程建設、藥品、食品衛生、獸藥和環境保護國家標準,由國務院工程建設、衛生、農業、環境保護等主管部門根據出版管理的有關規定確定相關的出版單位出版,也可委托中國標準出版社出版。行業標準由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出版管理的有關規定確定相關的出版單位出版,也可由中國標準出版社出版。地方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出版管理的有關規定確定相關的出版單位出版。”第五條規定“根據上級主管部門的授權或同標準審批部門簽訂的合同,標準的出版單位享有標準的專有出版權。”
對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有學者認為,作為政府部門行政規章的《標準出版管理辦法》中的上述規定,均與《行政許可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和第十七條的規定相抵觸,應當認定為無效。4王潤貴:《國家標準的著作權和專有出版權芻議》,載《知識產權》2004年第 5期,第 50-51頁。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是有根據的,值得支持。標準的制定機關,并不能以《標準出版管理辦法》為依據而獲取對經營標準的出版者實施行政許可的權力。
依法設立的出版社和其他出版機構,經營已經發布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既不需要取得本不存在的所謂著作權人的許可,也不需要獲得標準制定和管理機關的行政許可。出版者合法經營標準的權益,既不是基于著作權人的授權而產生的專有出版權,也不是政府機關給予的特許經營權,而是其作為經營主體應該享有的自主經營的民事權益,可以受到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的保護。當然,出版者在行使這種權利的同時,也要接受標準制定和管理部門的監管,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作者系中華女子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法學博士。
** 作者系北京立方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