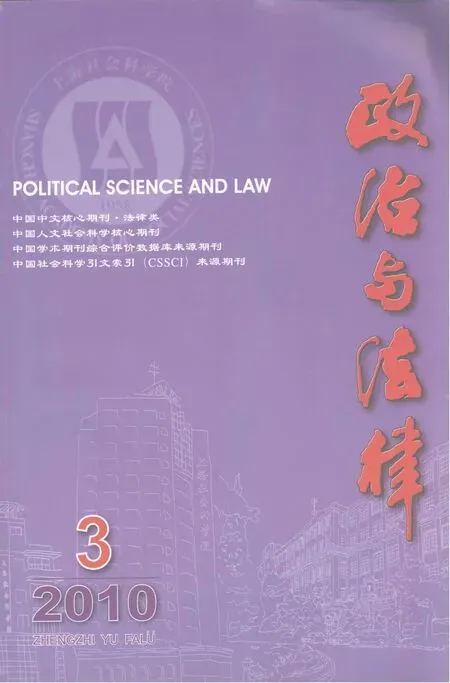氣候變化國際法與WTO規則在解決貿易與環境糾紛中的矛盾與協調
許耀明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中國臺北)
在氣候變化之議題上,對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與其京都議定書等相關法制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法制的兼容問題,已經引起相當之討論。1例如,排放權交易(Emission Trading)機制與WTO法是否兼容,排放權交易單位是否為服務貿易協議(GATS)所涵蓋,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與投資貿易協議(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簡稱TRIMs)之關系為何等等。本文主要討論在WTO之爭端解決機制下如何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以解決貿易與環境沖突議題,以及氣候變化法制(以京都議定書為主)與WTO規則在解決貿易與環境糾紛中的矛盾、沖突與協調等問題。
一、多邊環境協定與WTO法之沖突:法律解釋之角色
條約之解釋為相當復雜之過程。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以下簡稱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與第三十二條,分別詳盡地規范了相關條約解釋之法則。該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提出了文義解釋(依通常意義)與目的解釋(依條約之宗旨與目的);第三十二條則規定了探求締約者原始意向、并基于締約籌備相關歷史文件分析出發之歷史解釋方法。然而,雖然有前述規定之存在,WTO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所進行之條約解釋工作,在每一個個案之情形都不相同。縱使爭端解決議定書第三條第二項已經規范爭端解決機制之任務在于“依國際公法之習慣解釋規則,澄清本協議現有相關條款”,而爭端解決機制于汽油案中,以及相關學說,亦承認所謂國際公法之習慣解釋規則,即為條約法公約之規定,2但我們仍須進一步分析討論爭端解決機制所運用之相關原理原則、相關法律解釋方法與其來源。例如,在海龜小蝦案中,特別提到了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適用問題;而后續之生技產品案,則特別討論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之解釋問題,亦即WTO之相關解釋,是否可能運用“締約方之關系間可適用之所有相關國際法規則”。
(一)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思考:對于海龜小蝦案之省思
從WTO爭端解決機制運作以來,“司法化”為其重要特征之一,并形成所謂“司法經濟”(judicial economy)。3爭端解決機制此等運作,可從三方面觀察4:程序之衡平性、解釋之整體性與協調性、制度之敏感性。特別是所謂解釋之整體性與協調性,構成了美國法哲學家R.Dworkin所說的裁判“系列小說”,5而構成WTO法體系中調和式的解釋系統。
關于爭端解決機制進行條約解釋時之可能依據,在爭端解決議定書第三條第二項中所提及之“相關協議”,無疑為其主要來源。此外,國際間“合意法”(雙邊或多邊條約)、單方行為、習慣國際法與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皆為解釋之法源。6此外,在汽油案中,已經明白揭示WTO法“并非與一般國際法相隔絕”,而提倡不同國際法體系間之相互支持。7
而從方法論上看,依據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與第三十二條,上訴機構較常訴諸文義解釋,但較少使用上下文解釋、功能解釋或是目的解釋。8此等訴諸條約法公約之作法,也提升了爭端解決機制之正當性。9
例如,為找出“一般意義”,上訴機構常常訴諸字典。然而,單純僅參考字典是不夠的,還需要參照其上下文。10在汽油案中,為找出“當其有用時而為適用”之意義,上訴機構曾參考相關之牛津字典(New Shor ter Oxford Engl 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11但為詮釋GATT第XX條前言中所稱之“隱藏性限制”概念,上訴機構也曾完全不參照任何字典,而徑自認為“對我們而言,隱藏性限制,包括在國際貿易中之隱藏性差別待遇”。12此處,上訴機構不再尋求所謂“通常意義”,而是訴諸其它解釋方法。此即為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條約必須依……其上下文與宗旨與目的而為解釋”。此外,當字義不清或模糊時,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二條也規定條約之補充解釋方法,如參考條約之準備文件、締約重要因素以詮釋締約者之意向等歷史解釋方法。自此,所謂一般字義之解釋,其實為一種綜合性方法,包括其一般字面意義、條約文字之特殊用法、后續締約方之間之國家實踐或締約方當初之締約意旨等等綜合判斷。
關于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目的解釋,上訴機構在運用時則未曾系統地清楚說明如何運用。13有時,此等關于條約宗旨與目的之解釋,乃基于所謂“有效目的”(ef fet utile)或“善意解釋”(bonne foi)。14例如,在酒精飲料案中,上訴機構曾認為,“解釋者不能采取會讓條約失效之解釋”。15
海龜小蝦案中清楚地呈現了爭端解決機制進行解釋之不同步驟。上訴機構于本案中認為,基于WTO相關規則,WTO成員有權采取為保護物種或是可耗盡之自然資源等環境目的之貿易措施,但必須注意此等措施“不能以在會員間造成恣意或不正當之歧視之方式為之”,也不能“造成隱藏性之貿易限制”(GATT第XX條前言)。然而在本案中,尚須對于GATT第XX條第g款所稱之“可耗盡之自然資源”進行詮釋。
在本案中上訴機構并未訴諸文字解釋。然而,其否決了申訴方以歷史解釋所主張之“該款僅適用于無生命之資源”,16并援引了國際法院之“那米比亞案”,17同時參照成立WTO協議前言中關于永續發展之意旨,而認為“我們觀察到,對于該款所稱‘可耗盡之自然資源’之解釋,并非一靜態之觀點,而需有演化性之詮釋”,由是提出了嶄新的解釋方法即“演化性解釋”。然而如果依照前述之條約法公約,此種解釋方法,應該屬于哪一條項所規范?盡管學界討論甚多,目前仍無法清楚看出,此種演化性解釋方法,是否可以包含在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中。18雖然上訴機構曾援引成立WTO協議之前言,顯示其為一種上下文的參照,此已規范在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與第二項中。然而,演化性解釋是否是一種目的解釋,從上訴機構報告之字里行間尚難以斷定。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上訴機構曾經參考諸多國際文件以為解釋依據。因此,是否可以說,上訴機構已經意識到其乃適用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但也有些學者認為,前述演化性解釋,似乎是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四項所稱之“特殊意義”。19
(二)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之討論:對生物技術產品案之省思
在汽油案中,上訴機構曾明確表示“我們不能將相關協議隔離于一般國際法之外而為解釋”。20此等判決理由(dictum)顯得相當大膽,因為上訴機構不再僅限于運用解釋之習慣規則,而傾向不區分國際合意法與國際習慣法。21
在海龜小蝦案中,上訴機構援引了許多國際文件,以為其對于“自然資源”進行演化性解釋之基礎,包括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廿一世紀議程、對于野生遷徙性動物保護公約。然而,上訴機構并未直接援引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22根據此一條款,“必須考慮適用于當事國關系之任何有關國際法規則”。然而上訴機構參考了國際法院納米比亞案,并認為“所有國際法律文件之解釋,必須在解釋當時之現行有效整體法律體系之架構下,進行解釋與適用”。23此一引文之涵攝范圍,似乎比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來得更廣。24
然而,對于此等演化性解釋方法,有眾多批評。事實上,爭端解決議定書第三條第二項已經明示“爭端解決體系為確保多邊貿易體系之可預見性之基礎要素”。而對于WTO之部分會員而言,演化性解釋“將危害爭端解決體系之可預見性”;25此等解釋方法系“危險的,且未經諸會員同意”。26部分學說則認為,此亦有爭端解決機構自行“造法”(law-making)之議,27因此有限制此等演化性解釋適用范圍之必要。而亦有學者認為,“透過法律解釋所產生之新規范,亦屬習慣國際法之一部,而為許多多邊合意性之國際文件所承認”。28
如果我們從更廣之角度,亦即從各種多邊環境協議中之貿易措施與WTO之兼容性角度觀察,則前述討論實需要更精確地區分兩種情形:當爭端雙方皆為多邊環境協議之締約方與WTO之會員時,以及僅一方為多邊環境協議之締約方時。在第一種情形中,多邊環境協議似可作為“特別法”而優先適用。29然而,條約法公約第三十條第三項所稱之“后法原則”,于此似乎難以適用:當條約有修正時,很難斷定孰為后法。30此外,當我們以條約之生效日作為斷定時點時,可以認為GATT 1947為前法,而大多數多邊環境協議為后法;相反,如果我們采取創立WTO時之GATT 1994生效時點為判準,則多數多邊環境協議變成前法。同樣,如果我們改采修正時點為判準,則多數多邊環境協議在1994年之后都有修正,則又變回后法。此外,適用后法原則時,需要兩條約所規范之對象恰屬一致,然而我們很難認定多邊環境協議中之貿易措施與WTO法下所規范之貿易措施是否恰屬一致。31
在第二種情形中,爭端有可能發生于兩WTO成員之間,但僅其中一成員為多邊環境協議之締約方。于此情形,多邊環境協議中常出現多邊環境協議對于第三方之效力問題。此時,厘清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所稱之“當事國間關系”誠屬重要:究竟哪些相關國際法規則可以在當事國間關系適用?
海龜小蝦案中,上訴機構并未處理系爭個案爭端當事國是否恰為上訴機構所引用國際文件之締約國問題。然而,縱使美國并非生物多樣性公約之締約方,上訴機構依舊于解釋WTO相關協議時引進該公約而毫不質疑。本案之爭端當事國也沒有質疑上訴機構這樣做是否具有正當性。因此,于本案中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之問題,并未得到澄清。
然而在生技產品案中,此一問題為核心議題。本案中,歐共體引用了生物安全議定書以為其相關措施正當化之基礎。然而,爭端解決小組認為“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所得援引之國際法規則,必須為受解釋之條約所有締約國皆得適用者”。32關于此一論點,以下詳細分析之。
首先,必須厘清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所稱之“當事國”,究竟是“被解釋條約之當事國”還是“具體爭端之當事國”?關于此點,學說上亦爭論不已。33學者Palmeter與Mavroidis認為,此應指“具體爭端之當事國”。34而Marceau則采較廣之解釋,認為應采“被解釋條約之當事國”。35此外,Lennard認為,此應指“所有WTO之當事國”。36根據前述不同觀點,在生技產品案中,所謂適用于當事國間之國際法規則,有可能是美、加、阿根廷與歐共體間之規則(具體爭端之當事國間),或者是所有WTO成員國間之規則(如采被解釋條約之當事國說或所有WTO之當事國說)。不管采取哪一說,在本案中由于美國并非生物安全議定書之締約方,而加拿大和阿根廷尚未批準該議定書,因此該議定書無適用之可能。
雖然于學說上有前述爭議,爭端解決小組針對此點采取了“被解釋條約之當事國”說。所謂被解釋之條約,當然就是指WTO之相關協議,也就是說,必須所有WTO成員皆為締約方之相關國際法規則,于本案方有依照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而援引之可能。如此,可想見日后如欲于相關爭端中援引其它國際法規則之難度。37但我們還是要思考一下,爭端解決小組于生技產品案所采取之立場,究竟是否正當?學者Howse注意到,相較于上訴機構在海龜小蝦案中所采取之立場,本案之爭端解決小組之作法,明顯為一種實證主義與形式主義之倒退。38縱使我們認為前述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所稱之“當事國間”,系指“被解釋之條約締約方間”,Howse亦主張還是有引進其它國際法規則之可能性。因為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三項第C款系指“適用于”當事國間之其它國際法規則,所謂“適用”,并非指條約之“拘束力”。因此為求WTO法與其它國際法體系之調和,有可能以“適用”為名,促成國際法體系之調和性解釋。39從這一視角,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協定(簡稱SPS協議)第三條第一項也規定,“為求最大范圍地調和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各成員將以國際間規范、指令或建議為基準,制訂其防疫檢疫措施”。而此規定中,并沒有要求WTO成員需為此類國際標準之締約方。此規定恰好顯示,此等國際規則如何能夠“適用”于WTO成員間。40
其次,學者Howse也提出質疑,在WTO中,是否需要遵循“判決先例”(stare decisis)原則。41于酒精飲料案中,上訴機構曾認為:“爭端解決小組之報告為GATT重要既有成果(acquis)之一……對WTO成員而言,此構成正當之期待,因此于其它爭端發生時,必須將此類報告納入考慮”。42自此,如果后續之報告欲變更先前WTO案例中之法律論證,理應有明確且清晰之解釋。在生技產品案中,相當遺憾的是,爭端解決小組并未解釋為何其并不遵循于海龜小蝦案中參照其它國際文件之法律解釋方法。
最后,于本案中,歐共體也提出關于預防原則之論證,并主張其為習慣國際法或一般國際法。但此一主張亦遭爭端解決小組駁回。在荷爾蒙案中,上訴機構曾提及“關于預防原則之國際法地位,在國際法律學者與法律專業人士間已引起相當之討論。有些人認為預防原則已為國際環境法之習慣國際法。但其是否已被國際社會接受為國際法上之習慣國際法或一般國際法,則并不清楚。我們認為,于本案中上訴機構如果對此一重要但抽象之問題表明立場,將是浮夸而近于不慎”。43而于生技產品案中,爭端解決小組進一步指出,“由于預防原則之國際法地位尚不確定,如同在本案前之上訴機構無法決定,我們認為基于謹慎,不應嘗試解決此一復雜問題,尤其是在本案中必無解決之必要時”。44因此,迄今預防原則之地位仍屬模糊。然而,如果該原則被承認為習慣國際法或是一般國際法,則其相當可能成為在WTO解釋中得引用之法律原則。45
(三)小結
綜上所述,WTO法律體系不應脫離于其它一般國際法體系之外。按照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與第三十二條之法律解釋方法,我們可以擴大WTO之法律規范范疇,并嘗試在不同國際法次體系間找出平衡與調和之道,尤其在國際貿易法與國際環境法之互動上。當然,此種解釋方法與結果仍有其限制。
二、京都議定書與WTO之兼容性
為求減緩氣候變化之影響,國際間通過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條第五項規定:“各締約方應當合作促進有利的和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這種體系將促成所有締約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的可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從而使它們有能力更好地應付氣候變化的問題。為對付氣候變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單方面措施,不應當成為國際貿易上的任意或無理的視手段或者隱蔽的限制。”此外,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條第三項亦規定,“附件一所列締約方應以下述方式努力履行本條中所指政策和措施,即最大限度地減少各種不利影響,包括對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對其他締約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締約方和《公約》第四條第八款和第九款中所特別指明的那些締約方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影響……”從這些段落,我們可以歸納出的結論是:對抗全球氣候變化之相關措施,并不會妨礙國際貿易與發展,其相關措施與WTO相關法制是相容的。
申言之,關于京都議定書中所設計之各項貿易措施,即為實現減輕溫室氣體排放之“京都機制”,包括排放權交易、共同履行機制與清潔發展機制。此等機制,一方面為發達國家之承諾,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共同合作。首先,排放權交易機制,設計上為尋求最快地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制度,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規定“為履行其依第三條規定的承諾的目的,附件B所列締約方可以參與排放貿易。任何此種貿易應是對為實現該條規定的量化的限制和減少排放的承諾之目的而采取的本國行動的補充”。其次,共同履行機制為一財務機制,目的在于從源頭減低排放并加強碳匯之吸收。最后,清潔發展機制則設計為允許西方國家藉由各種投資于發展中國家之項目,以此達成其減排目標。綜上,此等機制乃藉由經濟與貿易手段,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因此會引發此等措施與WTO之兼容性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要先考慮此類措施是否對于國際貿易有不良效果?其次,需考慮該等措施是否乃為保護國內產品而設?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則必須再檢驗此等貿易限制措施是否有正當化之例外事由?例如這些措施是否適合用以達成環境保護目的?而我們也必須間接考慮,誰有權決定?如何決定何種目的系屬正當?何種手段系屬有效?
由此可見,為達成對抗全球氣候變化之前述措施,當然有其實行可能。例如,如果某國境內有環境稅之課征,則可能以邊境稅之方式對進口產品也加以課征。此外,如果國外產品之生產條件中關于環保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限制等系屬較為寬松,則也有可能透過一定措施,在進口時課征一定補償該等成本之稅捐。此外,對于能源使用標準,也有可能變成貿易措施。然而,這些措施是否符合WTO,尚待進一步檢驗。
(一)WTO不歧視原則之檢驗
WTO之不歧視原則,具體規定在GATT第Ⅰ條最惠國待遇原則與第Ⅲ條國民待遇原則中,而構成WTO法制之基石。然而,以京都議定書為基礎所采納之各項措施,也有可能落入前述條款之適用范圍內,甚至有其它WTO相關協議之適用,尤其是補貼與平衡稅協議(簡稱SCM協議)或技術性貿易障礙協議(簡稱TBT協議)之適用。
1.關于同類產品之認定
在WTO法律架構中適用不歧視原則亦即最惠國待遇或是國民待遇原則之基本前提,其關鍵點在于系爭產品是否為同類產品。如果基于氣候變化政策,WTO會員對于兩“不同”產品有差別之規范,則此時GATT第Ⅰ條跟第Ⅲ條并無適用之可能。
在實行氣候變化政策時,實際上存在許多可能性,而將影響是否為同類產品之認定。46
首先,兩相同物理特征與用途之產品,因生產方式之不同,可能有不同之溫室氣體排放。迄今,依據相關案例,尤其是鮪魚案Ⅰ與Ⅱ,生產方式之不同,并非區分不同產品之判準。然而,在石綿案中,消費者之偏好,被認為也可以作為區分不同產品之標準。47因此,如果兩產品有不同之溫室氣體排放,則依據消費者偏好,有可能被認為是不同產品。48同樣地,如果我們采取海龜小蝦案中曾提及的“演化性解釋”原則,且也認為于汽油案中所提及的“WTO法制不該自絕于其它國際法體系之外”之概念為正確,則環境保護意識和對抗氣候變化,將成為詮釋“同類產品”此一概念時相當關鍵之因素。
其次,如果兩產品之物理性質與用途皆相同,也有可能有不同之溫室氣體排放,但非因生產方式不同,而系因使用能源種類不同(例如太陽能與傳統能源之不同)。于此情形,依據WTO相關規定,有些學者認為,實在難以以“生產時所使用之能源”不同而為區分產品不同之標準,而認為此等產品應屬同類產品。49然而,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前述消費者偏好作為判準,則能源使用之不同,對于所謂綠色消費者來說,極有可能為不同產品。
再其次,兩個產品有相同用途,但其物理性質“在使用后”有所不同(例如用可再生利用之材料制成之汽車與傳統汽車),此時兩者是否為同類產品?由于此牽涉到生產方式,應屬不同產品。
最后,如果兩產品有相同之物理性質與用途,但其能源使用效率不同,此等與生產方式無關,但是與使用方式有關之差別,是否可能成為判準?根據石綿案之見解,此亦可能為不同產品。50
綜上所述,縱使生產方式依據相關案例不能成為區分產品之標準,消費者偏好依舊在未來有相關爭端發生而需判斷是否為同類產品時有關鍵性作用。
除前述之討論外,在WTO法律架構中,對于京都議定書規范之排放權,亦有判定其性質之必要。此等排放額度,究竟是產品還是服務?這牽涉到究竟最后應適用GATT或是服務貿易協議(簡稱GATS)之問題。部分學者認為,由于此等排放額度牽涉到具物理性質之溫室氣體,因此應為產品。另有學者則認為,此牽涉到無形權利之交易,因此應屬GATS之適用范圍。更有學者認為,此非產品,亦非服務。在有具體案例發生而由爭端解決機制斷定前,相信相關爭議無法停歇。51
2、WTO其它協議之適用可能
除了GATT或是GATS外,在WTO法律架構下,京都議定書之相關措施也有可能適用其它協議。
首先,關于補貼與平衡稅措施SCM協議之適用可能,必須注意該協議第一條第一項第A款第二目,其中規定,所謂補貼,乃指“放棄或未收取正常應收之公共收入”,且指“公共權力下財政收入”。如果WTO成員對于溫室氣體排放較少之生產有優惠措施,此是否構成補助;或者相反地,如果某WTO成員對于溫室氣體在生產之排放完全不加管制,但其它會員必須屢踐京都議定書,則前一成員之不管制行為,是否為補貼?由于迄今尚未有相關爭端實際發生,也沒有相關案例詮釋,部分學者認為對于前述問題,并無清楚確定之答案。52然而,也有學者指出,如果部分WTO成員無京都議定書下之義務,例如透過征收碳稅以達成減排目標,而其它成員卻已經以相關之規范落實京都議定書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此等不作為,將可能構成“放棄或未收取正常應收之公共收入”。53
如果采納此等大膽的解釋,則必須再進一步分析SCM協議之其它條款。該協議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依前項所規范之補貼,如果并非本協議第二條所定義之‘特定’,則不適用本協議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更有甚者,根據該協議第二條第一項第C款,“關于認定補貼是否‘特定’,必須考慮其它因素……對于特定產業之補貼、對于占優勢地位產業之補貼、給予特定產業不成比例之補貼、以及相關權責機構決定是否為補貼之裁量權行使”。如果WTO某一成員,并不限制特定產業之溫室氣體排放,很可能構成“給予特定產業不成比例之補貼”而為特定之補貼。54此等“特定之補貼”,可能構成該協議第五條第A款所稱“可控訴之補貼”,因其“造成其它會員國內生產之損害”。例如,美國如未對溫室氣體排放加以限制,則可能損及歐共體之相關產業。因此,依據該協議第十九條第一項,此時受損害之會員可以采取平衡稅措施。
其次,關于技術性貿易障礙TBT協議之適用可能,關鍵必須參考該協議附件一關于“技術性規則”之定義,其應屬“規范產品特征或制程或生產方式之文件,而具有拘束力者”。需注意在此定義中制程與生產方式清楚地在規范之內。因此,我們可以說關于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有TBT協議之適用。55
更有甚者,根據TBT協議第二條第四項,其規定“當相關技術規則有國際規范存在,或已經于最后決定階段,會員使用此等國際規范或其相關構成要素,以為技術規范之基礎,除非此等國際規范或要素,對于實現其正當規范目的系屬無效率或不適當,例如基于‘氣候因素’或基本地理因素,或基本科技因素”。據此,可能部分WTO成員將采取比國際標準更高之標準,只因為氣候變化之因素。此處存在著相當彈性。然而,此等實行必須有該協議第二條第三項所稱“既有科學與技術資料”之依據。
最后,TBT協議第二條第一項所規范之不歧視原則,當然也是相關措施實行時必須遵循之主要規范基礎。
(二)GATT第XX條之適用可能
雖然基于前述,如果WTO成員基于氣候變化政策之需要,針對產品為不同規范,此時是否為同類產品,尚有疑慮。然而,縱使認定為同類產品,此等措施仍有可能依據GATT第XX條之例外條款而為正當化。GATT第XX條前言規定“如(此等措施)不對相同條件下之國家間造成恣意或不公平之限制,也不造成對于國際貿易之隱藏性限制,則本協議并不限制締約方得基于以下事由,采取相關措施”。此外,本條第B款,規定此等措施為“保護人類、動物之生命或健康,或植物之保存所必要”;第G款則限制此等措施“需與保存可耗盡之自然資源相關,如果此等措施同樣地也限制國內之生產或消費”。
首先,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相關措施,是否為“保護人類、動物之生命或健康,或植物之保存所必要”之措施,應該毫無疑問。56而“氣候”是否為可耗盡之自然資源?在汽油案中,上訴機構已經明確表示,“空氣”(air)屬于可耗盡之自然資源。57因此,氣候極可能也符合此處可耗盡自然資源之定義。58
其次,分析第XX條前言系屬必要。59縱有各款正當理由之相關措施之實行,仍不能有恣意之差別待遇、不公平之差別待遇或構成對于國際貿易之隱藏性限制。在海龜小蝦案中,上訴機構曾明確表示,此一前言為:(i)平衡權利與義務之原則;(ii)有限制與條件之例外;(iii)善意原則(bonne foi)之體現;(iv)受禁止權利濫用(l'abus de droit)原則之啟發。60如果某一會員為實行其氣候變化政策,而有相關影響貿易之效果,則前述限制,必須在具體個案中逐案檢驗。尤其是根據海龜小蝦案之論證,基于多邊協商之方式應該是比較可行的。從此意義觀察,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毫無疑問地是多邊協商之結果。
而回到WTO成立之初,貿易與環境委員會(簡稱CTE)之成立,也彰顯了WTO成員間調和貿易利益與環境利益之意圖。然而,可惜的是,對于具體上如何落實,目前并無共識。在CTE 1996年報告第二十五段61中,曾指出“部分參與者曾表示……可能對于非多邊環境協議之締約方,采取差別性之貿易措施……。關于此點,參與者曾提及里約宣言之第七點原則,亦即在處理全球性之環境議題上的共同但有差異原則……。但其它參與者認為,此等對于非多邊環境協議之締約方,采取差別待遇之作法,并非達成環境保護之適當方法。其認為不能以差別性貿易待遇,作為強制多邊環境協議之非締約方加入該協議之手段,此并非WTO之角色……。因此,如果并未同時利用此等措施、尊重此等措施,特別是吸引各國加入此等多邊環境協議,則修訂WTO相關規定,以求基于多邊環境協議所采取之貿易措施得與WTO相關規則兼容之努力,將顯得失衡與孤立”。
在WTO各成員產生具體共識前,我們只能期待是否可藉由爭端解決機制之相關案例,找出調和之方式。然而,在前述CTE之報告中,也提及“WTO之成員,雖有權提交相關爭端至爭端解決機制,但如果某一爭端之當事方,同時也是多邊環境協議之締約方,則理應訴諸多邊環境協議之爭端解決方式”。62于此,展現了在貿易與環境之爭端中“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之想法。然而,如果相關貿易與環境爭端,僅有一方為多邊環境協議之締約方,則應該于何處解決,問題就變得復雜。
回到爭端解決機制,則悖論依舊存在:爭端解決機制是否該適用爭端當事國家所有相關國際法規則,即使這些并非WTO法制中之規范?此外,爭端解決機制是否可能以最寬松之方式詮釋“當事國間”之概念,而容許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在WTO相關爭端中得以適用?欲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能必須不幸地等到具體爭端發生后爭端解決機制之認定。
三、結論
即便WTO之會員、學說、相關案例皆展現了調和國際貿易發展與環境保護之意愿,真正要達成此一目的還有相當困難。如果運用“演化性解釋”之法律解釋方法,并堅持WTO法體系絕非自絕于其它國際法體系之外,則基于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所采取之各項措施,有可能藉由GATT第XX條,在WTO法制下例外地證成。然而,整體氣候變化法制仍在持續發展中,尤其是后京都時期(2012年之后)相關措施是否會有變化,還值得持續觀察。例如在2009年底落幕之哥本哈根會議,可說是毀多于譽。而會議之結果,所宣布之未經全體會員國大會通過之“哥本哈根協議”,雖然提出不少方案,例如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之經濟援助、財務機制,甚至具體提出“2℃”之全球氣溫上升上限目標,然而相關機制與目標,如何達成,于何時前達成,對于此等具體問題,并無規范。究其法律性質,與其說是國際法法源上之“宣言”,不如說是無拘束力之政治語言,或者充其量作為詮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后續國家實踐”。此等“軟法”,或者有人認為根本就不是法,對于后京都時期之變化,在新的有拘束力之國際文件出臺前,暫時應無太多影響。然而,此一協議中所涉及之財務機制或經濟、技術援助與WTO法制之兼容性如何,則亦如前述,有待于具體個案中澄清。
注:
1關于氣候變化之一般性介紹以及其相關經濟工具,參見P.-D.Cameron,The Kyoto protocol:past,present and future,in P.-D.Cameron and D.Zillman (eds.),Kyoto:from principles to practice,2001,p.3-23;R.Wolfrum et J.Freidrich,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in U.Beyerlin,P.-T.Stoll&R.Wolfrum (eds.),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a dialogue between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a,2006,p.53-68;J.-M.Arbour et S.Lavallée,Droit international de l’environnement,2006,Ch.5,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p.229-277;A.M.Chancosa,L’utilisation d’instrumentséconomiques dans la gestion international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global,in M.Bothe et P.H.Sand(dir.),La politique de l’environnement:de la réglementation aux instrumentséconomiques,2003,p.499-528。至于悲觀地認為京都議定書無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者,參見Th.Heeler,Climate change:designing an effective response,in E.Zedillo(ed.),Global warming:looking beyond Kyoto,2008,p.115-144。
2 Supra note 4,p.16-17.
3 L.B.de Chazournes,Le r le des Organes d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de l’OMC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environnement:entre le marteau et l’enclume,in S.Maljean-Dubois (dir.),Droit de l’OMC et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2003,p.379-400;v.p.379-383.
4 R.Howse,Adjudicative legitimacy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in R.Howse,the WTO system:law,politics and legitimacy,2007,p.211-246;v.p.218 et s.
5 R.Dworkin,Law’s empire,2003.
6 E.Canal-Forgues,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àl’OMC,2eédition,2004,p.108 et s.
7 29 avril 1996,WT/DS2/AB/R,p.19.
8 G.Abi-Saab,The Appellate Body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in G.Sacerdoti,A.Yanovich and J.Bohanes(ed.),The WTO at ten,2006.p.453-464;v.p.461-462.
9 R.Howse,supra note 13,p.231.
10 D.MacRae,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in G.Sacerdoti,A.Yanovich and J.Bohanes (ed.),The WTO at ten,2006.p.360-371,v.p.364;M.Lennard,Navigating by the stars:interpreting the WTO agreements,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7,22-27(2002).
11 Supra note 16,p.20.
12 Ibid.,p.25.
13 E.Canal-Forgues,supra note 15,p.104.
14 G.Abi-Saab,supra note 17,p.462.
15 4 octobre 1996,WT/DS8,10,11/AB/R,p.14.
16 Supra note 3,paras.127-130.
17 Ibid.,para.130,note 109.V.Namibie(Conséquences juridiques)avis consultatif(1971)Recueil de la C.I.J., page 31.
18 M.Lennard,supra note 19,p.28;L.B.de Chazournes,supra note 12,p.388;R.Howse,The use and abus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WTO trade/environment litigation,in M.E.Janow,V.Donaldson&A.Yanovich(eds.),The WTO:governance,dispute settlement,and developing countries,2008,p.635-670,v.p.645.
19 V.R.Howse,supra note 27,p.646.
20 Supra note 16,p.19.
21 E.Canal-Forgues,supra note 15,p.107-108.
22 R.Howse,supra note 27,p.644.
23 Supra note 3,para.130,note 109.
24 R.Howse,supra note 27,p.645.
25巴基斯坦之立場,Doc.WT/DSB/M/50,p.6.
26印度之立場,ibid.,p.11.
27 M.Lennard,supra note 19,p.75.
28 Eric Canal-Forgues,supra note 15,p.110.
29 A.Goyal,The WTO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006,p.368-371.
30 Ibid.,p.362.
31 Ibid.,p.361.
32 Supra note 10,para.7.71.
33 V.J.Pauwelyn,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2003,p.257 et s.
34 D.Palmeter and P.C.Mavroidis,The WTO Legal System:Sources of Law,9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41(1998).
35 G.Marceau,A Call for Coher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Praises for the Prohibition against'Clinical Isol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33(5)Journal of World Trade 125(1999).
36 M.Lennard,supra note 19,p.36.
37 Supra note 10,para.7.75.
38 R.Howse,supra note 27,p.652 et s.
39 Ibid.,p.656.
40 Ibid.,p.657.
41 R.Howse,supra note 13,p.238 et s.
42 Supra note 24,p.16-17.
43 16 janvier 1998,WT/DS 26&48/AB/R,para.123.
44 Supra note 10,para.7.89.
45 E.Canal-Forgues,supra note 15,p.120-121.
46 M.Doelle,Climate change and the WTO:Opportunities to motivate stat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3(1)RECIEL 85,93(2004).
47 12 mars 2001,WT/DS135/AB/R,para.101.
48 M.Doelle,supra note 55,p.94.
49 Ibid.p,94.
50 Ibid.,p.95.
51 W.B.Chambers,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Kyoto Protocol:Potential Incompatibilities,in W.B.Chambers (ed.),Inter-linkages: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s,2001, p.87-118,v.p.103-105;R.G.Tarasofsky,Heating up international trade law: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sed by effort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2(1)Carbon&climate law review 7,13-14(2008);Ch.Voigt, WTO law and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is there potential for conflict,2(1)Carbon&climate law review 54,55(2008).
52 M.Doelle,supra note 55,p.100;G.P.Sampson,WTO Rules and Climate Change:The Need for Policy Coherence,in W.B.Chambers (ed.),Inter-linkages: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s,2001,p.69-85,v.p.80.
53 L.G.T.Wolf,Countervailing a Hidden Subsidy:The U.S.Failure to Requir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s,19 Georgi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97(2006).
54 Ibid.,p.103.
55 C.O.Verrill,Jr.,Maximum Carbon Intensity Limitations and the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2(1)Carbon&climate law review 43,47(2008).
56 O.S.Stokke,Trade measures,WTO and climate compliance:the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O.S.Stokke,J.Hori&G.Ulfstein(eds.),Implementing the climate change—international compliance,2005,p.147-165,v.p.152.
57 G.P.Sampson,supra note 61,p.79;Meinhard Doelle,supra note 55,p.89.
58 W.B.Chambers,supra note 60,p.97.
59 S.Maljean-Dubois (dir.),Droit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et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2003,p.32,p.46.
60 Supra note 3,paras.156-158
61 12 novembre 1996,WT/CTE/1,para.25.
62 Ibid,para.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