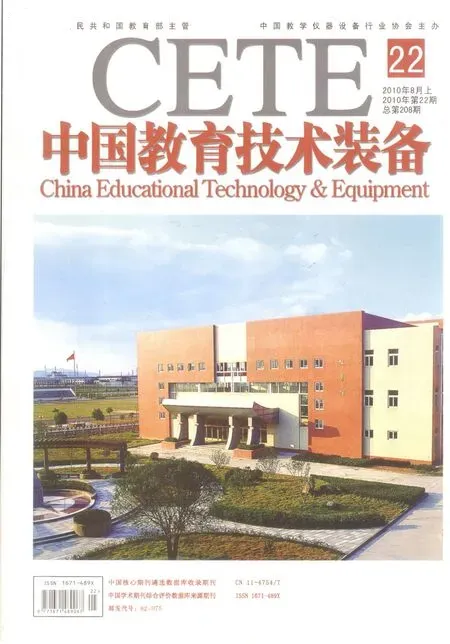淺談語文教材的處理
王立紅
語文教材處理指的是在準確理解語文教材的基礎上選擇教學內容、利用教學資源的教材組合過程,它解決的是“教什么”的問題。語文教材處理藝術指的是科學地、動態地、高效地從課文中提煉與組合最佳教學內容的藝術,它解決“教什么最好”的問題。教什么永遠比怎么教更重要,因此說,處理好教材是上好課的前提。
1 理思路與抓基點兩步走的處理藝術
每篇文章都有思路,思路體現在文章的層次之中。理清文章的層次,概括文章的層意是最傳統的教法也是最有效的教法,盡管目前有人否定這種處理方法。如果一個學生學了一篇文章,不知道文章寫了些什么,不知道文章前面說了什么,中間說了什么,后面說了什么,為什么要說這些,能叫讀懂了文章嗎?筆者認為,閱讀教學就要從理思路入手。理清文章思路,不但對提高理解能力有用,對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更有用。
在理清文章思路的前提下,教師要抓住兩個基點去組織教學。兩個基點指的是知識點與能力點。知識點包括字詞句篇、語修邏文等;能力點指的是讀寫聽說能力,具體指朗讀能力、識記能力、理解能力、分析綜合能力、表達應用能力、鑒賞評價能力。基點的教學是學生閱讀課文的一種導向,是訓練語文能力的一種規范,是對教學目標的具體落實。教師應該選擇課文中的精彩詞語、關鍵句子、重點語段、典型層次、突出手法、難點內容、主要知識等來落實基點教學。把理思路與抓基點結合起來,教學一定會有廣度,有深度,有厚度。
2 文言與文意并重的處理藝術
這種處理方法主要適合文言文教學。文言文教學的難點主要是語言隔閡,因此首先必須讓學生弄懂字詞句。語言沒疏通,就在那里大講“微言大義”,大講文化底蘊,這只是隔靴抓癢,囫圇吞棗,得不償失。文言文先學語言,不是說要大講古漢語語法知識,而是要把學語言放在理解文意的基礎上進行。學習語言一般要求學生弄懂:文言文中常出現的又較難的詞;古今異義的詞;典型的活用的詞;突出的通假字;突出的偏義詞;常用的又容易混淆的重點虛詞;古今不同的句式;難句的理解;等等。在理解詞句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去理解文意,把握基本內容和突出手法,把握作者的觀點與情感,積累語感,積淀文化,提高對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和鑒賞能力。在文言文教學中,要克服兩種錯誤的處理方法:一是支離破碎地只在語言上糾纏,甚至一句一句地串講,不賞析內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是丟掉語言,只在內容上求深求透,開拓創新。
3 “教教材”≠“用教材”?
其實“教教材”就是“用教材教”,“用教材教”就是“教教材”,誰能說它們的含義不是相同的呢?可許多專家硬是喜歡玩文字游戲,非得將“教教材”與“用教材教”區分開,并認定“用教材教”是教師的能動之舉,而“教教材”則是教師的迷信、懶惰之舉。
這一對人為炒作出來的概念把許多語文教師搞糊涂了,一些教師還沒來得及辨清二者的面目區別,就生吞活剝某些專家的見解,再加上自己的隨意附會,就滿那么回事地搞起“用教材教”的課。于是,這些教師對待教材的態度立馬變了,由“奉為圭臬”的走向“動輒非議指責”。在這些課堂上,教材如同話題作文中的材料一樣,只起引出話題的作用,而由材料(教材)引出什么話題,則全憑教師的直覺和個人喜好,并且多有對教材不挖出新意不罷休的魔念。這種情況下,“話題”一旦被引出并確定下來,他就敢拋開材料(教材),對文本的處理就變成“跳出文本”而非“立足文本”的純個性之舉。
筆者聽過一些教學文言文的課,總要涉及人物、作品、背景。此舉當屬正常,但如果過分細致地講析這些背景知識,必將弱化文言文語言教學的重點,并且只會增加這節課的歷史味道而非文學味道。筆者認為,背景知識當講,但只應講和文章內容緊密相關的知識,其他背景知識則應當一帶而過。
4 深入挖掘和處理語文教材
教師應重視在鉆研教材過程中自己的學習體驗與發現。鉆研教材的過程,是教師先行經歷和體驗知識生成過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教師的困惑和發現,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經歷,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的過程,所有這些對學生的學習來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這意味著教師能以一個“過來人”的資格對學生的學習施加影響。教師應積極深入地經歷這一體驗過程,珍惜自己的學習經驗,用自己的經驗來引領學生的學習活動,發揮教師在教學中的組織指導作用。錢夢龍老師把教師的這一做法上升到教學策略的高度來看待,認為這是一種“反求諸已”的教學策略。怎么教?自己怎么學就怎么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