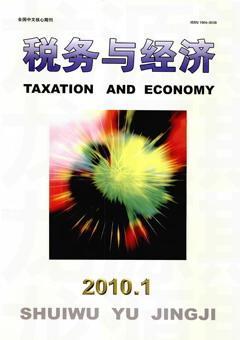雙邊稅收協定與CFC稅制關系探討
張衛彬
[摘要]長期以來,雙邊稅收協定與CFC稅制關系問題存在爭議。一般認為,受控外國公司稅制作為一種重要的反避稅措施,它與雙邊稅收協定是兼容的。但是,從一些歐盟國家的實踐來看,觀點并非一致。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規定了該項稅制,因此,解決兩者的兼容性也是將要面臨的問題。在我國《憲法》沒有對條約在國內法中地位進行規定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58條應予以完善。
[關鍵詞]稅收協定;受控外國公司;兼容性;企業所得稅法
[中圖分類號]FS10.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9339(2010)01-0107-06
為了避免跨國公司利用在避稅港或低稅區設立基地公司的渠道進行避稅,美國于1962年通過了肯尼迪法案,受控外國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簡稱CFC)法律制度得以體現在《國內收入法》(In-ternal Revenue Code)F分部。所謂受控外國公司,是指由本國居民直接或間接所控制的外國公司。由于CFC稅制能夠有效地限制納稅人的延期納稅或避稅行為,且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其予以特別推薦,因而使得德國、加拿大、日本、法國等20多個國家也先后制定了受控外國公司法。各國國內稅法一般都規定包括CFC規則在內的各種反避稅規則,以抵御有害稅收競爭。但是,稅收協定是否具有反避稅功能,抑或即使有此功能,但總體上是否包含一些具體的反避稅規則,兩者的兼容性一直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因此,如何厘清兩者的關系是各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雙邊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的關系
雙邊稅收協定(以下簡稱稅收協定或協定),是指兩國按照平等原則,通過協商分配稅收收入而簽訂的一種有法律效力的書面協議。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的關系實際也就是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關系的一個方面。盡管稅收協定包含法律實體規范和沖突規范,具有較大的復雜性,但有關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各項原則,同樣應適用于國際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的關系。
一般來說,稅收協定在國內法的法律效力依賴于一國的憲法。稅收協定是自動獲得國內法的效力,還是必須要經過特別立法轉化才能使其在國內獲得法律的效力通常存在采納和轉化兩種方式。如在歐盟范圍內,稅收協定納入國內法體系主要包括自動一體化模式、正式納入模式和實質納入模式。在自動一體化模式下,一國通過采納的方法使得稅收協定在國內法中成為自動執行條約,如法國、荷蘭、西班牙、瑞士等。在正式納入模式下,需要通過正式程序或法令將其納入國內法,如比利時、德國等。而在實質納入模式下,一些國家通過頒布專門的制定法將其轉化為國內法,如英國等。實際上,無論是正式納入模式還是實質納入模式,兩者都采用轉化的方式。
通常而言,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的目的有別,稅收協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雙重征稅以及防止逃避稅。因此,一般不會增加納稅人的負擔。但是,如果一國立法特別規定或者與一國的憲法相一致則存在例外。對于一些國家,憲法明確規定或通過憲法解釋,條約優于國內法。在這些國家內,稅收協定優先性是清楚的,因而推翻協定不可能產生。如根據巴西聯邦憲法第146條規定,作為補充立法的國家稅收法位階高于普通法。而且,國家稅收法也明確規定,稅收協定優于國內法。…然而,對于采用自動模式或者正式納入模式等國家來說,立法機關一般有權通過隨后的制定法推翻協定的有關條款。
根據條約必須信守的原則,推翻稅收協定應當予以避免。但是,“稅收協定優于國內稅法”并非各國的普遍觀點和一致做法。在一些國家,有的法律明確規定了政府有權不遵守稅收協定的規定,或者當意圖不明確時,由法院來予以決定。美國關于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關系的規定具有典型代表性。美國憲法實踐表明,條約和法律處于同一位階。如果出現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發生沖突時,為了國內法律的目的,通常隨后制定的規則優先。在《國內收入法》第7852條d款也明確規定“無論是協定條款還是稅收條款都沒有優先的地位”,以便于國內新制定規則的實施。
但是,美國最高法院在Cook訴美國一案中特別強調:美國國會通過聯邦立法違反其應當履行的國際義務的意圖應當明確。而且,在美國的許多部稅收法規中都允許通過明示方式廢止稅收協定的條款。例如,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外國投資不動產稅收法案》就有廢止稅收協定的條款。在1984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中,也規定了在外國公司發行囤積性股票的情況下可以違反條約。現在看來,這些例外條款發生得正越來越頻繁。鑒于此,OECD指出,推翻協定必須有特別的目的性。而且,建議其成員國在可能違反協定的國內立法出臺以前應當相互交換意見。當條款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時,該稅收協定就應當重新談判。
盡管美國國內稅法推翻稅收協定的做法遭到了其他一些國家的批評,許多與美國締結稅收協定的國家認為這種做法反映了美國對協定義務的隨意、傲慢的態度。然而,美國國會認為,這是其對稅收協定不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各種避稅而感到擔憂所致。但是,由于各國不能以國內稅法為由而不履行協定義務,否則是對國際法的違背,因此美國法院常常根據自身的判斷力盡量避免違反協定,且總是試圖協調解釋隨后的立法并沒有推翻稅收協定。即使在無法解釋符合協定時,也會辯解其可能違背了稅收協定的某些字面意思,但卻沒有違背協定的精神。
麥克奈爾(MeNair)認為,通常,國內法與國際法不符本身并不構成對國際法的直接違反。只有國家在具體場合不履行義務時才發生違反國際法的情形。實際上,美國以國內稅法優先為由而推翻稅收協定的情形在實踐中并不多見;只有在較為特殊的情況下,才會予以主張。而且,美國《國內收入法》第894條a款明確規定,其具體條款的實施應對美國所應負的任何協定義務適當考慮。有學者認為,在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的地位問題上,美國的法律有自相矛盾之處。但是,這種“矛盾”正反映了美國稅法的靈活性。況且,條約必須信守原則不能認為是絕對的,如果情況發生了變更致使條約的履行造成不公正的結果,該條約的履行就必須要受到一些限制。因此,稅收協定優于國內法不應絕對化。
不可否認,稅收協定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因為其經常與國內稅法的規定不一致,且僅局限于某些領域,往往需要國內法對其予以補充和完善。同時,各國的國內稅法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必須要經常地進行修訂和解釋,以保持其有效性。在國內稅法修訂之后,一般就要求對稅收協定也相應進行修訂,以與國內稅法保持一致。例如,1962年,瑞士就頒布了《防止稅收協定濫用法》。這在當時是違反瑞士與有關國家所簽的稅收協定的,但后來在與德國、比利時等修訂或締結新的稅收協定時,反濫用稅收法成為協定的條款。這也體現了各國總是意圖使得兩者具有一致性。OECD指出,雖然認為制定沖突性國內立法或者單方面采取國際法認為是不合法的行為構成對條約的違反,但也并不能為了避免條約沖突而單方面違反國內立法。近年來,為了避免國內立法與以前簽署的協定發生沖突的情況,有些國家進行了專門的
立法,以協調兩者的關系而不致于違反其條約法義務。
二、歐盟國家的實踐與OECD的路徑
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兼容性問題,并非僅是理論上的探討。對此,一些OECD成員認為,國內稅法的反避稅條款(包括CFC稅制)沒有必要在稅收協定文本中再進行特別地確認。德國等國家已經進行了單邊的國內立法。但是,國內立法有可能導致對協定的違反。在一些國家已有納稅人提起訴訟,主張適用稅收協定的規定并排除國內反避稅法適用的案例。基于此,下面主要以歐盟國家受控外國立法為例,進行闡述。
(一)歐盟國家的實踐
目前,英國、法國、芬蘭和瑞典4個國家對稅收協定與CFC稅制兼容性做出了判決,且各國對此觀點并非一致。在1997年英國Bricom公司訴國內稅務專員案中,該案涉及一個英國居民公司在荷蘭的一個名為Spinneys International BV(SIB)的受控子公司,它出售了在新加坡的一個分支機構而把資金借給英國母公司從而得到利息,英國稅務專員認為,應當將股息分配給母公司進行征稅。但SIB認為,根據英荷稅收協定第11(1)條款,該利息將得到豁免。對此,英國上訴法院認為,根據英國CFC稅制規定,英國母公司無需就荷蘭子公司所實際取得的利息進行納稅,判決英國的CFC制度與稅收協定的關于利息條款的規定不存在沖突。
然而,2002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Schneider案中得到了相反的結論。法院認為,法國的CFC體制違反了法國與瑞士的雙邊稅收協定第3(2)條款。甚至,法院強調即使法瑞稅收協定的目標旨在阻止避稅或逃稅,但此唯一因素對于消除法國CFC與稅收協定的兼容性而言理由并不充分。因此,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得出結論:除非稅收協定明確規定適用CFC的規定,否則稅收協定將排除CFC制度的適用。
在2002年A Oyj Abp案中,芬蘭最高法院判定,該國CFC稅制與芬蘭和比利時簽訂的稅收協定宗旨是一致的,即阻止公司逃稅或避稅。因此,稅收協定并不排除芬蘭CFC稅制的適用,除非協定本身明確規定排除其適用。但是,比利時不同意芬蘭的意見,認為兩者并不兼容。對此,達爾伯格(Dahlberg)認為,當一個國家在適用CFC稅制時,而另一國持反對意見,這難以確定該稅制與稅收協定條款是一致的。在此情況下,OECD建議有關當事國應通過協商采取適當措施對協定進行修訂。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國范圍內,其前后態度也并非一致。如在2005年4月4日,瑞典稅收裁決委員會在兩份不同的裁決中認為,瑞典的CFC制度并沒有違背相關的稅收協定,也就是與盧森堡和瑞士的雙邊稅收協定,并認為本國CFC稅制與稅收協定是兼容的。然而,在2008年4月3日對瑞士專屬自保保險一案判決中,瑞典最高行政法院完全不顧稅收協定的規定,認為其CFC規則優于與瑞士1987年簽訂的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對此,批評者認為,法院的裁決并沒有解釋協定的相關條款。
總之,在缺少相關國際司法機構或多邊條約對雙邊稅收協定和國內法律兼容性進行界定的情況下,而各國國內法院又從各自利益解決這些沖突勢必導致有爭議的結果。因此,盡管實踐表明,有的國家已經或者準備將國內法反避稅條款應用到稅收協定之中,以使得兩者具有兼容性,但各國對此問題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立場,這仍然依賴于各國的國內法。基于此,許多國家的稅收實踐都允許納稅人在協定與國內稅法的條款之間選擇于自己有利的納稅方案進行納稅;或者一些國家為了回避稅收協定與CFC稅制兼容性問題,特別規定CFC稅制只適用于協定締約國以外的國家。
(二)OECD的路徑
一般認為,如果在稅收協定中規定了CFC規則,那么就不會出現兩者兼容性的問題。然而,有的學者認為這將是對范本第7條的踐踏,阻止納稅人利用稅收協定規避CFC規則。同時,稅收協定是否具有反避稅功能抑或應當包含具體的反避稅措施,長期以來并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這需要通過國際層面予以解決,如OECD等。關于OECD范本(以下簡稱范本),最初的問題在于:能否從該范本概括出一般反避稅條款以使得與CFC體制相兼容。
1987年,OECD首先推薦其成員國引入CFC稅制。在1992年范本的注釋中,OECD只是簡單地說明了其大多數成員贊成兩者的兼容性,但并沒有采取一個清晰的立場。在2003年范本注釋第1條第1段中,對于國內反避稅法和稅收協定有關條款的兼容性問題做出了明確地規定,認為兩者是一致的。而且在第7段中明確提出,防止逃避稅也是協定的宗旨。對此,2005年和2008年的范本注釋進一步予以確認。
OECD認為,一般來說,國內反避稅法并不受稅收協定的影響。但是國家并沒有被賦予通過制定國內法而獲得稅收協定的利益,這構成了對協定條款的濫用。一般來說,實質優于形式(Substance-over—form)、經濟實質和一般的反濫用規則構成了國內反避稅法基本規則;而且,這些規則決定了上述違反事實所產生的稅收責任。從此意義上而言,作為國內反避稅法之一的受控外國公司立法與稅收協定并非不兼容。但是,并不是所有國家都滿意OECD的觀點。在2003年注釋范本發布不久,比利時、荷蘭、冰島、葡萄牙、盧森堡和瑞士等國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實,許多稅收協定都以范本為基礎,而且OECD建議各國適用其所提倡的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注釋范本。對于稅收協定的解釋,存在靜態和動態兩種不同的解釋方法。靜態的解釋方法是建立在協定締結時的情況及各當事方可預見的基礎之上,而動態的方法注重考慮未來的情事發展。由于2003年范本注釋明確規定稅收協定與受控外國公司等反避稅法的關系,這勢必對有關國家以前締結的稅收協定產生影響,即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對此,筆者認為,不應完全否認范本注釋有關條款適用于之前締結協定的解釋,可以將其作為協定補充解釋資料;畢竟該范本注釋體現了CFC稅制與稅收協定的協調一致性的關系。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58條檢討
為了防止我國一些企業在低稅率國家或地區建立受控外國公司②,將利潤保留在外國不分配或少量分配,逃避國內納稅義務,我國參照一些國家的做法,引入了CFC稅制。這是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在反避稅方面的突破性進展之一,具體體現在企業所得稅法第45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第116~118條等規定。這些條款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規制:取消了在低稅區非合理經營企業的遲延納稅;明確了構成受控外國企業的控制權力標準;界定實際稅負偏低的判定標準。
截止2009年4月,我國已經對外正式簽署了90個稅收協定。由于在此前的稅收協定并沒有涉及到CFC稅制,因此,我國在以后實施CFC稅制過程中,與稅收協定發生沖突將成為必然。那么在稅收協定與國內稅法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是適用稅收協定抑或適用國內稅法則成為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憲法沒有規定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關系。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5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外國政府訂立的有關稅收的協定與本法有不同規定的,依照協定的規定辦理”。從該條款規定來看,這與我國《稅收征管法》第91條、《民法通則》第142條、《繼承法》第36條、《行政訴訟法》第72條等規定大體是一致的;換言之,國際條約優于國內法。但是,筆者認為該條規定過于簡單,仍存在諸多需完善之處。
(一)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侵犯了憲法的調整對象
一般而言,憲法具有多重維度;其中,維度之一是:提供據以制定其他規則的規則以及確定其至上性和司法適用范圍的法律意義上的憲法。從理論上說,國際條約在國內法中效力問題首先應由憲法進行規定。雖然我國憲法并沒有禁止專門性法律規定其與國際法的關系,但在憲法沒有允許或授權的情況下,企業所得稅等基本法律做出規定,即使不違背憲法,但至少也有“越位”之嫌,侵犯了憲法的調整對象,也有悖于“憲法至上”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畢竟,專門性法律的規定不能替代憲法的規定,也不能導出憲法性原則。而且,那些關于“國內法與條約發生沖突,適用條約”的規定,并不意味著已將有關條約納入了我國的法律體系,或賦予了有關條約以國內法上的效力,畢竟條約對國家的效力與條約在國內法中的適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因此,我國在以后修改憲法時,應將條約的地位納入憲法,建議憲法的規定可以原則一些,具體規定可由其他相關法律予以完善,構建一個以憲法為主導、其他法律為補充的法律體系。
從各國的實踐來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通過憲法或者憲法習慣確立了條約與國內法的關系。但除了荷蘭等少數國家絕對堅持條約優先于國內法外,其他國家則采取較為靈活的做法,如有的國家遵循后法優先前法原則;有的國家法律明確規定,議會可以在后續立法中明示推翻稅收協定;有的國家態度模糊,由法院在具體適用時予以解釋。因此,我國企業所得稅法第58條所規定的內容,不僅缺乏憲法或憲法性法律依據,而且過于絕對化。
(二)協定的締結程序不同,國內法律效力也應不同
在我國,稅收協定是國際條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締結條約程序法》只對重要協定進行了規定,且《締結條約程序法》列舉了屬于重要協定的五種情況,并規定了相應的締結程序。一般來說,通過不同程序締結的國際協定在國內所獲得的法律效力應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國由聯邦法律或條約授權簽訂的行政協定,與其所依托的法律或條約有同樣的規范性地位,時間居后者有優先權。而由總統簽訂的單純行政協定其效力低于在它之前又與它相沖突的聯邦法律。從締結程序來看,我國對外締結的稅收協定應該屬于由國務院核準的條約或由國務院部委談判和簽署、不需要國務院核準的條約,這與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簽署程序相同。從法律效力上看,國務院對外締結的稅收協定,如果沒有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及國家主席的批準等程序,其就不能獲得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效力,更不能取得優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效力,而只能獲得行政法規的效力;否則,就會發生行政權替代立法權的可能。因此,稅收協定屬于行政協定范疇,其國內法的效力理應低于我國的基本法律。所以,企業所得稅法第58條規定違反了我國的法律效力位階,不利于國內法律體系的統一。
筆者認為,可以將稅收協定界定為《締結條約程序法》中的“其他需要批準”的重要協定,其締結應經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國家主席的批準并公布程序,從而使協定取得人大常委會立法的效力。這無疑有利于正確處理稅收協定與國內反避稅法的關系,較好地執行法律和稅收協定,也有利于促進憲政和法治國家的實現。
(三)條約在一國的效力和對一國的效力應屬不同法律范疇
國際法和國內法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法律,在效力關系上具有二重性。在國內層面上,國際法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國內如何實施國際法上的義務,即國際法獲得國內法效力的方式問題,國際法給予國家廣泛的自由裁量余地,屬于一國憲法解決的問題。而且,1989年《OECD報告》認可了以下四種憲法制度:協定自動生效,且優于國內法;協定的生效必須經過國會批準或特別立法將其并入國內法,給予協定優先地位;憲法規定協定與國內立法具有同等地位;憲法的效力基于國會至上原則,協定并不能約束其本身或者后續立法。由此看來,國際法并不關心各國在國內以何種方式實施國際法。因此,我國賦予稅收協定在國內法的效力低于全國人大或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從法理上講無可厚非。此所謂條約在一國的效力問題。
然而,在國際層面上,情況卻有所不同。雖然一國憲法在國內可以優先于國際法,但在國際層面上國際法優先于國內法是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1988年國際法院在聯合國本部協定案咨詢意見中,確認了這一基本規則;此謂條約對一國的效力。因此,無論是經過人大常委會決定批準的條約,還是國務院核準抑或無需核準的國際協定,其一旦生效,在國際法上就對中國產生同樣的約束力。如果條約、國際協定與國內法發生沖突,即便是由于條約或國際協定的效力地位低于國內法而使得條約義務未能得到履行,中國仍應承擔違反條約或國際協定的責任。我們不能以國內法作為違反條約義務的理由,如果想不違反條約義務,那就必須要放棄國內法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是選擇遵守條約還是維護國內法的權威,則很可能是政治上的一種考慮了。
從我國企業所得稅法第58條的規定來看,顯然有混淆條約在一國的效力與條約對一國效力概念之嫌。因為從目前我國協定的締結程序來看,稅收協定在國內層面上不可能優于企業所得稅法。因此,憲法或憲法性法律應當對此問題做出明確的規定,且應完善該條款的內容。除了一般規定稅收協定優于企業所得稅法外,還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在一定情況下授權我國立法機關制定后續的特別立法,以避免稅收協定的濫用。同時,國家可以根據“非加重原則”(non-aggravation),或在稅收協定中規定“保留條款”,允許納稅人選擇適用國內稅法或稅收協定。
值得強調的是,我國在與他國修訂或簽訂稅收協定時,已經涉及到了這一問題。例如,根據2007年7月所修訂的《新加坡共和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稅的協定》第26條規定,“本協定并不妨礙締約國一方行使其關于防止規避稅收(不論是否稱為規避稅收)的國內法律及措施的權利,但以其不導致稅收與本協定沖突為限”。這也是條約對一國效力的應然要求,同時也說明了在不與協定抵觸的情況下,國家有權對避稅行為進行規制。但是,該條規定并沒有具體涉及受控外國公司稅制。
實際上,一些實行CFC稅制的國家在對外簽訂稅收協定時,為了使得兩者具有兼容性,開始在協定中加入特別條款,允許締約國以國內CFC規則為由推翻協定的有關條款,或者明確規定稅收協定的一些條款不得被解釋為否定CFC規則。例如,在巴巴多斯與加拿大簽訂的稅收協定第30條第2款規定,該協議不得解釋為阻止加拿大按照所得稅收法令第91節規定對其居民進行征稅。㈨因此,我國以后在與他國重新談判或簽訂新稅收協定時,也應考慮將CFC規則納入協定條款,從而使得兩者具有兼容性。
責任編輯: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