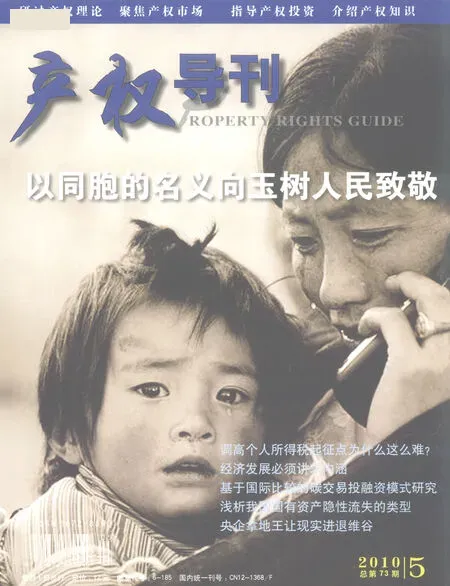人民幣升值:硝煙再起
■/于化龍
人民幣升值:硝煙再起
■/于化龍
近期,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論調一浪高過一浪。幾乎在突然之間,中國由帶領全球經濟復蘇的功臣,變成了造成全球不平衡的“罪人”。

人民幣升值硝煙再起
2010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暗示要求人民幣升值;3月15日,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撰文,直接要求美國財政部把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此言一出,美國百余名國會議員的聯名信、奧巴馬的支持更是把這一事件推向白熱化。3月16日,美國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領銜啟動了《2010年匯率監管改革議案》立法程序,他希望,美國政府能夠在判定人民幣匯率存在“根本性偏差”后,采取有力的經貿反制措施;3月23日,美國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發布名為《中國不平等貿易導致工作崗位流失》的報告稱,2001—2008年間,美國一共有240萬份就業流失,重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3月24日,美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舉行聽證會,參會的經濟學家普遍同意,人民幣的幣值由于中國政府對市場干預而被低估了,并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人為地增加了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價格而抑制了中國商品的出口價格。此次會議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再度推上風口浪尖。
主張人民幣升值有兩種思路,一種是以美國部分議員為代表的蠻橫派,簡單地從美國利益出發,要求奧巴馬政府在發布有關匯率操縱的定期報告時,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之一,還呼吁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反補貼稅。另一種則是以學術探討的語氣說服人民幣升值,試圖從中國角度證明升值不僅符合美國利益,對中國經濟也大有益處。他們主張,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能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能控制通脹預期尤其是資產價格泡沫,能調整經濟結構,更多地依賴內需。
近年來,中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儲備量持續增加,幾乎成為美國指責中國“刻意”壓低人民幣匯率的最大“罪證”。經典邏輯是,人民幣幣值低估,導致美國對華巨額逆差,而逆差奪走了美國人的就業。人民幣在2005年到2008年累計對美元升值21%,但這并未帶來同時期內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減少。在2008年夏季后,人民幣被普遍認為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上,而中國的貿易順差從2008年到2009年下降了約34%。世界銀行在3月17日發布的《中國經濟季報》中指出,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從2005年7月匯改至今年3月初這段時間升值了12.3%,另外,國際清算銀行日前的數據顯示,2月份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為118.41,比1月份大幅升值4.09%,漲幅創新高。
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美國的赤字問題,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2001年美元開始下跌,至今貶值40%,但美國出口并未因此上升。恰恰相反,赤字從2001年的1萬多億美元升到如今的3萬多億美元。而盡管人民幣從2005年開始升值,至2008年金融海嘯前升幅逾20%,但同時我國出口不降反升,貿易順差越來越大。
施壓另有企圖
人民幣短期內大幅升值能明顯改善對華貿易赤字嗎?答案是否定的。人民幣匯率并非靈丹妙藥,這是學界和業界的基本共識。一些發達國家對華貿易逆差原因更多的是結構性和政策性因素,而非匯率問題,逼迫人民幣升值無助于解決貿易失衡問題。以中美貿易為例,中國出口產品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出口中國的則是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品,這符合優勢互補和自由貿易原則。美國采取歧視性政策,單方面限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擴大了兩國間貿易差額,這種不對等地位不消除,貿易失衡狀況難以改變。據牛津經濟研究中心報告,即使人民幣升值25%,兩年后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僅減少200億美元,這對緩解美國每年數千億美元的貿易赤字也無足輕重。看來,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另有企圖。
首先,美國要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是為美貿易服務,配合美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通過迫使人民幣升值削弱中國產品的競爭力。美國經濟處境目前十分艱難,官方失業率是9.7%,而實際失業率可能接近17%,經濟低迷,前途渺茫,公眾不滿情緒一觸即燃,對于自由貿易的潛在不安逐步涌現,奧巴馬政府需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就會要求美國出口行業重振旗鼓,而美元貶值將有利于提振美國出口。值得注意的是提出這個問題恰逢美國兩黨11月份正式中期選舉之前,是執政方給另外一方施加的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更多是美國出于政治的需要,美國并非真的認為人民幣升值可平衡外貿。
其次,美國借助要人民幣升值來逃避其應承擔的金融危機責任。中國坐擁龐大美債,人民幣升值將稀釋債務,變相成為美國賴債手段。美國不能指望逃避其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應承擔的主要責任,更不能打著解決全球失衡的幌子實施貿易保護主義。2010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提出,要在未來5年內實現出口量增長1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出口國;3月,奧巴馬又簽署一項政令,成立了一個“出口內閣”,全力擴大美國出口。美國在金融海嘯剛過去之時,立即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生事,主要是配合后海嘯時期美國經濟調整的實際需要,同時將龐大的債務稀釋。
再次,美國的戰略目的就是遏制中國崛起。干預人民幣匯率令中國重蹈當年日本衰退的覆轍,這是美國一貫的策略,即當別國崛起可能妨礙其利益時,就會竭力打壓。盡管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在對中國青年發表演講時曾表示:一國的成功不應以另一國的犧牲為代價,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崛起。而實際上,美國允許中國發展,但絕不允許發展成它強勁的對手,更不允許中國崛起到美國之上。中國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體制,要受美國掌控,這才是美國的真實政治意圖。
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在對華貿易戰略上呈現出十分突出的“兩面性”,即:一方面積極提倡推行世界范圍的市場化和自由貿易;而另一方面從眼前自身利益出發卻又不斷強化貿易保護主義。美國要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借助要人民幣升值來逃避其應承擔的金融危機責任,最終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
升值的影響及應對措施
首先,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不僅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利,對整個世界經濟都有利。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目前中美已從單純的貨物貿易擴展到經濟的各個領域,美國企業獲得了豐厚收益。對華貿易投資還加快了美國就業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步伐,為美國服務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美方從中美經貿合作中獲得的宏觀經濟利益也相當可觀。一方面,中美經貿合作有助于保持經濟穩定;另一方面,中國購買美國的國債也有利于美國穩定金融市場。壓迫人民幣升值不僅不利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持續復蘇同樣沒有好處,人民幣匯率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施壓人民幣匯率不僅有損中國的利益,也難以改善美國的貿易狀況,是典型的損人不利己。
其次,人民幣升值還會對我國產生諸多負面影響。一是對資產的價格影響。在升值前外國投資者如把外幣換成人民幣,一旦人民幣升值,便能獲得與升值幅度相應的收益,促使投資者追逐我國資產。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產,投資者不但獲得升值收益還能獲得股票房地產本身增值收益,造成巨額資金進入,促使股價和房價進一步上漲,帶來泡沫經濟;二是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外國商品進入該國,要收回同樣的外國貨幣,價格相對便宜,商品就具有競爭力,有利于外國商品進入;三是對本國生產成本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人民幣升值會提高外商在我國的投資成本,同時也會提高我國原材料、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對國際市場的價格,進而增加外商在我國投資辦廠的成本。
那么,應如何應對新一輪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呢?
首先,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與調節機制。一方面,積極完善外匯市場運行機制,增強市場流動性,拓展市場交易主體的廣度和深度,構建完整的外匯市場,以促進外匯市場上均衡價格的形成;另一方面,豐富市場交易幣種,完善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大力推廣遠期、掉期外匯交易和外匯期貨交易等金融衍生交易方式。
其次,要降低儲蓄和低效投資。2007年至2008年,中國儲蓄率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5%,經常項目順差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0%,企業儲蓄幾乎占國民儲蓄的半壁江山,國企積累的資本更多地被投向本以產能過剩的領域,投資效率極低。在國民收入中,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僅為35%,國家在一段時間內無法從根本上提高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和工資水平。因此,為了提升國內消費,必須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將資本導向具有巨大國內消費潛能的領域。
再次,從長期看,不能簡單地從人民幣短期價格與簡單價值和國際關注的角度去考量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它是一個系統工程、配套工程和基礎工程。實際匯率的調整可通過貨幣政策、資源改革、價格體系、財政政策等的互動與調整,以及與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相結合,需多管齊下。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不斷演變和完善的過程,人民幣升值將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所以,人民幣匯率不可能在強大國際政治壓力形成明顯從而預期明顯和投機活動明顯的情況下調整,而必須根據我國經濟長遠發展的需要做出慎重決定,在適當的時機進行調整,否則不論對中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可能產生嚴重后果。如果強制中國進行人民幣匯率升值,在中國產業調整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造成中國資產嚴重泡沫化,形成當年日元升值之后的結局,這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沒有好處的。
(作者單位:北方國際信托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