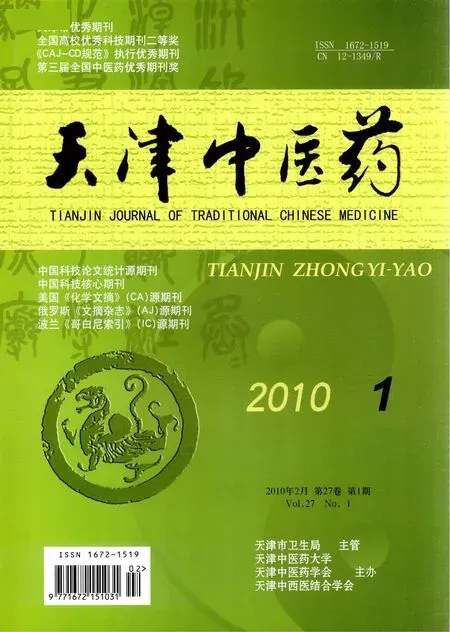楊錦堂教授治療急癥的經驗
趙冀生
(天津中醫藥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天津 300193)
中醫治療急癥歷史悠久,內容豐富,歷代醫家對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著述頗多。但時至今日,人們卻普遍認為中醫中藥只能治療慢性病,疑難雜癥,把一切急癥治療都寄托于西醫西藥,致使中醫治療急癥這一瑰寶有著瀕臨丟失的危險。楊錦堂教授行醫60載,除在醫院急診科室外,在農村、鄉鎮、民間也常會突然遇到卒病、暴病、意外損傷,其特點是發病急、變化快、病情重,如治療不及時,會延誤病情造成不良后果,其運用中醫中藥、針灸、甚至民間驗法驗方治療急癥,確有獨到之處。
楊錦堂教授總結中醫對急癥的治療,一方面取決于敏捷而正確的辨證與辨病,另一方面需要迅速的處方用藥。中醫在診治時,要及時、準確、果斷,重視脈診,重視腹診,明確急癥的病機。要突出“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的治療法則。用藥每以中成藥治療取得滿意的療效。針灸療法是急癥救治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有著很多為其他療法所不及的長處,它不受地點、時間、設備、藥物等各種條件的限制,器具簡單,隨時隨地,均可應急。
1 二陳湯加味治療神昏
1942年2月14日(農歷12月29日,除夕),楊錦堂教授回故里過春節,有一親戚患病,邀其診治。患者,男,30歲,神志不清5 d。5個月前,曾患高燒不退,請縣里2名中醫治療多日燒始退。近一段時間少言懶動,進而臥床,昏不識人。診時見:患者目睜直視,呼之不應,神昏不語,喂流質食物,勉強能進,不知饑渴,二便自遺,昨日大便軟。腹部不脹滿,肌膚不熱,手足不冷,刺上臂似有痛感。口舌不燥,舌苔白膩,脈弦滑。診查患者,不寒不熱,二便通,腹不滿,似煤氣中毒癥狀,而其居處燒柴草土炕,通風狀況好,無煤氣中毒可言。翻閱前醫的處方,多為清熱育陰之法。脈癥合參,辨證為痰濕蒙蔽心包。治宜溫化痰濕,方用二陳湯加味。
處方:陳皮、半夏、茯苓、蒼術、膽南星、白芥子、竹瀝、絲瓜絡、生姜。2劑,水煎服。
3月3日(正月17日),患者父親告訴說其子已愈。除夕當天,第1劑藥不慎煎糊不能服用,再煎第2劑,給其子服藥時又被其子用手打翻。又將第2劑藥渣再熬第2煎,多人幫助將湯藥灌下。半夜過后,患者清醒,自知要水喝,待到天明已能坐起。第3天能下地活動。
患者先前是感受夏秋濕熱病邪引起的外感熱病,濕遏熱伏,蘊蒸難解,故久熱不退,病程較長。前醫見高熱,治以清熱育陰之法,熱去濕留。濕邪久郁不去,凝結為痰,痰濁阻滯,蒙蔽心包,發為昏厥。“怪病多由痰作祟”,用二陳湯加味行氣豁痰,藥專力捷,痰濁去,病邪除,病自愈。
2 蘇合香丸治療暑穢
1969年夏,“文革”期間,工宣隊帶天津中醫學院師生在天津市薊縣馬伸橋接受“再教育”,楊錦堂教授被派往鎮衛生院,每日半天為貧下中農看病。鎮農機廠一職工之父,80歲,神昏2 d,不進飲食,邀楊錦堂教授去家中診治。
患者,男,80歲,神識昏蒙,嗜睡朦朧狀態,呼之可醒,旋即昏昏入睡。天氣悶熱,而患者有汗不多,身無灼熱,腹柔,小便短赤,當天無大便,舌苔白厚膩,脈緩。辨證為痰濁蒙蔽心包。鎮衛生院中藥飲片不全,但有中成藥蘇合香丸。處方:蘇合香丸2粒。囑:即刻化服1粒,晚間再服1粒。
第2天,農機廠職工來告訴說:其父服下1丸藥后即清醒,能進飲食。今天已能坐起,并下地稍微活動。病愈,未再繼續服藥。
本案患者夏季感受暑濕穢濁之氣,暑濕郁蒸,則膚熱有汗,但熱不太甚,汗亦不多,穢濁蒙蔽清竅而出現神昏。患者濕濁較甚,用蘇合香丸清利濕熱,辟穢化濁,豁痰開竅,只服1丸藥,即藥到病除。
3 針刺內關穴治療胸痹
1970年春,楊錦堂教授帶河北新醫大學65級學生在河北省欒城方村實習,該公社供銷社一職工,男,50歲,上午突然胸痛憋氣,病勢甚急,派人來求治。帶學生急速到達,視患者頭汗淋漓,捫胸呼痛,展轉不安,手冷,脈似有似無。血壓50/20 mm Hg(1 mm Hg=0.133 kPa),神志不清。診斷為胸痹。立即針刺兩上肢內關穴,強捻轉提插。讓學生到公社衛生院取人參須3 g,延胡索3 g(沒有人參和其他急救藥),搗碎,3 g/次,分兩次用溫開水送服。不斷捻轉提插針柄,15 min后患者喘大氣,胸悶憋氣疼痛消失,脈轉和緩,肢體溫和,血壓恢復正常,有疲倦感。囑其平臥休息。第2天上午去石家莊第四醫院診查,心電圖正常。
4 歸脾湯治療小產虛脫
1950年8月15日,楊錦堂教授在天津市河西區桃園村同鄉家做客。適逢其同院一40歲婦女陰道大出血,冷汗淋漓,神志不清,四肢不溫,脈微欲絕,急邀楊錦堂教授救治。當即用鐵菜刀、鐵飯鏟在煤球爐上燒熱,輪流用醋噴灑其上,使醋蒸汽熏其口鼻,約10 min后,患者清醒,汗出,下血減緩。開處方:歸脾湯去木香,加鹿角霜、敗蓮房3劑,令其家人速買藥煎熬,藥后血漸止。1周后再見患者,其訴說:自己妊娠3個月,小產后下血不止,15 d大出血昏厥,幸遇良醫,藥后已不出血,身體逐漸恢復。
本病屬中醫學“產后血崩”的范疇,是婦產科的急危重證。患者突然陰道大出血,以致造成陰血暴亡,陽無所附,陰陽離決之危象。急則治其標,限于當時條件,用鐵器燒紅,淬醋中,以熏其鼻孔,促其蘇醒。再用歸脾湯加減益氣固脫,使其向愈。
5 歸脾湯治療產后出血過多胞衣不下
患者,女,30歲,山東陵縣神頭鎮農婦。1942年12月生產,村里產婆接生。產下女嬰后大出血,胞衣脫出部分,牽引拖動不出,血出如注,產婦昏厥。診時見:產婦面色蒼白,半仰半臥位,若躺平或坐起則立即昏厥,語言低微,回答不清,手足不溫;適值災荒饑謹之年,營養不良,身體消瘦。舌質暗淡,脈虛弱似無。急以歸脾湯加血余炭、懷牛膝、鹿角霜煎湯令其服,囑咐家屬,胞衣不可再牽動,任其自行脫出。第2天,胞衣自行脫出,血出不多。繼續服用原方2劑,出血止。家貧無錢再吃藥,囑其注意調護。隨訪半年,母女均安。
本病屬中醫學“胞衣不下”。患者素體虛弱,產時沖任胞脈受損,出血過多,以致陰營下奪,氣隨血脫,氣血暴虛,推動無力,胞衣不下。治療應本著“勿拘于產后,亦勿忘于產后”的原則,急用歸脾湯健脾益氣,固攝養血。氣血恢復,胞衣自行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