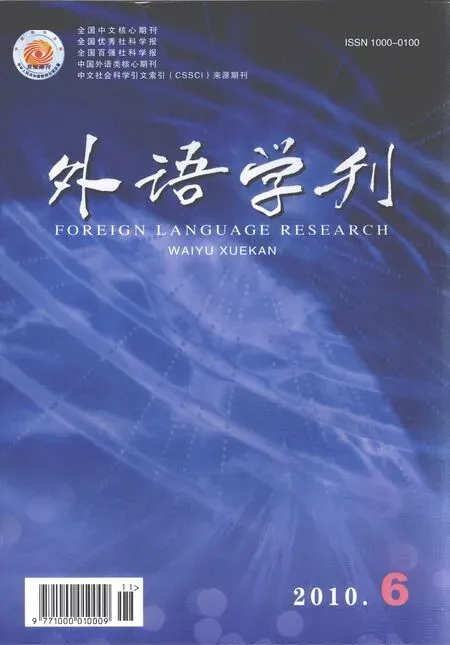從《舞 舞 舞》的三種譯本談譯者的翻譯態度
于桂玲
(黑龍江大學,哈爾濱150080)
早在2006年卡夫卡文學獎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之前,村上春樹就已經成為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日本作家。近年來,學界對村上文學的研究越來越熱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從譯介學,尤其是版本研究角度出發,分析村上春樹在中國乃至漢語圈國家和地區的譯介狀況及其產生原因,作者、譯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關系的研究尚未展開。本文將探討村上春樹的《舞舞舞》(以下簡稱《舞》)的三種譯本。
1 選擇《舞》及其第23章作為素材的理由
1.1 《舞》繼《挪威的森林》之后在中國譯本最多
《舞》是繼《挪威的森林》之后村上春樹的又一部長篇小說。它1991年譯介到我國,半年間就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版本,分別是:《舞吧,舞吧,舞吧》(張孔群譯,1991年1月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3000冊),《青春的舞步》(林少華譯,1991年3月南京譯林出版社,10,000冊;1996年桂林漓江出版社12,000冊;2002/2004/2007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更名為《舞!舞!舞!》]77,900冊。合計 99,900冊)和《跳!跳!跳!》(馮建新 洪虹譯,1991/1992/1993年桂林漓江出版社,計27,500冊)。可見,《舞》的累計銷售量達13萬多冊。
1.2 《舞》能夠代表村上春樹的寫作特點
關于《舞》的寫作經歷,村上春樹曾經在游記《遠方的鼓聲》中寫道:“我覺得這篇小說幾乎從頭到尾都寫得很順暢、舒服。《挪威的森林》對我來說,因為以前從未寫過同類作品,曾經邊寫邊胡思亂想:‘這篇小說會被怎樣理解呢?’而寫《舞》時卻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村上春樹2006:382)
在《舞》這部作品里,村上春樹以他非凡的想象力,把現實世界與非現實世界鑲嵌得天衣無縫,它顯然與《挪威的森林》不同。《挪威的森林》是一部“與社會無限隔絕,一直凝視著死的陰影”(清水良典2006:153)的作品。而《舞》則“可以看出其有意提及社會,從這點上來說,是在為他1995年以后‘回歸社會’系列作品作準備,是以批判的目光審視社會現實”(清水良典2006:152)的作品,可見其在村上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至于選擇第23章的理由,筆者認為,選擇一部作品作為版本對比研究的對象時,既要考慮到反映作品主題的要素,即原作(作者)要素,又要考慮到翻譯中難以把握的因素,即譯者要素。作為原作要素,重要的是反映作品中心思想的“我”與“羊男”和“我”與“五反田”(“我”的分身)的對話部分。關于譯者要素,從譯者對于對象國的社會文化了解程度等角度考慮,翻譯中比較難以把握的以外來詞標記的樂隊名、樂曲名、歌手名、西洋料理名、服飾品牌名、高級轎車名等,應該作為選擇研究對象時考慮的一個要素。另外,作品中的議論部分、襯托主人公心境的環境描寫等在翻譯過程中體現邏輯性和感性的要素也應在考慮范圍內。
第23章主要由“我”與「ユキ」的對話構成。「ユキ」是“我”在札幌“偶然結識并把她帶回東京,具有特異功能的少女。在故事的展開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宮脅俊文1996:204)。并且,在這一章中除了有許多難以翻譯的音樂、西餐、外國名牌商品名外,還包含有關“羊男”的對話。另外,有主人公“我”對自己少年時代的回憶與感慨以及自然環境描寫等。
2 三位譯者的特點
2.1 從人名和車名的翻譯看三種譯本
三種譯本發行時間只有5個月的差異。最先翻譯的張孔群譯本(1991年1月)存在著漏譯、轉譯等許多問題。林少華譯本比張譯本晚了兩個月,沒有參考張譯本的痕跡,在三種譯本中顯得鶴立雞群。馮建新、洪虹合譯本最大的特點是沒有前兩位譯者存在的漏譯現象。讓我們首先從人名的翻譯看一下三位譯者的特點。
給作品中的主人公命名,是作者慣用的手法。但是村上卻使《舞》中的女性角色僅僅是一個能指的發音符號,所指卻不確定——他用片假名來標記在《舞》中登場的女性的名字。除了上文提到的「ユキ」,還有「アメ」、「メイ」、「ユミヨシ」等。但這些命名卻不是隨意拈來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比如,那個耳朵美得“無話可說”的女子名字被表記為「キキ」——這首先讓人想到日語中的動詞“聽”:“聽”本來就是靠耳朵來實現的。再有,仔細想一下kiki的發音:它與多個漢字對應,如“奇氣”、“奇奇”、“輝輝”、“暉暉”等。
翻譯時給這些能指以帶有所指意義的漢字,似乎是譯者的習慣。翻譯「キキ」這個貫穿故事始終的重要人物的名字:張譯為“菲菲”,林譯為“喜喜”,而馮譯為“吉吉”。這樣,問題便產生了:(1)把kiki譯成漢字后,原來的神秘感隨之消失。(2)林少華翻譯的“喜喜”的“喜”字,在漢語里有“喜悅”、“喜慶”、“高興”等意思,例如《白毛女》中的“喜兒”。不過,現代女性卻不會選擇這個名字。因為它沒有絲毫的時髦、高檔的色彩,而且讓人覺得俗氣。與此相對,張譯“菲菲”和馮譯“吉吉”聽起來更有感覺,遺憾的是二者的日語發音都不是kiki.可見,相對于村上春樹的深思熟慮,三位譯者的譯法顯得有些輕率,因而失去了原作中該人物的神秘感和空靈性。然而,臺灣時報出版社的賴明珠譯本把它譯作“奇奇”,“奇”有“珍奇”、“與眾不同”的意思,再加上有“奇奇怪怪”這個說法,考慮到「キキ」離奇地失蹤這個要素,也許更貼切。
下面看一下車名的翻譯。《舞》發表的1988年,正值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前夕。村上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通過“我”和“五反田”兩個關鍵人物的車的檔次、兩個人物的不同結局(乘坐外國高檔轎車的五反田自殺,而駕駛日產汽車——斯巴魯的我卻存活下來)的對比,批判和諷刺了如海市蜃樓般過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隱藏的不穩定因素。作品中五反田和“我”在中學畢業后第一次見面時,五反田用配有專人司機的公車——梅賽德斯去接“我”,兩人見面后以各自喜歡的車為話題緩解久違的尷尬。對于他們這次談話中出現的車名與五反田的“坐騎”,三位譯者的翻譯分別是:日語:ポルシェ、マセラティ、シビック、スバル、メルセデス;林譯:波爾西、馬賽拉提、西比克、雄獅/昴星、奔馳;張譯:波爾希、馬塞拉德、希比克、斯巴爾、梅塞德斯;馮洪合譯:波爾舍、馬賽拉地、西比克、斯巴爾、奔馳;現漢語名:保時捷(德)、瑪莎拉蒂(意)、思域(日/本田系列)、斯巴魯(日/富士重工)、梅賽德斯(德/奔馳系列)。即使對同一品牌的車,三種譯作相同的譯法很少。也就是說,這些在《舞》中當作資本主義商品社會高度發達的重要符號,在譯作中似乎沒有得到相應重視,或者這些符號在上個世紀90代的中國,對三位譯者或者對一般讀者來說,僅僅代表一部轎車而已。至于車的不同檔次,反映出來的主人公的年齡層、社會地位、生活品味、經濟狀況等情況不但是譯者甚至是讀者都不熟悉的信息,這種陌生帶來了譯者翻譯態度上的漠然,譯者并沒有像原作者一樣看重這些信息。如前所述,《舞》這部作品標志著村上“回歸社會”的開始,表達作者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諷刺與批判。如果那些代表經濟符號的標志性詞語不能很好傳達給讀者,無疑對原作是最大的缺憾和傷害。從客觀角度看,當時諸如外來語詞典等工具書匱乏,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這些高檔轎車對于大多數人還是陌生的。不單是車,其他諸如爵士樂、西餐、名酒、名牌服飾等也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不熟悉而不能與原作產生共鳴。經濟要素也許是村上作品直到90年代末期才在中國流行的深層原因。
2.2 三位譯者各自的特點
2.21 張孔群譯本
張譯特點之一是縮譯或誤譯較多,對難以翻譯的外來詞不譯。23章中有一段「ユキ」與從看守所里出來的“我”見面的場景。當時「ユキ」的裝扮是:彼女は今日はデヴィッド?ボウイのトレーナー?シャツを著て、その上に茶色の揉み革のジャンパーを著ていた。そしてキャンバス地のショルダー?バッグを下げていた(村上春樹1991:273)。這種在當時只有時髦大學生才有的打扮,突顯13歲女孩「ユキ」與眾不同,不過張譯本對此卻一字未譯,整段刪去(張孔群 1991:230)。又如,「ユキ」吸的弗吉尼亞牌細支女士香煙和“我”開的斯巴魯車只翻譯成“煙”(張孔群1991:230)和“車”(張孔群1991:232)。至于弗吉尼亞牌女士煙的原產國、歷史以及品牌暗示的的持有者的品味、愛好、生活方式、收入、消費檔次等信息都被譯者忽略了,而這恰恰是作者刻意向讀者傳達的。穿著、言談舉止可以理解為人物性格特征的符號,它們甚至可以反映出登場人物的個人修養、思想、學歷等重要信息。作者精雕細刻這些細節,是意圖通過它們給讀者輸送自己的言外之意——超過有限的文字意義的信息。但是因為譯者的主觀不譯,作者要傳達給讀者的信息就蕩然無存,作者和讀者的交流因為譯者的有意不配合而無法實現。
關于斯巴魯車。作品中主人公“我”當時賦閑在家,只能開普通人都買得起的“斯巴魯”。不過,“斯巴魯”與同樣是普通人買得起的大眾車“豐田”、“尼桑”、“本田”不同。它能使熟悉日本社會的讀者聯想到車主對車甚至人生的一種與眾不同的喜好和追求,從而暗示主人公外表普通,但性格與眾不同——這也是村上作品男主人公的普遍特點:外表看起來是普通年輕人中的一員,沒有任何特殊之處,而在其日常生活及言談舉止中卻有一種凌駕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殊性。譯者不譯,這種印象是不能傳達給那些只能靠譯本閱讀村上的讀者,村上與異國讀者之間的交流再次因譯者不合作而受阻。
2.22 馮建新、洪虹譯本
馮洪合譯本的特點有:幾乎沒有漏譯的部分;與張譯相同,雖然是三種譯本中最后出版的,但誤譯較多。從事研究或翻譯時,搜集前人的翻譯作為參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樣做,至少可以避免一些錯誤,給予讀者更正確的信息。但是這個合譯本卻沒有多少參考先前譯本的跡象。張譯無論在大陸還是港臺都是第一個譯本,沒有譯本可以參考。而馮洪合譯本沒有參考在它之前的兩個版本讓人費解。
2.23 林少華譯本
林少華是目前世界上翻譯村上文學最多的翻譯家。本節采用的研究對象是1991年3月南京譯林版的《青春的舞步》和2002年6月上海譯文版的《舞!舞!舞!》。
2.231 南京譯林版《青春的舞步》
這個譯本最大的特點是與前兩個譯本相比,誤譯很少。列舉如下:
①ウェット?スーツを著たまま砂浜に座って煙草をふかしていた(村上春樹1991:280)。譯文:(沖浪運動員只好上陸)穿上簡易潛水服坐在沙灘上吸煙(林少華1991:222)(上海譯文版改為“仍穿著簡易潛水服坐在沙灘上吸煙”(林少華2002:232)。
②そういうことは誰か他の人が考えることで、君が考えることじゃない(村上春樹1991:285)。譯文:那是別的什么人認為的,不是你那樣認為(林少華1991:226)(應為:那是該別人考慮的事,不是該你考慮的)。
林譯本的另一個特點是常常使用4字成語或類似成語。這種4字格的運用,有時候能有效傳達原文的意思。例如:
③プロだから。だいたい人が一人殺されてるんだ(村上春樹1991:272)。譯文:老手嘛,況且人命關天(林少華1991:215)。
③中成語“人命關天”的運用,簡潔有效地傳達原文的意思。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如果4字格運用過多或者不當,就會使譯文內容與原文不符,意思變得曖昧、難以理解。例如:
④僕は物事の新鮮な姿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た。それは素敵なことだった。匂いがきちんと匂い、涙が本當に溫かく、女の子は夢のように美しく……映畫館の暗闇は優しく親密であり、夏の夜はどこまでも深く、悩ましかった(村上春樹1991:276)。譯文:我可以捕捉到事物新鮮的風姿,那實在是令人快慰的時刻。香氣四下飄溢,淚水滴滴灼人,女孩兒美如夢幻……電影院里的黑暗是那樣溫柔而親切,夏日的夜晚深邃無涯而又撩人煩惱(林少華1991:218)。
這是“我”由13歲的「ユキ」聯想到自己13歲時發出的感慨。的確,“香氣四下飄溢,淚水滴滴灼人,女孩兒美如夢幻”這種對仗結構的運用,讀起來很上口,不過意思卻變得含混不清,與原文簡潔明快易于理解又略帶感傷的語體不符。另外,從譯文本身看,原文“素敵”修飾「こと」(事情),而譯文中出現的“時刻”在原文中并沒有,屬于譯者主觀添加的部分。另外,將“素敵”翻譯成“令人快慰”是否妥當有待商榷。
2.232 上海譯文版《舞!舞!舞!》
上海譯文版第23章與南京譯林版相比,有52處(此數據不包括相同內容)作了修改。換句話說,2002年譯文版不是重新作了翻譯,而是把1991年譯林版作了修訂。52處改動的地方從內容上來看,包括句子之間的標點符號的改動7處,音樂方面的外來詞10處,車、服裝、飾品等品牌名5處,還有上文提到的對誤譯的更正一處。另外,對「味に勢いがある」的翻譯由“味道勢不可擋”改成“味道沖得勢不可擋”。以上共計24處。其余28處,則是把“犯人”改成“罪犯”,“青菜”改成“蔬菜”,“時分”改成“多時”,“凄婉”改成“哀婉”,“200”改成“兩百”,“電話交換員”改成“電話接線員”,“女孩兒”改為“女孩”之類的同類詞互換,還有“(食欲也多少)上來”改為“(食欲也多少)上來了”之類的助詞補充,“林蔭”改為“林陰”、“失望似地說”改為“失望似的說”之類的錯字訂正等。
在出版新譯版前,改正誤譯、補充意思不足、改正錯字等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過,對于占變更部分40%的同義詞互換是否必要,則值得考慮。筆者認為與其花費時間去變動一些對讀者閱讀影響甚微的東西,不如去訂正誤譯,補足漏譯等更為重要。例如,對于下文的劃線部分,兩個譯本均沒有譯出。
⑤でもそれは起こるの。見えるのよ。でももう何も言わない。何か言うとみんな私をお化けって呼ぶから。ただ見ているの。ここでこの人は火傷するじゃないか、(村上春樹1991:282)。譯文:但畢竟發生了,而且我能看見,使我覺得此人可能燒傷(林少華1991:224,2002:234)。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結論:譯者在出版新譯本之前,并沒有將舊譯本與日語原文對照,而只是對舊譯版中的譯文進行一些改動。
3 譯者的翻譯態度
對三位譯者來說,最大的難度也許是外來詞的翻譯。這些代表泡沫經濟時期的商品符號以及那些許多研究者忽略的、在作品中津津樂道的、構成作家標志性符號的美國元素(爵士樂、西餐、名牌煙酒)等,被譯錯或忽略不譯,作者構建的源語文化氛圍就不能傳達給那些只能靠譯文欣賞作品的讀者。“翻譯是復雜的文化交流活動,承擔著精神交流的中介作用,譯者的作用不可忽視。作為橋梁,翻譯的首要職能是溝通。因此,面對作者和讀者,面對出發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譯者應采取怎樣的態度,應采取怎樣的溝通方式,是翻譯研究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許鈞1997:7)
不同文化背景、翻譯目的、譯文用途,勢必產生不同的翻譯策略和翻譯認知。文學翻譯與其他翻譯不同,它要求譯者最大限度地忠實、再現原文以滿足讀者對作品的審美期待,作者則理所當然地期待自己的創作意圖原封不動傳達給讀者。正因為翻譯是一種交際活動,我們必須尊重話語的原發者。對于“翻譯就是再創作”、“翻譯文學不應是外國文學而應列為中國文學”等主張,如果從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外一種語言的角度說,翻譯確實是一種再創作;用漢字二次表述的外國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說也算是中國文學,但不能由此就說譯者可以改寫原作。
全球化背景、網絡時代,獲得信息的渠道四通八達,文學賦予的文學以外的政治性或功利性使命正逐漸弱化,而讀者強烈需求其本身作為藝術的審美使命。另一方面,文學正在經歷著商品化洗禮,出版商的宣傳和炒作、不可避免的營銷策略又使得翻譯文學在消費前已經披上五顏六色的外衣,這勢必影響其審美使命的純潔性。對于被商業因素化妝了的翻譯文學,作為譯者,應該做的不是再另外為它涂抹上一層脂粉,而是盡最大限度地隱蔽自己,展現原作。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全作品1979-1989⑦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M].講談社(第1刷),1991.
村上春樹.張孔群譯.舞吧舞吧舞吧[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
村上春樹.林少華譯.青春的舞步[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1.
村上春樹.林少華譯.舞!舞!舞![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村上春樹.遠い太鼓[M].講壇社(文庫本·第32版),2006.
宮脅俊文.村上春樹作品詳細ガイドマップ[J].ユリイカ臨時増刊號第21巻第8號総特集『村上春樹の世界』,1996.
清水良典.村上春樹はくせになる[M].東京朝日新聞社(第1版),2006.
藤井省三.村上春樹の中の中國[M].東京朝日新聞出版社,2007.
藤井省三編.東アジアが読む村上春樹[M].于桂玲.中國版『ダンス ダンス ダンス』の版本研究[M].WAKAKUSASHOBO,2009.
許 鈞.關于翻譯理論研究的幾點看法[J].中國翻譯,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