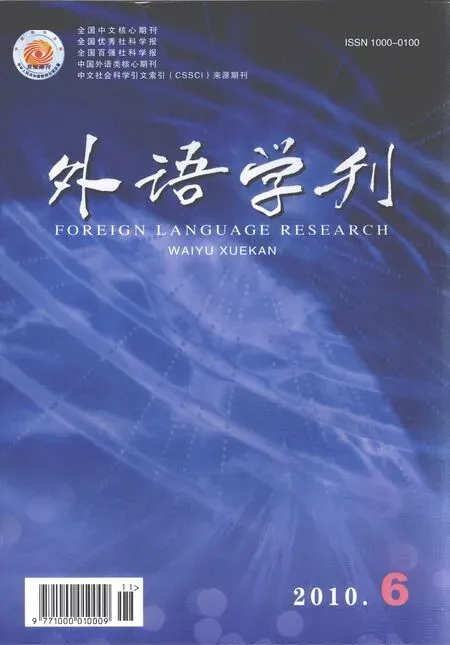術語研究中的辯證法*
葉其松
(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研究中心,哈爾濱150080)
既然辯證法可以用于語言研究,那么也可以用于術語研究,因為術語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研究對象。
現行的國家標準“術語工作 詞匯 第一部分:理論與應用”(GB/T 15237.1-2000)將“術語”定義為“稱謂專業領域內概念的詞或詞組。”這就決定了術語具有雙重身份,即術語既是語言詞匯系統的組成部分,又是專業領域概念系統的組成部分。這種雙重特性是術語矛盾特性產生的根源,由此可以衍生出若干組對立方面。
1 異-同
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一句話:任何認識都是從確認異和同開始的(Султанов 1996:2)。這句話意味深刻,因為外部客觀世界原本是個連續統一的整體。當一個個客體從中區分出來時,異和同就已包含其中了,且兩者是相依而生的:客體的存在就是與其自身的同,這種同是以與其他客體的異為條件的;但沒有與自身的同,與其他客體的異也無從談起。
因此,異同就與劃分界限的問題緊密聯系起來了。這自然使人聯想到“術語”所對應英文詞term的詞源意義——“界線、邊界、終點”。界限問題也由此成為術語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什么是術語,什么又是普通詞,這首先就是劃分界限的問題,這關乎術語在現代語言詞匯系統中的地位。過去語言學及其分支學科詞匯學、詞典學等主要研究的是普通詞,術語作為具有社會方言性質的、帶有某種修辭色彩的詞匯類別,被關注得不多。但術語學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原因在于:只有將術語從詞匯體系中分離出來并確定其與普通詞的界限,術語學才能從詞匯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科學。但對于該如何劃界,學界意見不一:標準化學者傾向于采取將術語與整個詞匯系統對立的極端化方法,他們認為這是實現術語標準化的前提。一些學者主張從功能的角度區分術語和普通詞,最早提出這一觀點是 Г.О.Винокур:“術語不是特殊的詞,而是用作特殊功能的詞”(Винокур 1939:5)。Р.А.Будагов 后來重復這一觀點:“大多數情況下,術語不是特殊的詞,只是詞的特殊用法。普通詞本身也能被術語化”(Морозова 2004:11)。也有學者主張術語是詞匯系統中與普通詞性質不同的詞。В.В.Виноградов 指出,“術語具有稱名功能和定義功能。一方面,它們是表達手段,也就是普通符號;另一方面,術語是邏輯定義的手段,也就是科學術語”(Морозова 2004:11)。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后來發揮了這一思想,他區分了術語的“列克西斯”(lexis)方面和“邏各斯”(logos)方面。最后一種觀點為后來的大多數術語學家所接受。С.В.Гринев認為,術語的性質在于:它是在詞匯單位的基礎上疊加相應概念系統的特征。
另一個界限是有關術語與專業詞匯其他單位之間的,其中包括兩個類別:一是共時層面的,即術語與名稱(nomen)、職業詞(professionalism)的界限問題;另一個是歷時層面的,即術語與原始術語(прототермин)、類術語(терминоид)和初術語(предтермин)的界限問題。
術語與名稱的關系問題早在19世紀已由英國哲學家W.Whewell提了出來,但后來的西方學者不大注意兩者的區別,他們習慣于把后者看成前者的一個類別。不過俄國學者卻從一開始就將兩者明確區分,我國學者鄭述譜教授對此曾有專文論述(鄭述譜2006:4-8)。術語和職業語的區別在于后者的使用范圍更為有限,此外帶有一定的評價、表現力色彩,而術語則是專業詞匯中使用范圍最廣的,且在學科領域內不帶有評價和表現力色彩。
術語與原始術語、類術語和初術語的差別體現為它們分別對應概念發展的不同階段。辯證邏輯認為,概念的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即從直觀表象到前科學概念、再由前科學概念到科學概念(彭漪漣1992:153)。原始術語基本上和前科學概念相對應,其特點在于:一方面,它是抽象思維的結果,能夠反映同類事物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它還不夠準確,且沒有形成系統。對原始術語和術語進行區分有助于澄清術語學的根源問題,即現代科學出現之前有沒有術語?古希臘哲學有關名稱來源的討論、中世紀的名實之爭能不能算作術語學問題?按照現代術語學的說法,真正的術語是在文藝復興之后伴隨近代科學的興起而產生的。至于類術語和初術語,它們稱謂的是科學發展過程中尚未完全確定的概念,因此尚不符合術語的要求,類術語和初術語要么內容上過于寬泛、不夠準確,要么形式上不夠簡潔等。
以往詞匯學在研究術語和普通詞的關系時,普通詞被看作“標準”,術語是多少偏離標準的單位;而在術語學框架內研究術語與專業詞匯其他單位,如名稱、職業詞、原始術語、類術語和初術語的關系時,術語被看作“標準”,而其他專業詞匯是多少偏離標準的單位。可以想象,這種研究角度的差異只有在術語學成為獨立學科后才能出現。
辯證思維包括相互矛盾中的兩個方面,以上我們只提到術語與普通詞、術語與其他專業詞匯的區別問題,下文將論述對立面之間是如何相互運動和轉化的。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А.說過,“就算術語不單單是詞,就算它不是普通詞,就算它比較‘睿智’,就算可以使它合理化,甚至它是想出來的;但術語首先是詞,而且術語應該是語言詞匯系統的正常成員,即便不是正常成員,也不會與這一系統相背”(Буянова 2002:64)。列福爾馬茨基這段話說明,術語和普通詞之間的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術語可以通過“非術語化”進入普通詞匯之中,比如“反饋”(feedback)、“邏輯”(logic)、“進化”(evolution)等都由術語進入普通詞之中。普通詞也可以通過“術語化”進入專業詞匯之中。比如,memorary(記憶力),operation(操作;運行),programme(節目)成為計算機術語“存儲器,內存”、“運算指令”、“程序;編碼指令”等。
異與同的辯證法還可以解釋術語詞典和語文詞典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兩者之間存在若干區別,這體現在:在編纂方法,術語詞典是稱名學的,即從概念到名稱,一般先確定概念,然后賦予一個合適的名稱;語文詞典是語義學的,即從名稱到概念,從現有的名稱出發,然后再解釋其意義。在收詞范圍上,術語詞典只收錄學科領域內的術語,而語文詞典收錄的是普通詞。在定義模式上,術語詞典要求確定術語所稱謂概念的內容,一般優先采用嚴格的科學定義;語文詞典則一般只進行釋義。另一方面,術語詞典和語文詞典的區別也不是不可逾越的,因為在編纂方法、詞條安排、結構設計等很多方面,術語詞典和語文詞典都有相近似之處。作者曾按照若干參量對同一領域內的多部術語詞典和幾部語文詞典的結構進行過比較、分析,結果證明:兩者在結構上十分接近(葉其松2009:127-130)。
2 主觀-客觀
А.А.波鐵布尼亞(Потебня)曾將詞的意義分成近義(ближа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和遠義(дальне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兩類。他指出,近義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帶有民族性,可以滿足說話人和聽話人相互理解的需要,是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遠義則是因人而異的,但從個人理解也可以產生高度客觀的思想,即科學思想,遠義是其他科學研究的對象(Звегинцев 1960:128)。在以上論述中,主觀和客觀之間的辯證法已清晰可見了。
與普通詞不同,很多術語都是某個研究者創造的。比如,物理學術語“慣性”(inertia)是伽利略創造的,化學術語“氧”(oxygen)是拉瓦錫創造的,生物學術語“進化”是達爾文創造的。科學家在創造和使用術語時,不可避免會帶有個人主觀的因素。但科學思想要為世人所接受,又必須是非常客觀的。美國科學家、科學學家P.Choen指出,任何科學思想的發展要經過若干階段:第一階段就是當一個科學家(或一個科學家小組)提出一種新的方法、概念或理論,并引入新的表述(一般情況下是術語——作者);第二階段就是形成對此新方法、概念或理論的信仰。前兩個階段都是在私下進行的;第三階段就是讓這一新思想在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之間流傳;最后一個階段就將之以文字形式公諸于眾(科恩1998:36-40)。科恩的以上論述大致概括了科學思想和術語由主觀走向客觀的基本步驟。術語只有擺脫了個人的主觀性,成為已被普遍接受的客觀概念的稱謂手段,才能成為保存、傳遞信息的知識單元。
同時,術語中包含的知識并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科學的發展,新的研究者會對原有的客觀知識增加新的主觀認識,甚至徹底推翻術語中原先包含的知識。這時的術語研究又從客觀走向主觀,這也是科學發展、知識更新的必然途徑。
3 民族-國際
這對矛盾與主觀-客觀之間的矛盾類似。雖然科學思想的本質是國際的,但任何術語都必須借助民族語言的形式表達,因此又是民族的。俄羅斯術語學家 М.Н.Володина說過:“作為專業概念的語言表達系統,術語的特點在于:形式上是民族的,內容上是國際的,這是因為人類思維的普遍性決定了科技發展規律的一體化(Володина 1997:99)。
這對矛盾在科學發展的很長時期內并不突出,因為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希臘語、拉丁語長期處于國際語言的地位。但文藝復興之后,意大利語、法語、英語、德語等民族語言的逐漸興起。拉丁語的國際語言地位受到極大挑戰,并于18世紀完全退出歷史舞臺。“17與18世紀,取代了教會大一統思想的民族主義思想開始明朗化。不但科學,就是一般的思想,也都具有了極顯著的民族色彩。各國的學術活動各自分道揚鑣,歐洲各國的國語也代替了拉丁語,成為科學寫作的工具。”(丹皮爾1997:389)
在民族語言的形成和發展階段,學者往往傾向使用民族語形式表達新概念。各種各樣的語言凈化思想就是一個證明,學者們擔心借入術語數量的增加會影響本民族語言的純潔,因此拒絕從外語中借用術語,甚至用本民族術語替代已有的、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術語。有時語言凈化問題還同民族、政治等敏感問題聯系到一起,走向可怕的極端。上個世紀30年代,希特勒上臺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曾提出極端的民族語言政策,要求用德語詞Rundfunk,Funk替代已經廣泛使用的國際詞Radio(無線電)。
但國際性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規律。“國際主義是科學最特殊的特征之一。”(貝爾納2003:226)“科學……不過,他又是屬于一個講著一種世界性語言的世界共同體;他在波士頓、東京、莫斯科、斯德哥爾摩、北京、新德里、達卡,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樣。盡管它自身具有種種個性,但他的調查結果、報告、發現,都必須接受其同行的普遍檢驗,這些同行們越過所有個人興趣的壁壘,越過一切情趣,改造舊事物。”(瓦托夫斯基1989:7-8)一方面,民族術語必然跨越地域界限,進入其他國家、民族的術語體系之中,并發展成為國際術語。通常情況下,優勢學科領域的民族術語成為國際術語的機率更大,目前國際通用的音樂術語很多來自意大利、航海術語很多來自荷蘭,這與這些國家在這些領域曾居領先地位有關。英語國家,尤其美國目前在各個領域所處的優勢地位,決定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最新術語都來自于英語。另一方面,各民族不斷從其他民族語言中借入大量術語成分(terminological element)。“術語成分”這個術語是由俄羅斯術語學派的創始人Д.С.Лотте首先提出來的,它是構成術語的最小表義單位,可以是詞素、詞,甚至詞組。術語借用的一個重要來源還包括希臘語和拉丁語構成的國際術語成分,de-,масro-,micro-,теле-等已被借用到很多印歐民族語中。實踐證明,單純排斥國際術語或其他民族術語并不利于本民族術語的形成和發展。
4 靜態-動態
索緒爾曾提出區分靜態語言學和動態語言學,這對術語研究同樣具有啟發。術語研究長期以靜態研究為主,這體現在:一是從共時層面描寫術語的結構和語義特點;二是將術語作為一個確定的語言單位來研究。
對于術語這樣復雜的研究對象,從靜態研究入手并沒什么不妥,起碼有助于確定研究范圍,而且這種研究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后來發現;靜態研究并不足以認識術語的本質。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研究者開始研究領域術語的發展歷史。實踐證明,這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譬如,研究術語構成的目的是要確定最有效的術語構成模型和最佳的構成方法,但只研究現有術語的構成狀況,得出的結論往往有所偏差。原因在于:術語構成模式在一定時期內容易受到特殊因素的影響。但是通過分析學科領域術語的發展歷史,專家們發現:學科領域所處的發展階段與術語構成模式之間存在著某種對應關系。語義法(從普通詞、其他語言或學科借入術語)是學科領域發展之初主要的術語構成方法,之后是形態法(前綴法、后綴法等),學科領域發展成熟后多用形態-句法構成方法(如合成法、省略法等)和句法構成方法(構成術語組合)。因此,分析學科領域目前所處的階段,就很有可能推斷目前流行并預測將來可能流行的術語構成模式和方法。
術語研究中靜態和動態的辯證法還表現在:術語不僅可以作為確定的語言單位來研究,還作為在言語中使用的單位來研究。這種研究可以從兩個角度入手:一是對術語進行篇章分析,研究術語在不同類型語篇,如學術專著、一般科普讀物、文學作品等中的使用情況,借此確定篇章的類型。二是對篇章進行術語分析,調查并統計某一領域術語或單個術語在特定語篇中的使用頻率,借此確定同義術語、多義術語的使用情況。
可見,術語的靜態研究是進行動態研究的基礎和前提,而動態研究又為豐富和拓展靜態研究提供保障。
5 一般-個別
科學學認為:學科存在的條件之一就是形成能夠解釋該領域內所有現象的一般理論。同其他學科一樣,術語學的一般理論也是圍繞其研究對象——術語展開的。
有學者提出:作為語言學研究對象的語言應該是單數,泛指人類的語言。那么,作為術語學研究對象的術語也應該是單數,包括不同語種、不同學科領域內的術語。的確,術語的特性應該適用于可以歸入“術語”名下的所有符號單位。術語學的一個任務就是研究與術語有關的一般理論。
但不同學科領域術語的性質又不盡相同,自然科學術語與人文科學術語之間的差距甚大。俄國術語學家А.Д.Хаютин曾指出這種差別:“(1)自然界中具有自發的、不知不覺的力量,而社會歷史則是人為的,受其意識與意志力左右;(2)社會科學具有明顯的階級性;因為在發現與運用社會發展規律中,階級傾向表現明顯;(3)自然科學甚至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也具有很強的唯物主義傳統,而社會科學則隱約帶有唯心主義的性質。”(Хаютин 1972:89-90)法國詞典學家、術語學家A.Ray根據學科性質的不同將術語分成3類——“純”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的術語、技術領域的術語和人文科學的術語。其中,第一類術語主要來自英語、法語、德語等被廣泛使用的幾種語言及希臘語和拉丁語,因此大多是跨語言和跨文化的,具有國際化的趨勢;第二類術語與技術的運用有關,起初依附于與一種語言或同一語系的幾種語言;第三類術語往往是某一語言,甚至某一集體所特有的(Ray 1995:88)。不僅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人文科學之間,就連自然科學內不同學科之間的術語也有很大不同。比如,基于推理的數學、邏輯學術語和基于實驗和觀察的化學術語就有很大不同。
不同學科領域術語性質的不同使得研究者從一般走向個別,類型術語學(typological terminology)、對比術語學(contrastive terminology)等分支學科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的,這些研究有助于更為全面地了解術語的特性。
6 標準-偏差
術語研究始于標準化工作。現代術語學的創始人、奧地利學者E.Wüster所寫的術語學劃時代著作《在工程技術中(特別是在電工學中)的國際語言規范》就與此內容密切相關。
既然是標準化,就要遵照一定的規范,并使術語符合一定的標準。為此,國際上和各國的標準化組織都制定了相應的規范文件,如國家標準《術語工作 原則與方法》(GB/T10112-959)、《概念與術語的協調》(GB/T 16785-1997)、《術語工作 詞匯第1部分:理論與應用》(GB/T 15237.1-2000)等等。經過標準化的術語應該滿足一系列要求:具有定義、理據性、系統性、簡潔性等等。
但即便在術語標準化工作之中,也難免有偏離標準的情況出現。鄭述譜教授在《術語標準化中的辯證法》一文中對此已有相關論述。這里著重討論一下術語翻譯中的標準與偏差這對矛盾。
翻譯術語通常要借助該學科領域的雙語(或多語)術語詞典。但對于很多新興學科領域,術語并沒有經過整理,術語學的術語的情況就是如此。此時,術語翻譯依據的標準就是外語術語的定義。術語“термииология”可表示3種意義:(1)對術語、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一種研究;(2)用于收集、描寫和表征術語的一套方法;(3)某一主題領域的詞匯。
那么,與上述三種意義相對應,“термииология”則應該被相應地譯成“術語學”、“術語方法”、“術語集”。其中,“術語集”中的“集”是不能省略的,因為“термииология”在英語表示一個集合概念,和“термин”(術語)是有明確區別的。
但考慮到漢語的表達方式,尤其與表學科名稱的名詞連用時,“集”就被省略了。俄語用“физиче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химиче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漢語用“物理術語”、“化學術語”,而不說“物理術語集”、“化學術語集”。此時,由于原文術語定義中的集合概念就沒有體現出來,翻譯就出現偏差了。
過去的研究對術語中的邏各斯方面過于強調,而對術語的復雜性、異質性等認識不足,致使術語與普通詞、其他專業詞匯的關系、同義術語、多義術語等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今后要充分運用辯證思維的方法,從術語“邏各斯”和“列克西斯”雙重特性的矛盾運動出發,進行整體研究,尤其加強不同學科領域術語系統的特性,漢外相同或相近學科領域術語的對比、術語在不同篇章中的使用和功能等過去關注不多或尚未涉獵的研究領域和方向的研究。
鮑亨斯基.當代思維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馮 契.哲學大辭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
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科 恩.科學中的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列 寧.列寧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彭漪漣.概念論——辯證邏輯的概念理論[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楊連生.科學學[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
葉其松.Lexicography與terminography辨析[J].外語學刊,2009(3).
鄭述譜.術語學核心術語辨析[J].術語標準化與信息技術,2006(1).
鄭述譜.試論術語標準化的辯證法[J].中國科技術語,2008(3).
Rey A.Еssays on Terminology[M].Amsterdam/Philadelph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Буянова Л.Ю.Термин как единица логоса[M].Краснодар:Кубанский гос.Ун-т,2002.
Винокур Г.О.О некоторых явлениях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усской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A].Татаринов В.А.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Классики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Очерк 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C].Москва: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1994.
Володина М.Н.Теори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оминации[M].Москва:Изд-во МГУ,1997.
Звегинцев В.А.История языкознания XIX-XX веков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C].Москва:Гос.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1960.
Канделаки Т.Л.Значен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системы значений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логий[A].под рекдацией Бархударова С.Г.Проблемы языка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Логические,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 историконаучные аспекты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C].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0.
Лосев А.Ф.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M].Москва:Правда,1990.
Морозова Л.А.Терминознание:основы и методы[M].Москва:Прометей,2004.
Султанов А.Х.О природе научного термина,Проблемы философии языка[M].Москва:Изд-во РУДН,1996.
Хаютин А.Д.Термин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M].Самарканд:СГУ,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