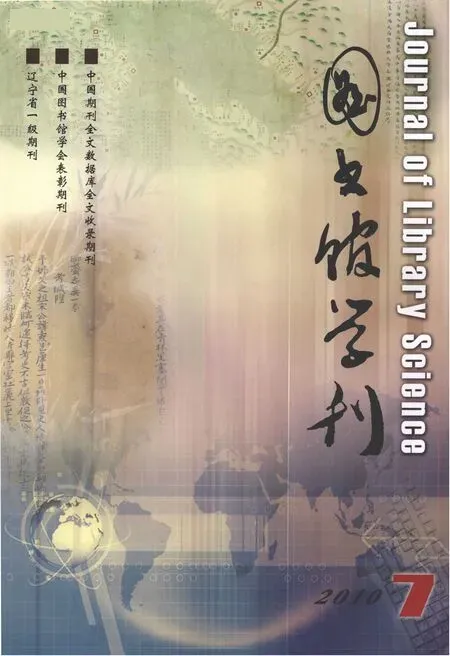地方文獻概念辨析
姜浩天
(遼寧省圖書館,遼寧 沈陽 110015)
姜浩天 男,1970年生。本科學歷,館員。
不久前,與幾位同事談論起有關地方文獻的話題。幾位同事就“地方文獻”的概念及其范圍等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不歡而終,局面非常尷尬。本著求證學習的心態,筆者于近日查閱了有關地方文獻的專著和大量學術論文,但從中很難發現關于地方文獻的明晰概念和相對統一的、明確的詮釋,各級各類圖書館在地方文獻收藏范圍的劃定,以及地方文獻特色數據庫的建設上更是各行其是,五花八門。鑒于此,筆者認為,我國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需要進一步規范,而明確地方文獻的概念、界定地方文獻的范圍則是保證地方文獻工作上質量、上水平的基礎。
長期以來,關于地方文獻的解釋,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目前仍沒有一個極具說服力的、為大家共同認可的定義。通常人們對地方文獻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廣義”的地方文獻包括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史料;“狹義”的地方文獻專指地方史料。
正是由于理論界對地方文獻概念內涵的多重解釋和描述,導致了各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標準各異、參差不齊。正是由于對地方文獻概念的模糊不清,致使一些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工作者難以準確把握“地方”的范疇,從而造成了地方文獻的重復收藏。正是由于對地方文獻內涵缺乏深刻的理解,導致許多公共圖書館在建設地方文獻數據庫時,難以形成固定的地方文獻收錄標準,從而造成了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的現象。
究竟什么是地方文獻?筆者認為,無論是狹義的解釋還是廣義的闡釋,從本質上講,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都不能準確、全面地揭示地方文獻的本質內涵。
“狹義”的地方文獻是指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指內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區域性文獻。它不管文獻的出版地和出版形式,也不管文獻編著者的籍貫和文獻的載體形式,只要內容與本地有關,無論是涉及本地的地理位置、建制沿革、名勝古跡、風俗人情、物產資源、語言文字,還是涉及經濟、文化教育等,都可視作地方文獻。地方史料以文獻內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為劃分地方文獻的唯一標準,凸顯了地方文獻的地方特色和“資政、勵志、存史”的功能,但“狹義”的地方文獻概念充其量只是從一定層面上揭示了地方文獻的本質特征——地方區域性。事實上,“地方史料”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專指,并不足以完全涵蓋所有的地方文獻,因為具有“地方區域”特性的文獻還有很多,如果以《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來定位,帶有“地方區域”特征的文獻可能散布于每一個大類。可見,狹義的地方文獻概念將人們的視線引入了“死胡同”,很多地方文獻工作者僅僅將地方文獻工作的基點落在“地方史料”,即《中圖法》“K29地方史志”的范疇。
“廣義”的地方文獻包括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史料,其內涵外延與“狹義”概念相比寬泛了很多,使地方文獻的范圍具有了更廣的包容性,但實踐中,并非所有的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著述都屬于地方文獻的范疇。
就地方出版物而言,它是指某一地域范圍出版的出版物,包括圖書、紙、期刊、音像制品,甚至是網絡信息等。可以是印刷型的,也可以是縮微型、視聽型、機讀型的,地方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地域在某一時期的科學文化發展水平,但由于其內容繁雜,涉及各個領域和學科,所以,多數地方出版物在內容上并不具備地方特色。如果我們不加區分、一概而論地將地方出版物作為地方文獻收藏,勢必造成地方文獻的龐雜無序,地方文獻的特色和優勢難以顯現,我們建設地方文獻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義。可以說,在文獻內容上不具備地方特色的地方出版物應排除在地方文獻收藏之外。
同樣,地方人士著述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目前人們關于地方人士也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地方人士指籍貫為本地籍的人士;“廣義”的地方人士包括本地籍人士和居住、工作在本地的外地籍人士,具體有這樣3種情形:①籍貫為本地且工作、居住在本地者;②籍貫為本地,工作、居住在外地者;③籍貫為外地,長期工作、居住在本地者。不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地方人士,因為工作生活環境和人生經歷的關系,他們與本地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在他們的著述中,有一部分或多或少都會帶有明顯的地方性,這部分著述理應作為地方文獻收藏。但在地方人士的著述中,也還有相當一部分并不帶有明顯的地方特征。這些文獻就應該排除在地方文獻之外。
筆者認為,給某一概念下定義不能無視事物的本質,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無限擴大事物本身的內涵與外延。從地方文獻的內容來看,它所記錄的是關于某一地區自然、人文各種現象的描述。所揭示內容的“地方區域性”是地方文獻的本質特征。所以我們給“地方文獻”下定義不能舍棄“地方區域”這一本質屬性。我們首先應該認識到地方文獻是“文獻”的一種特殊形式,對這一特殊的文獻概念所作的詮釋必須以“文獻”的基本概念作為重要參照,并加以特別的概念限制,以求所下定義的準確、規范和嚴密。
《中國文獻著錄總則》(GB3792.1-83)中對“文獻”所下定義為:“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這一定義簡潔明快,意蘊深刻,短短的10個字卻包容了構成文獻的3個要素,即記錄、知識、載體。這一定義應該成為我們對文獻進行細分并加以描述的基礎。以往關于地方文獻的定義盡管有很多,但仔細品味,大都存在某些缺失或遺憾,因為它們大都采用描述的方法來給概念下定義,不可能給地方文獻一個明確的界定。我們知道,給概念下定義是有其規則的,任何描述的方法、否定的方法、比喻的方法,都是給概念下定義應該回避的。而用肯定的方法來陳述事物概念本身所蘊含的本質和規律才是我們給概念下定義應該堅守的原則。
立足于“文獻”的標準化解釋,系統考察并借鑒以往眾家“地方文獻”定義之長,筆者斗膽對“地方文獻”作如下詮釋:“記錄有某一地方相關知識的載體。”這一定義不僅能夠囊括構成文獻的3個要素,更為主要的是突出了地方文獻的“地方區域性”特征,具有廣泛的涵蓋性,符合當代文獻發展的特點和未來趨勢。它正像“文獻”標準化定義一樣,不僅可以將分散在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的“地方文獻”囊括其中,而且也能夠將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各種出版形式、各種載體形式的文獻包羅其中,簡潔曉暢,通俗易懂,界限清晰,準確嚴密,可為地方文獻理論研究者和具體實踐者參考。
[1]鄒華享.關于地方文獻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1):60-65.
[2]羅力可,劉雪萊.地方人士著述采集理論新探.圖書館,2000(3):45-48.
[3]賈少巖.縣市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的幾個問題.圖書館,2000(4):72-73.
[4]鄒華享,張勇.新技術環境下的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圖書館,2000(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