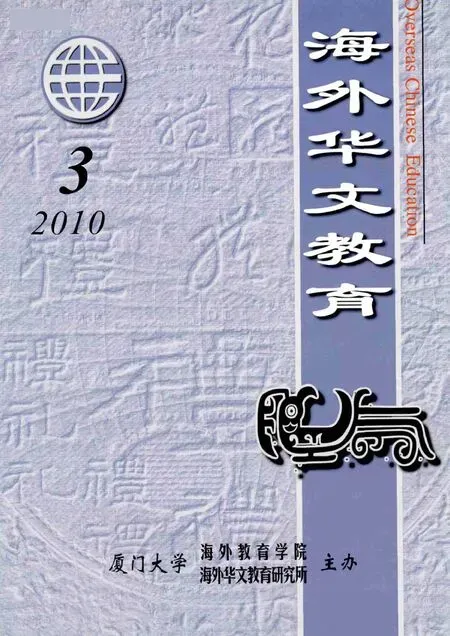語言知識的認知特性與教材的編寫策略
方環海
一 引言
近年來,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得到了海內外的一致關注,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過去學界一直強調漢語國際推廣過程中存在的三難現象,也就是三個關鍵性環節,即教材、教師、教法。這種認識很到位,三個關鍵環節呈現三位一體,其中教師是核心(所謂“三難”,實為“一難”,教師核心的觀點來自于廈門大學鄭通濤教授的指教——作者注),教材與教法是兩翼,教材更重要,沒有合適科學的教材,教師就無本可依,教法也就難以得到有效應用與充分體現。無疑這是漢語國際推廣表現出來的顯性問題,確實也是站在漢語推廣的發展戰略和推廣過程的有序實現上看的。
再深入一步看,要使漢語國際推廣工作的科學開展,取得更好的實際成效,并且能夠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高水平的本體研究作為漢語國際推廣戰略的根本支撐與工作基礎,離開了漢語的本體研究,漢語國際推廣必然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根基,軟弱無力。上面說到的三位一體關系中的教材就是漢語知識體系認識上的具體表現,確實如此,如果沒有對漢語本體理論知識的系統了解,就不可能有科學內核的教材,如果沒有對漢語本體理論知識的深入闡釋,也就不可能達到很好的教學效果。正如陸儉明(2000)所言,以培養語言交際能力為主要目的漢語教材,必須奠基在基礎研究之上,否則基礎研究的不足將使得教材編寫的隨意性永遠難以克服。
所以,對漢語國際推廣而言,教師、教材、教法等三個環節構成的三難現象,只是顯性的表層現象,而漢語本體理論知識體系的認識與規律的闡釋,則是隱性的深層,表層的問題是受深層制約的,也是由深層生發出來的。本文擬先從語言知識的本質入手,探討語言知識的認知屬性問題,由此提出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認知策略。
二 語言知識的認知屬性
(一)認知視域里的語言知識
認知科學研究內容主要包括知覺、學習、記憶、推理、語言理解、注意、情感和統稱為人類智能的高級認知現象,涵括語言學、人類學、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等多個領域,是多學科交叉研究發展的領域,也是當今最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語言學由此在現代認知科學體系中占據自己的獨特位置。雖然語言學只是認知科學的一個領域,但以探索人類語言結構(包括語音韻律、句法結構、語義關系等)的本質和規律為己任的語言學研究在認知科學體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
最近十幾年來,語言學與認知科學已結合成一門新的邊緣學科,提出了許多全新的觀點,并且這種新的探索方興未艾。語言知識(關于意義和形式的知識)從根本上講就是概念結構,即句法、形態、語義、音系表征都是概念性的,對語言知識的本質而言,任何語言學理論也都必須回答這樣三個基本問題:
1.語言知識是什么?當代認知科學認為,在人類的心智大腦中存在著一套語言認知系統,表現為一套數量有限的原則和規則系統,高度抽象的語法規則構成了語言應用所依靠的語言知識。
2.語言知識是怎樣習得的?理論上的假設是人類心智中存在著一個內在的天賦的機制,先于后天的經驗而存在,這一天賦機制應該建立在現代科學體系的理論基礎之上,是由生物遺傳決定的認知機制系統,能夠得以正常地生長與成熟,又可稱為“心智器官”(mental organs),構成人類語言知識的是其中一個子系統,可以稱為“語言機能”(language faculty)。
3.語言知識是怎樣使用的?(Taylor 2002)人類語言使用的創造性特征,超越了物質概念能夠解釋的范圍,只能到心智大腦中獲得解釋,設定于心智大腦中的其他有關認知系統,對語言認知系統的功能的關系,說到底也就是人類認知系統的分工與合作問題。①
不同的語言學理論,包括結構主義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對這些問題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人類的認知體系里,語言知識系統具有復雜的層級性,它是由一套音位系統、音義結合的詞匯系統和用以編排組織詞語的句法系統組成的。在這三大系統中,句法系統最為抽象,主要存在于深層的語言結構之中,尤其對于漢語來說,語法形式缺少顯性的形態結構的變化,漢語的語法較多的是與語義相聯系的隱性語法特征。(胡明揚,1992)
心理科學認為,人類的語言知識可以分為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這種分層很重要,這樣,陳述性知識是一種靜態的知識,即回答“人類的語言知識是什么”的問題,而程序性知識則是一種動態的知識,回答“人類的語言知識怎么做”的問題。研究證實,人類的語言學習包括兩種學習方式:外顯學習和內隱學習,其中,外顯學習是一種有意識的主動學習方式,在教師指導下所進行的課堂教學多是外顯學習,例如學習生詞、語法等關于語言知識系統的學習過程,學習者明了學習的內容與要求;內隱學習則與外顯學習相對,是無意識的學習方式,指在實際語言運用過程中生成的語言技能,所學的東西是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可以表示如下:

事實上,大量的語言學習方式都是內隱學習,說到底,陳述性知識是外顯的,是可以學習的,而程序性知識則是內隱的,是由陳述性知識轉化而來的一種技能,如何運用語言,得靠學生自己在交際過程中去體驗、歸納和領悟,教學中系統地講授語法的基本知識,最根本的目的還是幫助學生掌握語法規律,來真正提高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實際能力。“通過必要的語法學習,使學習者易于表達、便于閱讀、善于交際”。(李曉琪2004)當然,學生的語言學習存在這兩種不同方式,而這兩種學習方式各有特點,在語言學習中的作用不可互相替代,但語言能力、語言交際能力的形成卻是這兩種學習方式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漢語的認知表征差異
從語音系統上看,漢語與西方語言差異很大,在西方語言里,普遍存在著音義對應規則,其中“形”一直與“音”對應,與“義”沒有直接關系,而漢語卻大相徑庭,在大多數情況下,字形與字義存在著對應關系,所以在通達意義上,西方語言只有語音通達這一個路徑,而漢語卻有字形和語音兩條通達的路徑。②從意義的通達上,也可以看出漢語具有的類型特征。從認知語言學上看,不同的語言是否有不同的加工表征?這是一個大問題。對此的回答不外乎兩個:一是通用語言系統理論,即單加工理論模型,無論使用哪種語言,都要運用普遍一致的認知機制和同樣的認知表征結構,二是多用語言系統理論,即多加工理論模型,認為使用不同語言的人運用不同的語言加工系統和認知表征結構,不同語言在正字法、語音、形態、句法上的差異可能會導致不同的認知方式,因此會存在著不同的認知結構表征,近來許多實驗實證研究較多地支持多用語言系統理論,即語言不同,認知和表征都有差異。③
漢語是音節語言,而印歐語多是音素語言,目前的研究表明,加工漢語時激活的很多認知活動區域在加工西方語言時很少被發現。我們知道,左額中皮層主要用來調節空間和語詞的工作記憶,同時還負責工作記憶的中央執行系統協調認知資源分配,由于漢語有不同于印歐語的字形結構,在完成語義加工任務時,需要在視覺空間分析和語義分析間進行認知資源分配,因此,加工漢語時左額中回的強激活與漢字的空間立體特征密切相關,有研究已經證明了這點。④同時,研究還表明漢語加工中激活的另一個特別的認知區域在右半球,在語義判斷和同音字判斷任務中也被激活,拼音文字加工時這些區域并未被激活,這恐怕也與加工漢字需要大量的視覺-空間分析有關,可見,右額葉和右頂葉皮層主要負責對漢字的空間結構進行加工。另外,甚至右側枕葉皮層都參與視覺符號的空間再認活動,這些結論表明,漢語的加工有特殊的認知表征。
因為功能和形態可塑性是認知加工區域的固有特性,認知加工區域的形態特征未必與不同語言有關,作為孤立語的漢語加工與作為屈折語的其他語言加工能夠導致皮層的形態差異嗎?對此,Kochunov,P.等(2003)研究認為,操漢語者與操英語者的認知加工區域差異有四處,分別是左額中回、左顳中回前部、左頂葉和右頂葉上部,在這一區域操漢語的人明顯大于操英語的人。當然,并非所有的功能差異都一定會有形態差異與之對應,但每一形態差異都對漢語加工有特定意義。在加工漢語時,左額中回負責視覺-空間分析,是激活最強的區域。⑤左顳中回前部在語義判斷和同音判斷中有較強激活,左顳中回在加工復雜的空間或聲音特性時起作用,與英語相比,漢字在空間結構和語音方面都比英語復雜。
上面講的是不同的人與不同的語言,那么對二語習得或者外語學習而言,不同的語言是否會與母語有不同的認知活動區域?對此,一種觀點認為,加工兩種語言有相同的皮層表征;另一種觀點認為,加工兩種語言有不同的皮層表征。
對母語是漢語的雙語者,有研究支持兩種語言有相同的皮層表征。Pu,Y.等(2001)使用中文和英語的動詞產生任務比較了母語為中文的人加工漢語和英語的皮層差異,結果是加工中文和英文有相似的認知功能區域激活,左半球的激活區顯著大于右半球的相應區域,激活最顯著的區域處于額中回下部。⑥Tan等人(2003)則比較了母語為漢語的漢英雙語者在押韻判斷和字形相似判斷任務中的表現,結果發現,對英文詞和漢字加工的腦區顯著相似,最大激活都出現在左額中回。中國人的左額中回對加工漢字和英文都有重要作用,加工漢字和英文并未引起不同的腦區激活,左顳中回和左額下回是加工英語音素的腦區,中國人在加工英語時卻沒有明顯激活。⑦這至少也可以說明,中國人將加工漢語的認知機制遷移到英語加工過程中,用加工中文的認知策略對英文進行加工。
不同的語言既影響了人類的認知加工方式,也影響了認知策略與過程,不同語言有不同的詞匯形式和語法結構,這會導致語言使用者在加工語言時使用不同的加工策略。如英語強調拼寫-聲音轉換規則會使人更重視詞的拼寫形式和音素結構,詞的曲折變化更易使被試形成關注詞尾的策略,而漢語中詞的方塊結構和單音節特性會使人更多地以整體方式儲存詞的字形和語音,在進行語義加工時更多地關注詞的義符,在進行語音加工時更多地關注聲旁。可見,語言影響認知過程,講不同語言的人在進行某些認知過程時會有區別,語言中的范疇和原型會影響人對事物的加工、編碼和儲存,會使講不同語言的人或雙語者使用不同語言時得到不同的認知結果。
三 教材編寫的認知策略
教材作為教學結構中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教師組織教學活動的主要依據,也是學生學習的重要來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時教材也是語言教學理念、教學水平以及相關的基礎研究、理論研究的集中體現。⑧教學程序、教學環節的設計和開展,師生的所有互動和交流,都緊緊圍繞著教材的內容展開。
教材是為學生服務的,必須要滿足學生學習的認知加工需要,但實際上教材是按照語言知識的邏輯體系編寫的,是以線性安排展開的封閉系統,語言習得獲取的是隱性知識,而語言知識學習所掌握的是顯性的、有意識的知識,比較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學習過程而得出語言學習快速性的結論并不能令人信服。影響語言習得的關鍵因素是學習動機,而不是年齡因素,語言習得是一個即時的過程,語言使用者是理想的語言使用者,他們生活在同質的語言環境中。這一預設不太符合語言實際,與語言學習經驗也不太相符。所以,研究者都試圖描述學習者的處理語言輸入時的心理過程和在語言輸出時表現的知識系統。由此可見,二語習得中認知理論主要目標是解釋語言學習過程,而認知語言學是從認知角度解釋語言現象本身。
教材是構建認知結構的手段和工具,是實現教學目標的客觀條件。教育心理學認為,動機和興趣對學習效果起著重要作用,教材在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上的作用不可忽視。因此,教材必須符合學習者的認知過程,體現學習者的心理規律。對外漢語教材的編寫應該自覺吸收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認知心理學、語言理論研究等的成果,在語言輸入的規范、學習動機的激發、語言信息加工過程的關注等方面體現出不同的編寫思路。
(一)語義優先的認知原則
自然語言的認知語義網絡是沒有邊界的立體網絡,似乎我們一生中都在持續地編織這張漫無邊際的語義網。⑨由此可見,在基本語言能力或日常語言能力的上層還存在一個可以不斷建構的語言知識系統。盡管不同個體所掌握的專業知識不盡相同,由此形成個體語義網絡的差異性,但是這些不同的專業知識可以通過專家們的合作梳理,使之成為百科知識體系。將日常語言知識和百科語言知識匯總,則可以進一步建構龐大的語言知識庫,日常語義網絡是基礎語言能力,而專業語言知識是基礎語言能力的進一步延伸和發展。
人類個體一生的主要精力也就是在不斷掌握或建構語義網絡,語義網絡建構的過程,也就是認知能力不斷發展和認知范圍不斷擴展的過程。一方面,語言能力的提高伴隨著認知能力的發展,另一方面,認知能力的發展反射為語言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見,在語言能力的底層,存在著不斷發展的認知能力。人類擁有基于認知能力的語義網絡自建構能力,也就意味著人類具有一個以語義網絡為表現方式的認知網絡,由此決定了認知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互轉化,一直持續互動的歷程。
對學習漢語的外國人而言,學習漢語語法知識的目的是要指導自己的語言實踐,是要學好漢語,掌握實際的漢語綜合運用能力,學習的結果會直接影響他們能否正確地使用漢語。“一個詞語,一個格式,怎么用是合乎漢語的語法,怎么用是不合漢語的語法,要教給學生的不正是這個嗎?”(呂叔湘1979:6)這就決定了“教外國學生重點不應該是理論體系和概念術語,而應該是用法”(胡明揚2002)。傳授語言知識的目的是指導實踐,規范學生的言語行為,這也是對外漢語教學和對“內”漢語教學的一個重要區別,語法教材急需在漢語書面語的語言運用上下功夫,從語言運用的角度來降低語法學習的難度,語法教學的目的恰恰是要走出語法。
語言是人類認知、思維和交際的音義符號工具。以往的許多語言理論研究,過度強化了句法的作用,使得語言習得完全與母語習得的實際背道而馳,而忽略了人類語言交際最為根本的語義性,而建立在人類獨有的認知能力之上的人類語言習得能力,也就是具備語義網絡的自組織或自建構能力。個人獲得語言能力的過程,就是個體語義系統的建構過程。當出生時,他已置身于一個世代傳承的語言氛圍中,他的任務就是通過能動性模仿不斷激活遺傳性認知機制,構建一個為自己所掌握、為社群所認同的語義世界。人類自然語言,作為認知成果的是“語言系統”,作為使用工具的是“語言能力”,作為使用過程的就是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言語行為”。作為工具使用的語言能力,是在作為認知成果的語言系統的建構過程中一步步實現的。語言能力側重于運用的言語機制(言語生成和言語理解)、會話機制(會話策略和語境模型)及語言知識。
(二)語言認知的刺激驅動
語言的認知,包括刺激驅動(包括聽覺、視覺等)和概念驅動。在語言學習的初始階段或是年齡較小者更多是經由前者來學習,因為概念的形成是內部語言發展的結果。
據信息加工理論,語言習得應當按照語言輸入-集中加工-語言輸出的流程來進行,在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中,聽和讀是向學習者輸入信息;說和寫是學習者輸出語言信息。⑩語言信息的有效刺激加工模式體現在“聽說合一、讀寫合一”的教材編寫過程中。
以往基于紙本介質的限制,教材的多通道刺激的選擇是難以達到的,而在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持下,計算機在信息呈現形式和內容上較一般的文本方式有很大的進步,它可以把文本、圖形、視頻圖像、動畫和聲音等信息結合在一起,給學習者提供了多感覺通道、多表征形式的語言刺激。學生除了接受來自視覺通道的信息外,還可以同時感受大量由聽覺通道呈現的語音信息以及大量的非語言信息,如圖畫、實物、音樂、動作、姿勢、面部表情等。當這些以多感覺通道呈現的刺激同時激活左右大腦的不同區域時,可直接讓大腦接受大量形式不同的信息,使得整個學習活動在更廣的層面上發生。因此,教材編寫應該采用大量的有效的多通道刺激輸入材料,可以有效刺激視覺、觸覺和聽覺,例如非文字材料,包括圖片、聲音等,這些非文字材料不是傳統教材中起裝飾作用的插圖,而是教材的有機組成部分,并以其直觀的形象和色彩,發揮了文字所不易或不能具備的調動學生感知和想象的作用,有助于學習者理解、儲存和記憶。
聲音、圖象、文字等多種刺激并重,聞其聲、觀其形、臨其境,再現了生活實際,表達了大量信息,拓寬教材的表現形式,加大了課堂容量,促使教學效果達到優化,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和運用漢語交際的能力,這也應該成為未來漢語教材編寫的一個趨勢。
四 結語
語言認知反映的是人們對整個語言體系的基本看法,語言能力的提高過程,也是不斷掌握程序性知識和學習陳述性知識的過程,隨著語言知識的增長,個體語言能力不斷提高,語義網絡不斷擴展。
漢語因受到對本體語言認知相對滯后的影響,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體系,漢語認知理論的形成尚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論證和探討。漢語是一種自成體系的語言,其語言認知必須遵循漢語語言自身的規律,而針對教材編寫所做出的策略定位,應盡量避免各種干擾本體語言認知的因素。
注
①吳 剛,《生成語法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3-8頁。
②有證據說明,由于長期使用漢字,人們對漢字的義符更為敏感,在提取漢語詞的語義時,很多都采取“由形到義”的路徑。
③張積家,劉麗虹,譚力海.語言關聯性假設的研究進展,《語言科學》.2005年第3期。
④Tan,L.H.,&Spinks,J.A.,&Gao,J.H.,&Liu,A.,&Perfetti,C.A.,&Xiong,J.,&Pu,Y.,&Liu,Y.,&Stofer,K.A.,&Fox,P.T.Brain activation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A functional MRI study.Human Brain Mapping,2000,10:27-39.
⑤Kochunov,P.,&Fox,P.,&Lancaster,J.,&Tan,L.H.,&Amunt s,K.,&Zilles,K.,&Mazziotta,J.,&Gao,J.H.Localized morphological brain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speaking Caucasians and Chinese–speaking Asians.Neuro Report,2003,14(8):1-4.
⑥Pu,Y.,&Liu H.L.,&Spinks,J.A.,&Mahankali,S.,&Xiong,J.H.,&Feng,C.M.,&Tan,L.H,&Fox,P.T.,&Gao,J.H.Cerebral hemodynamic response in Chinese(first)and English (second)language processing revealed by event-related functional 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2001,19:643-647.
⑦Tan,L.H.,&Spinks,J.A.,&Feng,C-M.,&Siok,W.T.,&Perfetti,C.A.,&Xiong,J.H.,&Fox,P.T.,&Gao,J.H.Neural systems of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are shaped by native language.Human Brain Mapping,2003,18:158-166.
⑧在討論教材的編寫原則時,以往一些學者通過研究,提出了許多原則,例如科學性、針對性、實用性、趣味性、生動性、標準性、漸進性、重復性、數量性、人文性、創新性、優化性、實踐性等等,事實上,這些原則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歸納出來的,并沒有運用同一標準,這樣的原則歸納一旦標準不一,得出的原則就太多,勢必難以窮盡,所以歸納出來的原則從學術上看并無太大意義。
⑨以G.Lakoff,R.Langacker等為首的語言學家們以語義為研究中心,運用經驗主義語言觀,對范疇化( categorization)和原型理論(prototype)、隱喻(metaphor)、意象圖式(imageschema)等基本認知概念及其與語言的關系進行了新的闡發。
⑩輸入假說是美國應用語言學家克拉申提出的。他認為,語言交際要獲得成功,輸入至少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第一,輸入應該是學習者可理解的;第二,輸入量必須充足;第三,語言輸入要稍高于學習者的語言能力。
胡明揚.漢語語法教程序[J].載孫德金.漢語語法教程[M].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2.
李 泉.論對外漢語教材的趣味性[J].載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第七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李 泉.論對外漢語教材的針對性[J].世界漢語教學.2004,(2).
李魯平.漢語語言認知的嬗變[J].齊魯學刊.2008,(3).
李曉琪.關于建立詞匯—語法教學模式的思考[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4,(1).
劉頌浩.關于對外漢語教材趣味性的幾點認識[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5,(5).
陸儉明.關于開展對外漢語教學基礎研究之管見[J].第六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馬箭飛.漢語教學的模式化研究初論[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4,(1).
齊 沛.對外漢語教材再評述[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3,(1).
王初明.應用心理語言學[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許 琳.漢語國際推廣的形勢和任務[J].世界漢語教學.2007,(2).
趙金銘.漢語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
朱志平,江麗莉,馬思宇.1998-2008十年對外漢語教材述評[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5).
Boroditsky,L.Does language shape thought?Mandarin and English speakers'conceptions of time[J].Cognitive Psychology,2001,43(1),1-22.
Dabrowska,E.&E.Lieven.Towards a lexically specific grammar of children question constructions[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5,16:437-474.
Feldman,J&S.Narayanan.Embodied meaning in a 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J].Brain and Language,2004,(89).
Geoffrey Sampson.The“Language Instinct”debate(revised edition)[M].New York:Continuum,2005.
Lieven,E.&M.Tomasello.2008.Children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a usage-based perspective[J].In P.Robinson&N.Ellis(eds.).2008.168-198.
MacWhinney,B.A multiple process solution to the logical problem of language acquisition[J].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2004,31:883-914.
Pinker,S.語言本能——探索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The language instinct)[M].洪蘭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5.
Robinson,P.&N.Ellis(eds.).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New-York/London:Routledge,2008.
Taylor,J.Cognitive gramma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Tomasello,M.Constructing a language: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Zwaan R A.The immersed experiencer:toward an embodied theory of language comprehension[J].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