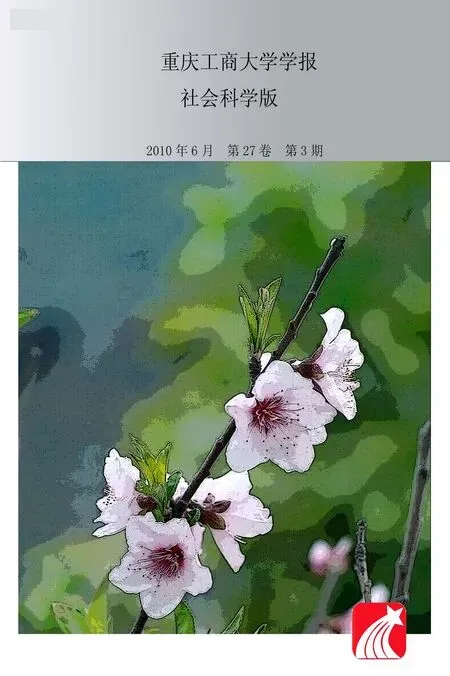論世情小說名著《金瓶梅》對《水滸傳》敘事體例的生命承傳
張鵬飛
(亳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安徽 蒙城 233500)
一、《金瓶梅》對《水滸傳》敘事范式的文化承繼
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文化思想始終崇奉著“男尊女卑”的道德理念,女性只是作為男性的附屬物存在而絲毫不享有人生的自由權利且在婚姻問題上主要是承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凄慘命運。正如馬克思所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期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1]譬如說,《水滸傳》作為一部收集前人資料整理演義而成的小說名著卻深受儒家文化“三綱五常”道德規范的影響而深深地打上了傳統女子婚嫁觀的審美烙印。比如段三娘曾與王慶交手又主動托媒求親。但《水滸傳》作為忠實維護傳統婦女婚嫁觀的文學典籍卻這樣評價不守“閨訓”段三娘:“從小不循閨訓,自家擇配,做下彌天大罪,如今身首異處,又連累了若干眷屬”。[2]強調女子自家擇婿的正當舉動是不可饒恕的罪孽。
恩格斯指出:“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了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同時論述:“為了保證妻子的貞操,從而保證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親,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絕對權力之下了;即使是打死她,那也不過是行使了他的權力罷了”。[3]由此,封建貞節觀其實是男權意識對女性的一種行為規范以及身心自由上的道德限制。可見,古代社會要求女性貞節可以說是個頗具世界性的普適問題,但在封建宗法制森嚴的中國,也許更為突出,并成為維系整個社會的基本紐帶之一。[4]然則《金瓶梅》人物刻畫中業已了無傳統文化思想規范的約束功效,而是體認著蕓蕓眾生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封建禮制及程朱理學的嘲弄、褻瀆與叛逆以及傳統價值觀念在市井平民社會階層中的貶值乏味和對人生在世的享樂生活的孜孜不倦地渴望吟誦。即社會轉型期帶給世人的唯有道德的迷失、行為的失控、野性的張揚、神圣的蕩滌,倫綱的不復、佛道的疑惑和信仰的動搖。自此,中國文學演繹開始拓進到禮教人倫的封建禁區并突顯著小說藝術苑囿的新境界。
《金瓶梅》雖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演繹的長篇小說名著,但其敘事體例卻多半是依托于《水滸傳》而加以演化生成。比如說,《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陳經濟被陷嚴州府,吳月娘大鬧授官廳”的回首詩“暑往寒來春復秋”源自于《水滸傳》第三回“史大郎夜走華陰縣,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嘆曰“事遇機關須進步,人逢得意早回頭”。感喟時光短暫且富貴在命不由人的勸誡意圖。《金瓶梅》第九十七回“經濟守御府用事,薛嫂賣花說姻親”的回首詩出自《水滸傳》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豹子頭誤入白虎堂”。宣講著貧富由命、窮通在天的宿命論。《金瓶梅》第九十九回“劉二醉罵王六兒,張勝忿殺陳經濟”的“一切諸煩惱”發自于《水滸傳》第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鬧飛云浦”之回首詩等。[5]皆表征著作者創作思想義理與立身處世思辨的心有靈犀的契合融匯。故而張竹坡品評:“《金瓶》內之西門,不是《水滸》之西門。且將半日敘金蓮之筆,武大、武二之筆。皆放入客位內,依舊現出西門慶是正經香火,不是《水滸》中為武松寫出金蓮。為金蓮寫出西門。卻明明是為西門方寫金蓮。為金蓮方寫武松”。[6]即言蘭陵笑笑生演藝故事雖有模仿之處但卻是順著西門慶一支線索自然而然、有條不紊、栩栩如生地加以鋪陳敘述。
《金瓶梅》雖說是一部“從藝人集體創作向完全獨立的文人創作發展的過渡型作品”或是“我國第一部文人創作的擬話本長篇小說”。[7]然則黃霖曾在《<忠義水游傳>與<金瓶梅詞話>》一文中統計了《金瓶梅》中蓋有27個人物與《水滸傳》源出同名。又將《金瓶梅詞話》和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加以對勘就找出兩書相同或相似的描述12處,《金瓶梅》模仿《水滸傳》的韻文54處,認為《金瓶梅》承續的是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而劉世德先生通過對《金瓶梅》與《水滸傳》比勘則認為:“《金瓶梅》作者襲用《水滸傳》文字時。既參考了天本(天都外臣序本)又參考了容本(容與堂本)”。[8]像欣賞者在文本對讀中皆可發現《水滸傳》與《金瓶梅》有相當程度的融通之嫌。譬如,《金瓶梅》第二十回“盂玉樓義勸吳月娘,西門慶大鬧麗春院”的回首詩“在世為人保七旬”所表達的即是聽天由命、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就源自于《水滸傳》第七回“鄆哥幫捉罵王婆,淫婦藥鴆武大郎”的回首詩“參透風流二字禪”的莫計得失、安貧守拙的生命理念。
《水滸傳》故事的成書可謂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歷程。它產生于北宋且醞釀、豐富、流傳于宋、金、元并一直延續到明初的多事之秋。加之施耐庵《水滸傳》的敘寫始終認為漢家一統的難以為繼切實表征著忠義不在朝廷。故而另辟蹊徑地借助民間廣為流傳的宋江故事來振呼忠義報國。李卓吾則主張:“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那些“有忠有義”的“大力大賢”之人不愿“束手就縛而不辭”就聚集水滸之地。“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9]然則《金瓶梅》小說故事的產生卻有著迥異的歷史文化淵源。蘭陵笑笑生所面臨的是一種近乎粉飾太平表象下的盛世繁華。再者,程朱理學扼殺人性的本質越來越受到有識之士及日益壯大的市民社會的質疑和顛覆。故此“物極必反”的事物運動規律又導致了明代中葉以后人欲的泛濫與肆虐的矯枉過正的現實生存窘境。
二、《金瓶梅》對《水滸傳》敘事樣式的藝術嬗變
《水滸傳》小說敘事中包括西門慶與潘金蓮等主要人物在內的諸多形象或姓名卻承續在《金瓶梅》敘述中反復出現。然其故事顯然經過了程度不等的改寫編撰。諸如《金瓶梅》關乎世俗人情的敘事是注重以小說得名的“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為主要女性形象加以描摹。雖說人物出身、性格和遭遇皆有差別,但在她們的內心深處卻有著一種共同的超乎尋常的對于情欲、物欲和肉欲的渴求或是對赤裸裸的人性的自然欲望的求索。而潘金蓮可謂是淫蕩、狠毒、欲望的鬼魅化身。即所謂“宜乎金蓮之惡冠于眾人”。[10]但毋庸諱言,《金瓶梅》中的確尚有一些地方過多沿襲著《水滸傳》中的大片整段的文字敘寫和詩詞韻文。張竹坡評介:“《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數,為之尋端競委,大半皆屬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書。如西門慶、潘金蓮、王婆、武大、武二,《水滸傳》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無論”。[11]可以說,《水滸傳》與《金瓶梅》是明代兩部承續關聯契合的小說典籍。袁中道指出:“模寫兒女情態具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12]從小說發展的角度觀之,自《水滸傳》到《金瓶梅》可謂是體認著小說敘事范式由歷史傳奇向世俗人情敘事轉化的演進軌跡。因此,沈德符評曰:“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13]
馬克思指出:“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衡量”。[14]可以說,《金瓶梅》著力展現了晚明時期平民百姓所信奉的離神、解咒、祛魅的現實境遇,世人不再以傳統的宗教倫理思辨來束縛性靈,也不愿將人生幸福寄托于來世托生而去忍受現世的諸種苦難磨礪卻尊崇當下肉體的快樂歡娛以及奉行著“快活了一日是一日”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陽溝溝里就是棺材”的人生哲學。因此,中國傳統佛教文化中的“因果報應”觀念作為一種信仰雖說可給民眾提供一種敬畏崇奉和形而上的生命關懷,然則吳月娘就始終認為潘金蓮“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如同馬爾庫塞所指出:人可以根據充分發展的知識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重新提出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的問題。[15]即寓意著潘金蓮對佛教的來世愉悅的說教不感興趣而常常毀僧謗佛且變得無所畏懼的去追求當下的生命體驗并干盡了毒殺武大、害死官哥,陷害來旺、逼絕惠蓮等彰顯著道德虛無主義生存理念的惡劣行徑。
晚明時期中國社會所充滿的動蕩和變革的轉型體征就突出地的表現在由經濟轉型而引發的一系列的文化變遷。概因明中葉以來的城市全面繁榮、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層壯大、政治斗爭尖銳、王朝更替頻繁的諸多社會大動亂,導致了理學信仰的危機和異端思想的抬頭,加之雅俗文化的日益對流與中西學術的初次碰撞以及處此復雜多變環境里的士人騷客心態的無助、狂放、抑郁、渺茫的矛盾匯集情愫。凡此種種,社會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諸多心理因素的整合貫通致使晚明社會日趨推崇個性宣泄的文藝思潮的誕生。正如溝口雄三評介:晚明思想界的變化是經濟與社會深刻巨變的伴生物;這其中,對“欲”的肯定和對“私”的主張,是儒學思想史上一個根本的變化。[16]可以說,《金瓶梅》小說敘事中兩性關系的露骨化描寫孕涵著對封建等級秩序的公然蔑視和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叫囂宣戰,它突顯了世人的獨立意識的覺醒和個性本體的張揚以及滲透著人的本能解放與社會創造及經濟發展的內在關聯。譬如說,西門慶針對吳月娘要其“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干幾樁兒,卻不攢下些陰功”的善意規勸卻在《金瓶梅》第五十七回公開宣稱:“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是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富貴!”[17]李卓吾評曰:“成佛證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雖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18]體認著“三教合一”下的晚明社會境況和泰州學派的陽明心學觀照下的審美取向并預示著傳統倫理道德之下的世人心靈的躁動和對人性肆意發泄的希冀。
從接受美學觀之,《水滸傳》敘事中潘金蓮是個“淫婦”欲女而西門慶是富而好淫。然涉及《金瓶梅》的相關情節的兩個人物的基本風貌仍然未有迥異質變。即言蘭陵笑笑生所接受的不僅是潘金蓮、西門慶的名字而主要的卻是接受了人物形象的生命體征。換句話說,西門慶和潘金蓮惟有在《水滸傳》現有“基本形象”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發展和演繹,否則將背離讀者欣賞的期待視野。即《金瓶梅》的敘事情結不能完全擺脫《水滸傳》的“陰影”或偶爾必須牽涉關情到《水滸傳》,可以戲說是“《金瓶梅》中的水滸”。同樣,人類喜歡獵艷趨奇又是其天性本真使然,而重視故事情節的生動、有趣、誘人則是古今中外小說家從事創作時所偏愛的審美效應。像《金瓶梅》在被翻譯到西方出版發行時就在書名問題上煞費苦心而絞盡腦汁地突出其故事性、媚俗性、趣味性和煽情性。諸如1853年法國巴黎出版的巴贊所譯的《武松與潘金蓮的故事》、1927年紐約出版的《金瓶梅:西門慶的故事》、1930年出版弗朗茨·庫恩翻譯的《金瓶梅:西門慶與他的六妻妾之艷史》、巴黎出版公司1949年出版的讓·皮埃爾·波雷編譯的《金瓶梅:西門慶與其妻妾奇情史》等就是頗含意味的典型范例。[19]可以說,《金瓶梅》借用一部小說去接受另一部小說的特殊接受方式又與小說敘事范式中的續書演繹有所差異,但《金瓶梅》中諸多人物顯然被作者加以“改造”深化。像武松在《金瓶梅》中就完全變異,“這位景陽岡上的打虎英雄,一落到人間就成了蕓蕓眾生。西門慶才是‘虎’,是‘英雄好漢’,是強者;在西門慶面前,武松變成了‘羊’,是凡夫俗子,是弱者。《水滸》中殺嫂祭兄、仗義自首的慷慨悲歌的場面不見了,光明磊落、義薄云天的英雄,變了卑微瑣小、凡夫俗子”。[20]即小說敘事模式可謂是由作者的自由思維所建構。《金瓶梅》誕生之前的長篇小說在敘事模式上承受史傳文學思維的百般觀照而大多展現神秘虛幻的非現實生存空間且構成了敘事情節的離奇怪誕、跌宕起伏和生動傳神。然則《金瓶梅》故事情節的敘述空間卻洗滌了神仙佛教所賦予世人的神秘觀感且聚焦于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的幻化夢境。
《金瓶梅》小說敘事中卻張揚著作者的人性關懷和哲學幽思并試圖尋覓到生命的信仰而重建世人的精神家園。它強調著塵世萬物的幻化、痛苦和空虛,意在喚醒讀者對生命本身的反省抗爭。恰如作者在卷首詞所吟:“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旨在喚醒讀者對生命本體的自覺感悟并以此奠定全書的審美基調。正如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所言:“我從超越的存在中能了解到的是,我們所尋求的行為是一個純粹的虛構”。[21]坦言人生的歡樂、痛苦、欲望皆為生命幻影,所謂彈指間去來今,顯示著無法救贖欲望而慰藉眾生的悲涼、憐憫和哀嘆。故而清代張潮在《幽夢影》評說:“《金瓶梅》是一部哀書”。張坡竹亦主張《金瓶梅》是一部“炎涼書”。[22]比如說,《金瓶梅》小說演義中的潘金蓮就是一個對傳統婚嫁觀最具挑戰性的世俗女子形象。她雖遭際命運的不幸坎坷但卻對人生表現著強烈的憤懣抗爭。當張大戶將之許配給“身不滿尺的丁樹”般的武大郎時就突顯其面對強迫的不合理的“婚姻”的強烈哀怨。蓋因武大郎“生的身不滿三尺,為人儒弱,又頭腦濁蠢可笑”。清河縣人見其“模樣猥衰”。起了他個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23]故而嘆息身世:“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個貨?每日牽著不走,打著倒退的,只是一味嘛酒。著緊處,卻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里晦氣,卻嫁了他!是好苦也!”[24]于是乎整日“打扮油樣,沾風惹草”而變得更加輕浮、招搖和淫蕩,看似“春心”騷動的青年女子的正常心理追求即是對男性壓抑的某種報復以及對封建禮教與倫理道德的一種控訴且富含追求自由幸福、性靈張揚和個性解放的生命情韻。它體現出作者對遭受傳統婚姻制度戕害毀滅的婦女的深切同情以及對造成女性身心痛苦的婚姻制度的強烈不滿,也是《金瓶梅》在婦女自由婚姻理念上對《水滸傳》傳統婚姻觀的超越升華。
綜上所述,《金瓶梅》可謂是一部出現于明代萬歷年間的摹寫市情世相的寫實主義經典小說,它是對當時的現實社會、人生百態、世俗民事的真實、生動、自然的高度貼近化的敘述描寫。然則《金瓶梅》敘事情結可謂徹底滌除了中國傳統章回小說《水滸傳》等由市井彈詞到文人寫定的近乎道德評判的文化心態,而是以冷靜、客觀、寬容的敘事摹寫對諸多人物形象的行為舉止加以真實的披露刻畫且認同著某種菩薩般的慈悲心腸并傳達出哲人思辨的悲哀憐憫,從而彰顯著意味雋永的生命情韻。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C]//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
[2] 施耐庵.水滸傳[M].濟南:齊魯書社,1991:169.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C]//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2.
[4] 李新燦.女性主義觀照下的他者世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75.
[5] 周鈞韜.《金瓶梅》素材來源[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87.
[6]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M].濟南:齊魯書社,1987:62.
[7] 周鈞韜.《金瓶梅》:我國第一部擬話本長篇小說[J].社會科學輯刊,1991(6):26.
[8] 劉世德.《金瓶梅》與《水滸傳》:文字的比勘[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1(5):22.
[9] 李贄.焚書續[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9.
[10] 侯忠義.張竹坡評點第一奇書金瓶梅[M].濟南:齊魯書社,1988:66.
[11] 張竹坡.金瓶梅寓意說[C]//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589.
[12] 袁中道.游居柿錄[C]//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229.
[13]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C]//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230.
[14]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C]//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71.
[15] 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學探討[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56.
[16]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M].北京:中華書局,1997:27.
[17]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776.
[18] 李卓吾.焚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5:101.
[19] 胡文彬.金瓶梅書錄[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9.
[20] 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28.
[21] 耿春紅.庸眾的沉淪和哲人的悲哀[J].明清小說研究,2005(3):75.
[22] 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444.
[23]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一回)[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8.
[24]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M].香港:明亮書局,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