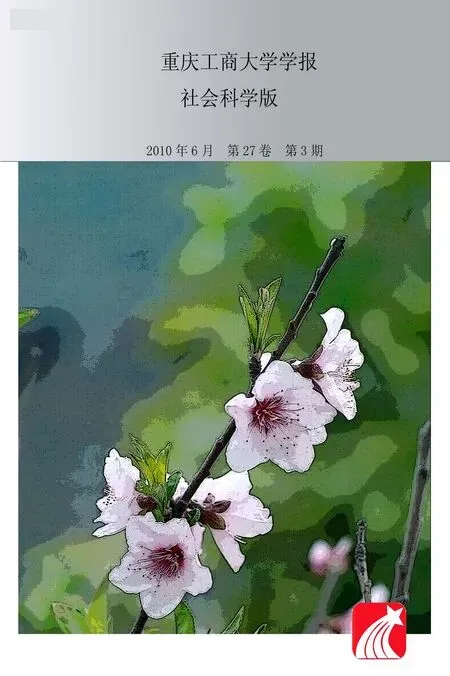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的特征及其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孫立春
(杭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一、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的五個階段及兩個高潮
日本近現代小說指的是從明治維新到現在的小說,而開啟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的正是梁啟超1898年翻譯的《佳人奇遇》,可見這段翻譯史主要集中于20世紀。因此筆者將以20世紀為中心來研究這段翻譯史,21世紀最初7年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也略有涉及。關于20世紀中國的日本文學翻譯史的分期,王向遠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中分為五個階段,即清末民初(1898—1919),二三十年代(1920—1936),戰爭時期(1937—1949),建國頭三十年(1949—1978),改革開放以后(1979—2000)。另外,譚汝謙在《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把300年的中日翻譯史分為五個時期,即萌芽期(1660—1895),第一過渡期(1896—1911),發展前期(1912—1937),第二過渡期(1938—1945),發展后期(1946—1978)。相比之下,王向遠的分期更符合20世紀日本文學翻譯史的實際。因此,筆者參照王向遠的分期,并結合譚汝謙歸納的各階段譯書分類明細表,簡單地回顧了20世紀中國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
通過梳理這100多年中國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其中有兩個高潮:一個是第二階段,即五四運動至抗戰爆發;另一個是第五階段,即改革開放以后的二十余年。這兩個高潮期的共同點是譯者人數多,譯作數量大,影響面廣。不同點在于前者偏重于引進日本的近代小說,以對抗中國的舊文學,促使中國文學發生質的變化;而后者重在全方位地介紹日本小說,以填充“文革”后的文學空白期,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體現出中國文學已經成熟,譯介過來的日本近現代小說不再是文學革命的武器,而是中國文學的有效補充。也就是說,譯介過來的日本近現代小說在這兩個高潮中的作用不同,而且譯介的范圍也不一樣。從這100多年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中,我們可以發現小說是近現代中日文學交流的主要載體,翻譯是近現代中日文學交流的主要媒介,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進行深入研究,以找出這繁榮現象下的深層次規律。
二、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的總體特征
近現代的中日文學交流是一千多年的中日文學交流史中最輝煌的一章,而日本近現代小說的翻譯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梳理豐富多彩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我們發現這段翻譯史有四個鮮明特征。筆者試述如下:
第一,隨中日關系而變化。近現代的中日關系史是錯綜復雜而變化多端的,既有和平友好的時期,也有戰爭動蕩的年代。甲午中日戰爭以后,中日關系走上了不正常的軌道。后來日本在中國又制造了二十一條要求事件、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等,第一、第二階段的中日關系日趨緊張,但由于中國非常需要日本政治變革和文學變革的經驗,以及魯迅等大批留日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所以第一、第二階段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并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并逐步走向第一個高潮。“七七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戰爭阻礙了正常的文學交流,也使日本文學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中日關系急劇惡化,原來譯介日本近現代小說的知識分子只能放下譯筆,投身到救亡圖存的抗戰中去,因此日本近現代小說的翻譯驟然減少,所譯介的少數小說也是為了配合抗戰。日本投降以后,中國又陷入內戰,譯者們也無心譯介日本近現代小說。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歷史原因,所以這一時期譯介的日本近現代小說也不多,而且局限于左翼文學和反戰文學,忽視了戰后日本文壇的發展。1972年兩國恢復外交關系,中日關系也開始邁向正常化的軌道。改革開放以后,中日兩國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這種良好的中日關系也帶動了中日文學交流和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的繁榮,并形成了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上的第二個高潮。
第二,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大。意識形態決定著譯者個人和譯入語社會的思想觀念,進而影響譯者的選題和翻譯策略。第三、第四階段尤其體現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在第三階段,國共兩黨都堅持抗戰,打敗日本侵略者、確保中華民族的獨立是愛國知識分子的共識,所以他們為了配合抗戰,譯介了一些揭露日本侵略者兇殘本質的侵華文學和在華流亡日本人的反戰文學。而在偽滿洲國和汪偽政權控制的淪陷區,當權者為了鞏固日本的殖民統治,宣揚日本文化的優越性和侵華的合理性,譯介了一些純文學和侵華文學作品。第四階段,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偏左的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作品的思想內容是選題的首要依據,藝術價值是第二位的標準,所以只有符合這種意識形態的日本左翼文學和反戰文學才得到我國譯者的重視,其他小說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排斥或輕視。而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宣傳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左翼小說自然不會受到青睞。除了社會整體的意識形態,也存在有一定獨立性的個人意識形態。某些內化在譯者腦海中的思想意識也會在無意中影響譯者的選題。例如在第一階段時,清王朝日益衰落,梁啟超等維新派對這種落后的意識形態不滿,所以為了開啟民智、實現變法維新,他們譯介了日本的一些政治小說和科學小說。
第三,純文學與通俗文學并重。在第一階段時,譯者的文學本位意識薄弱,他們譯介的目的在于輸入文明和借鑒日本近現代小說的思想意義,而不是看重其文學價值,所以他們譯介的大多是二三流的通俗作品,而不是文學名著。例如他們幾乎沒有翻譯二葉亭四迷、幸田露伴、樋口一葉、森鷗外、夏目漱石等名家的小說,尾崎紅葉的小說雖然翻譯了兩種(吳梼所譯的《俠黑奴》和《寒牡丹》),但不是尾崎紅葉的代表作。而他們對二三流作家如押川春浪、菊池幽芳、櫻井顏一郎、黑巖淚香等人的作品卻翻譯了很多,同時大量翻譯的政治小說藝術價值也不高。第二階段,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開啟了研究日本文學的風氣,所以這一時期的譯者在選題時少了隨意性和盲目性,開始把小說的藝術價值作為選題標準,譯介了大量優秀作品。第五階段,翻譯家已經成熟,他們認識到了日本近現代小說的價值,因而全面翻譯了屬于純文學的小說,而且有的小說有多種譯本。同時為了滿足普通讀者的娛樂需要和獵奇心理,他們也翻譯了大量可讀性強的社會小說、家庭小說以及趣味性強的推理小說。王向遠經過統計和比較,指出這一時期推理小說的譯本約有270種左右(含復譯本),占100年來日本文學譯本總量的七八分之一,約占這一時期日本文學譯本總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森村誠一是20世紀中譯本最多的日本小說家。[1]純文學譯介與通俗文學譯介的共同繁榮是這一時期日本近現代小說譯介的最顯著特點。
第四,譯者個人因素突出。相對于意識形態和贊助人而言,譯者選擇譯本的自由是有限的,但這并不等于譯者始終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譯者雖然受意識形態等因素制約,但他們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翻譯主體,可以在可供選擇的材料中,選擇契合自己價值觀、興趣愛好、翻譯目的的作品,對于其他作品可以視而不見,同時在翻譯過程中決定譯本的具體形式。除了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第三、第四階段,其余階段都明顯體現出譯者的主體性和個人風格。在這些階段中,譯者可以選擇某一流派、題材類型的小說,也可以拒絕某一流派、題材類型的小說;可以用這種語言風格去表達原作,也可以用那種語言風格去表達原作;可以用直譯的翻譯策略,也可以用意譯的翻譯策略。正因為譯者在對原作的選擇、理解、表達中發揮了不同的主體性,所以不同流派、類型的小說在20世紀的中國才有了或被重視或被忽視的不同境遇,而且有的小說也有了不同風格的譯本。譯者的個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譯本世界的面貌。
三、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中國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大大開拓了中國人民的視野,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王向遠所說:“一百年來,我國共翻譯出版日本文學譯本兩千多種。日本翻譯文學對我國的近代文學、五四新文學、三十年代文學以及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文學,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2]中國讀者從這些數量龐大、類型各異的日本近現代小說譯本中,不僅了解到日本的風土人情和日本人的內心世界,在思想上受到了啟示,而且也從這些譯本中學到了一些藝術技巧,從而為中國小說的近代化轉變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概而言之,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詞匯上。實藤惠秀曾經考察過中國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兩種辭典(《新名詞辭典》和《新知識詞典》,各收新名詞6000多條),發現其中的日語詞匯和與日語詞匯結合的詞匯占了大半。[3]高名凱、劉正淡合著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和王立達的《現代漢語中從日本借來的詞匯》也陳述了這一事實。例如高名凱和劉正淡指出:“日語詞匯對現代漢語詞匯的影響很大,是現代漢語詞匯中的外來詞的主要來源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大的來源;許多歐美語言的詞都是通過日語轉移入現代漢語詞匯里的。”[4]日語詞匯進入現代漢語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留日學生的廣泛應用,二是翻譯的日本書籍的流行,可見日本近現代小說的翻譯對輸入日語詞匯也是有功的。融入現代漢語的這些日語詞匯不僅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詞匯量,帶來了許多新觀念、新思想,而且促進了現代漢語的復音化和現代化,使現代漢語表達更加精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的豐富也必然會帶來文學表現方式的多樣化,所以隨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而來的日語詞匯,首先在語言層面上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
第二,觀念上。小說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一直處于末流,為中國傳統文人所輕視。梁啟超通過提倡翻譯日本等國的政治小說,改變了這種傳統的文學觀,提高了小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五四運動”以后,周氏兄弟對白樺派小說的譯介,使中國作家發現了白樺派主張的個性解放、人道主義、理想主義,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這些思想的合理內核。20世紀20年代末,后期創造社對日本左翼文學的譯介,促使中國左翼作家在“階級意識”上覺醒,并使他們把這種意識體現在自己的創作中。由此可見,日本近現代小說的譯介不僅對扭轉中國文人輕視小說的觀念產生了積極作用,而且也在文學思想上給中國近現代文學以新的啟迪,同時也使中國知識分子改變了輕視日本文學的觀念,從而能在平等的條件下開展中日文學交流。
第三,形式上。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曾經借用了日本政治小說《雪中梅》的倒敘手法。除了倒敘,梁啟超的“新文體”也來自于政治小說的翻譯實踐。在《佳人奇遇》中,他把原文的漢文調文體直譯為中文,結果形成了一種半文半白的翻譯文體,并受到學者文人的歡迎。日本近現代小說譯介對中國小說形式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第一人稱敘事、景物描寫和心理描寫等方面。中國古典小說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敘事,在翻譯過來的日本等外國小說的影響下,中國小說家也開始用第一人稱敘事,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性。例如,從赤裸裸地告白“我”的性欲的《沉淪》中,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第一人稱敘事的魅力,也能看出郁達夫對日本私小說敘事模式的借鑒。另外,中國古典小說不太注重心理描寫和景物描寫,很少用大段文字刻畫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描繪自然景物,而且在早期的外國小說翻譯中,這些文字也經常被整段刪去。隨著日本等外國小說譯介的增多,中國小說家開始適應這些描寫技巧,并逐步加以模仿,所以中國的近現代小說才逐漸有了細膩的心理描寫和豐富的景物描寫,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
第四,題材上。郭延禮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中指出,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教育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未涉及的題材類型,這4種題材都是從外國小說借鑒來的。[5]其實,這4種題材中,最早的政治小說和教育小說都譯自日本,它們分別是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和山上上泉的《苦學生》,而偵探小說和科學小說中也有不少是直接譯自日本或從日文轉譯的。例如直接譯自日本的偵探小說有黑巖淚香的《離魂病》和江見水蔭的《女海賊》《地中秘》等,從日文轉譯的偵探小說有加博里奧的《奪嫡奇冤》(轉譯自黑巖淚香的日譯本)等。科學小說中的相當一部分也是來自日本,影響最大的科學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的大部分中譯本都是從日譯本轉譯的。例如梁啟超譯的《十五小豪杰》,依據的是森田思軒的譯本。魯迅譯的《月界旅行》,依據的是井上勤的譯本,而且魯迅在這個譯本的《辨言》中寫道:“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于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故茍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6]由此可見,魯迅當時的小說觀也受到梁啟超功利主義小說觀的影響。除此之外,押川春浪創作的五六部科學小說也被翻譯過來,如包天笑譯的《千年后之世界》,徐念慈譯的《新舞臺》等。不僅如此,“20世紀初中國‘新小說’的主要的小說題材分類概念,幾乎全都沿用了日本文壇在翻譯西洋有關小說題材類型時所創制的漢字概念”,而且“對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這三種題材的優先提倡,同時也受到了日本文壇的啟發。”[7]由此,我們可以了解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對引進新的題材類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通過對中國的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史的整理,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其中的四個鮮明特征,了解到日本近現代小說翻譯對中國文學的深刻影響[8],從而為我們從文化角度研究日本近現代小說在中國的翻譯情況,提供了宏觀背景和選題依據。因此,我們應該重視并深化日本現代小說翻譯研究。
[參考文獻]
[1] [2] 王向遠.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382-383.
[3]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M].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310-311.
[4] 高名凱,劉正淡.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158.
[5] 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97-501.
[6]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52.
[7] 王向遠.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225-226.
[8] 范榮.林杼小說翻譯策略的讀者視野關照[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