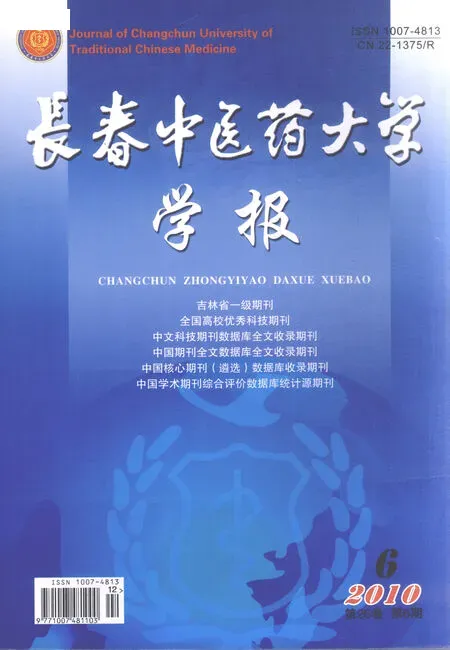中醫教學再思考
薛益明(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香港)
中醫教學再思考
薛益明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香港)
中醫學不僅是實踐性、經驗性、靈活性極強的醫學專業知識;更具有豐富的思想和獨特的研究方法,學習、領悟與掌握了這些特有的思維方法,才算是真正學會了教授中醫、學習中醫。
中醫學;中醫教學;教學研究
中國內地的高等中醫本科教育是從1956年開始的,雖然經歷過幾次課程調整與教學改革,但總體上講,中醫教學科目、課程結構與教學模式等沒有根本變化,一直沿襲至今,逐步形成了相對穩定而成熟的中醫本科教育體系。香港的高等中醫教育是從1998年開始的,在引用內地高等中醫教育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香港醫療體制與生源特點而有所側重,歷經十余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與可喜的成就。筆者在一線從事中醫教學工作近30年,從未間斷,先前在南京中醫藥大學任教,2006年來到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任教。系統講授《中醫各家學說》《中國醫學史》《中藥學》《方劑學》《內經》《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學》等。可教學時間越長,教學科目越多,困惑也就越多,常常獨自思考,中醫到底怎么教。
1 關于教學語言
語言是一種藝術,它是教學過程中最直接、最重要、最常用,然而又最難用好的一種工具,一般要求具有趣味性、啟發性、通俗性、節奏性和激勵性等,而我以為在中醫教學中,通俗性顯得格外重要。
中醫學的語言文字本來就深奧專業,很難與非中醫人士交流與溝通,即使中文、古文好的人也未必明白。因此,教學語言通俗與否,對于中文基礎一般的同學、低年級同學,尤其重要。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力求把深奧的術語通俗化,把理論概念實際化,把抽象知識形象化,圍繞教學內容,用簡明的、生活化的、形象生動的語言,寓理于事,深入淺出,將復雜的、抽象的問題講得清楚明白,通俗易懂。
中醫理論體系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一種以古代哲學思想為基礎,以臟象學說為核心,以辨證施治為診療特點的一門學科。其思維方法樸素而獨特,理論抽象,要使從中學剛進大學的學生產生學習興趣與動力,《中醫基礎理論》的教學要特別注意。第一,不要引經據典去解釋適應證,特別是引用《內經》。古代中醫教學本無《中基》這門課,是為適應現代高等中醫教育的需要,將以《內經》為主要內容的中醫基礎知識白話成如今的《中醫基礎理論》,是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學舉措。如果反復引證、講解《內經》《難經》等,實際是往回走了,也因此而增加了學生的學習難度,勢必會影響學生學習中醫的興趣與動力。第二,不要過多擴展古代哲學內容。盡管中醫學與古代哲學有交叉與重疊,但畢竟是兩個不同學科,哲學的辨證思維、認識論、方法論等對其它學科都有指導意義,但不能代替。醫學是自然學科、應用學科,如果在一年級講太多、太深的哲學內容,會有失偏頗。
2 關于教學標準
中醫教學內容與教學效果,究竟以什么標準來評價?從中醫學科特性而言,筆者以為應該是臨床。中醫是以經驗為主導,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即使是中醫基礎類學科,對臨床也是絕對依賴,不結合臨床是講不清說不明的。既然臨床療效是中醫的生命線,那么中醫教學的目的、意義、評價標準就應該以這條線為基準。
搞學問的專家,為了研究的目的,經常把看似簡單的問題,進行復雜化處理;而教師為了教學的目的,又不得不把那些復雜的問題,用言簡意賅的語言進行簡單化闡述。這就是研究與教學的區別。中醫應該算是“復雜”的學問,因為它用哲學文化、模擬歸納、抽象推理等解釋自然生命科學,即“無形”對“有形”。這就產生了中醫理論概念內涵的不確定性,外延的無限性。如何解析與拆分這一復雜問題,根本一點就是以中醫的核心理論與臨床療效為中心;如何界定教學內容的價值,關鍵一點還看對臨床是否有指導意義,這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與評價標準。不要在概念、文字上糾纏爭拗;也不要在課堂上化大量的時間去解釋對臨床沒有指導意義的問題;更不要把理論擴大化、玄奧化,人為地把中醫推向神秘與復雜化。如《內經·舉痛論》的講解;《中國醫學史》醫家年齡的考證;《中醫各家學說》中的李東垣論“陰火”、朱丹溪論“陽有余陰不足”等,這些內容如何教學,如何取舍詳略,就看對臨床的指導意義在哪里,對學生臨床辨證是否有幫助。
中醫理論的核心內容其實是通俗、簡單、樸素的,非常直觀與明確,經過幾千年的不斷注解與演繹,使中醫的概念越來越復雜,教材越編越厚,分科越來越細,不可否認中醫在概念、文字上的復雜化有人為因素。惟有用“臨床”這把標桿,直入中醫理論的核心與本質,才能使中醫教學與人才培養更加高效與實用。
3 關于教學思維
古老而傳統的中醫學,是以哲學為基礎,臨床為核心,思維方法獨特的自然學科。有人總結中醫具體的思維方法有整體思維、辨證思維、意象思維、變易思維、中和思維、直覺思維、虛靜思維、順勢思維及功用思維等等。其實,以臨床為出發點、為基準,核心一點就是臨證思維。也可以說,中醫學是屬于思辨性思維,在中醫的教與學中要用“圓形”思維(哲學思維),不要用“線形”思維。
如在《中醫基礎理論》教學中,學習五行學說時應強調其體現了中醫的意象思維;學習治則時應強調其體現了中醫的中和思維;學習五臟與形、竅、志、液、時的關系時應強調其體現了中醫的整體思維;學習氣的運動時應強調其體現了動態平衡思維等等。這樣既加深了中醫理論的理解,又培養了中醫的臨床思維。中醫臨床思維是整個中醫思維體系的核心部分,是多種思維方法的總和,主要體現為整體觀、動態平衡觀及辨證論治觀。
作為教學主體,教師首先要求自身有堅定的中醫信念、扎實的中醫理論及臨床功底。因為,思維的培養如同習慣的培養,是個極其漫長的過程,需要教師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引導并不斷重復,使之于潛移默化中成為學生的思維定式。作為教學模式,案例式教學是被普遍認同的,醫案是中醫臨床的實錄,能最直接地反映醫生的臨床思維,接近于直觀場景,克服了從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理論課堂教學方式的弊端,能充分吸引學生注意力,調動學習積極性,適合中醫教學的任何課程。
G642.1
A
1007-4813(2010)06-0982-02
2010-07-23)
薛益明,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醫經典課與中醫基礎類課程的教學以及中醫文獻與中醫教育研究;內科疑難病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