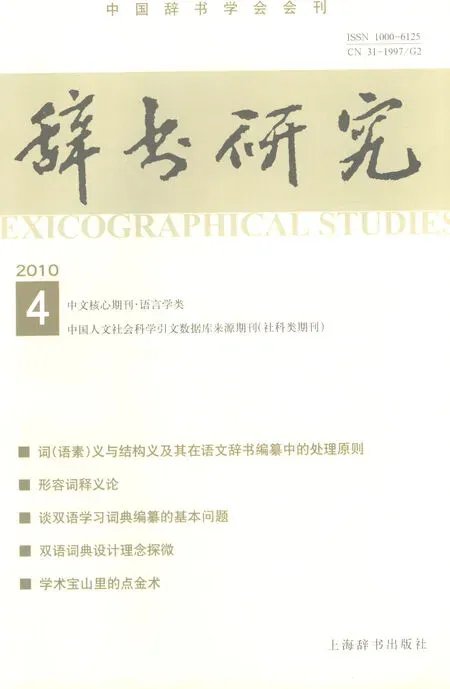跨文化視角下的法律術語解析
馬 莉
(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上海 200042)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心和視角都發生了轉移,在素有語言關懷傳統的翻譯和雙語詞典編纂理論領域則表現為“文化熱”的興起。法律文化是使用法律語言作為表達方式的群體所特有的現象。正如不同的文化群體對不同事物有不同反應,即文化焦點不一樣。法律文化的焦點就集中體現在大量的法律術語上。本文根據現有常用詞典及法規譯文中對部分法律術語的解釋,探討在法律文化語境下對法律術語的理解,以及在翻譯中如何兼顧文本語言轉換和文化轉換。
法律語言這一術語源于西方,在英語中它原指表述法律科學之概念以及用于訴訟和訴訟法律事物時所選用的語種或選用某一語種的部分用語,后來亦指某些特定法律意義的詞語,即法律術語,并且擴展到語言的其他層面。法律術語作為一種語言功能變體,是法律文化的產物和載體。用文化語言學的眼光來看,法律術語與法律文化關系密切,現擬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考察國內目前常用詞典對法律術語不同文化內涵的解析。
1.體現法律概念的特定性
在法律術語的英譯過程中,譯者有時會望文生義,用一個在形式上較為相像或相似的英語法律專業術語來翻譯母語中的法律術語,但是這樣往往導致譯文的意思大有出入。英語中有兩個表示侵害他人名譽權的詞:libel和 slander。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libel指的是以文字或其他書面形式對人進行誹謗,而slander則指以口頭形式誹謗他人。國內如《新英漢詞典》《英華大詞典》《遠東英漢詞典》《英漢法律詞典》等都注意到了這兩個詞的差異,但將這兩個詞都譯為“誹謗罪”。在英美法等國,libel和slander是一個侵權法上的概念,而不是刑法上的概念。對于侵害他人名譽權,受害人可以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我國沒有專門的侵權法,侵權行為根據其嚴重程度分別由民法和刑法來調整,因此我國有所謂的“誹謗罪”。而查英美國家的刑法著作和法典都找不到libel和slander的有關內容,但在侵權法中卻能找到。這兩個詞在英美國家實際上表達的都是侵權法上的概念,而不是刑法上的概念,因此,將 libel和 slander分別譯為“書面誹謗”和“口頭誹謗”較“誹謗罪”的譯法要更為適宜。
再如“物證”一詞,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和法規譯審和外事司聯合編寫、1998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法規漢英對照詞語手冊》將其翻譯成“material evidence”。這種譯法貌似正確,但實際上意思相距甚遠。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第七版對“material evidence”的解釋,該詞實際上是指“evidence having somelog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consequential facts or the issues” ,意 為“與案件的事實或結果存在邏輯關系的證據”,它既可能是言辭證據也可能是實物證據。在這里,“material”并非什么“物質”。那么這個“material”在法律文字中的實質含義又是什么呢?據陳忠誠的考證[1],香港洪士豪《英漢法律辭典新編》中,material evidence解釋為“實質性證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漢國際經濟法律詞匯》中,解釋為“實質上的證據,主要證據”。綜上所引,“物證”在英語中另有專門的法律術語與之對應,如“ physical evidence” 、“ real evidence” 、“demonstrative evidence” 或“objective evidence”等。
我國法律專業術語英譯方面存在的另一問題是譯者有時將漢語文本中的同一法律概念用多個不同的英語法律術語來表述。每個專業術語基本上對應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例如漢語法律專業術語“原告”在英語中就只能夠譯為plaintiff,而不能譯為其他。但是“原告”一詞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漢英詞典》編寫組編的《漢英詞典》(修訂版縮印本)[2]中卻有“plaintiff”和“prosecutor”兩個譯名。此一解釋值得推敲。因為“prosecutor”代表的是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是行使國家的公訴權來指控犯罪,更多是用于刑事訴訟意義上的,因此,“prosecutor”譯為中文時,應是“公訴人”,而不應是“原告”。
語體的嚴肅性和語義的特定性是法律術語的重要特征。嚴肅的語體要用嚴謹精密的專門法律術語去體現。因此,在法律專業術語的解釋中不能夠想當然地望文生義。
2.體現法系的差異
法系是根據若干國家和地區基于歷史傳統原因在法律實踐和法律意識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而進行的法律的一種分類,它是具有共性或共同傳統的法律的總稱。當代西方社會存在著兩大法系,即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兩大法系在法律制度上存在很大差異,如英美法系有專門的侵權法,而大陸法系則沒有,大陸法系有公法和私法之分,英美法系則沒有。例如:英國財產法律制度中有 tenancy in common和joint tenancy兩詞,《英漢法律詞典》[3]將其分別譯為“共有租賃”和“共同租借權”。如若不了解其在英國法律中的含義,不知道英國法律的財產制度和其獨特的信托制度,就難以對其進行準確的翻譯。根據英國信托法中的有關定義,兩者區別在于tenancy in common是指“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可加確定的份額,共有人死亡,其份額可轉至健康人手中”,“joint tenancy”是指“合有財產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一合有人死亡時,其權利轉移給生存的合有人而不是繼承人,直至該權利為最后生存者所有為止”。因此,前者可譯作“共有”,后者可譯作“合有”。
不同的法系中,相同的語言符號可能會表示不同的概念。如一般詞典都將jail和 prison這兩個詞譯成“監獄、牢獄”,不加區分。但在美國司法背景下,jail不同于 prison。prison是由聯邦或州政府設立的關押已判決重罪犯的改造場所,相當于我國的“監獄”,而 jail是用于短期關押由聯邦或州立司法機關起訴的等待審理的被告或被判處短期有期徒刑的輕罪犯的地方設施,相當于我國的“看守所”,因此,在解釋時應注意區分,以準確表達詞義。
3.體現不同文化語境
法律制度的共性與語言的普遍性為法律語篇的可譯性奠定了理論基礎,而各種語言的特殊性及本土性又為法律詞匯翻譯提出了新的課題,因此探索法律術語文化語境及其具體的處理方法對體現法律文本特殊的社會功能和實用價值至關重要。
就英漢對應詞語而言,一種文化寓意在一種語言中存在,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可能幾乎完全沒有。這種情況在英漢法律翻譯中經常出現。如英語bar和與其對應的漢語“柵欄”。在英、美等國家,由于 bar被用作在法庭內分隔不同的訴訟人員,由此逐漸具有了諸如“法庭”、“被告席”、“審判臺”、“律師”、“律師界”、“律師職業”、“司法界”等法律國俗語義 。同時還在此語義上派生出諸如 debar、disbar和 disbarment等新的法律術語。此外,由bar組成的許多術語或習慣用法也與以上的文化寓意密切相關,如 bar examination(律師資格考試)、bar association(律師協會)等等。相比之下,漢語中的“柵欄”或“欄桿”則無任何此種法律文化寓意。
4.體現時際特征
法律莊嚴神圣,不可朝令夕改,因此法律及其語言載體的發展較為緩慢。但是即便如此,隨著時代的變遷,總會有一些新的詞匯涌現到法律語言中,并漸漸地演化為專門的法律術語。比如羅馬法系中的“legal person”最初被譯成“法人”,它的意義對當時尚未建立法人制度的中國來說就是一個創造。雖然現在一些新版詞典經過修訂已經收錄了相當一批法律新詞,但這些被收錄的法律詞匯僅僅是近年來出現的法律專門術語中的一小部分。有些法律詞匯諸如“第三者”、“探視權”、“離婚損害賠償”等,雖然早已出現在眾多法律法規和法律文件之中,但由于“時差”的原因,卻尚未被收錄在詞典中。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英語的時際特征。當這些新詞沒有被收錄于我國的法律詞典中,而且也不見諸國外的法律詞典和法規中,而產生這些制度的法律文化背景又不能在外國的法制歷史上加以考察的時候,就對我們的翻譯提出了挑戰。
根據Sarcevic的觀點,法律翻譯與一般翻譯有著本質區別,它是“法律機制中的交際行為”,是“法律轉換和語際轉換的雙重操作”,[4]法律術語的解析無疑也處于法律和翻譯的雙重框架之內,它不但要遵循普通翻譯理論,還要受制于法律概念、價值觀、分類規則、歷史淵源、方法論和社會經濟等原則。從文化視角對法律術語詮釋旨在搭建一種法律間溝通和相互理解的橋梁,為促進不同法律文化的理解、交流和合作作出貢獻。
附 注
[1]陳忠誠.法苑譯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256.
[2]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漢英詞典》編寫組.漢英詞典.修訂版縮印本.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7:1546.
[3]英漢法律詞典編寫組.英漢法律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143.
[4]Sarcevic S.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T 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