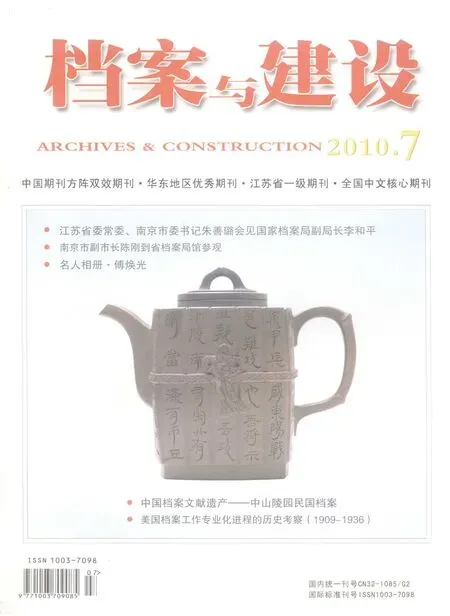江蘇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與研究的若干問題*
□孟國祥
近代以來,江蘇經(jīng)濟發(fā)達,人文薈萃,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江蘇在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發(fā)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誠如周恩來所言,誰掌握了滬寧杭地區(qū),誰就掌握了大半個中國。1937—1945年期間,日軍肆意燒殺淫掠、轟炸破壞,在淪陷區(qū)實行殖民統(tǒng)治,給江蘇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和建設(shè)事業(yè)造成巨大的損害,江蘇成為日禍的重災(zāi)區(qū)之一。詳實的抗戰(zhàn)損失統(tǒng)計應(yīng)當載入史冊,警示國人。戰(zhàn)后,國民政府曾開展抗戰(zhàn)損失的調(diào)查,然而由于戰(zhàn)時江蘇大部淪陷,戰(zhàn)后國共政治軍事對峙,因此缺乏完備的統(tǒng)計。1990年以來,學者不斷吁請開展抗戰(zhàn)損失研究。2006年,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牽頭,各省市開展了關(guān)于抗戰(zhàn)損失的調(diào)研。筆者研究發(fā)現(xiàn),要科學地進行江蘇抗戰(zhàn)損失研究,需要了解江蘇抗戰(zhàn)時期的歷史、政權(quán)與轄區(qū)的變革,以及損失計算的方法及可信度。為此,本文擬就江蘇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研要注意的諸問題,略以考證和辨析,以期為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與研究提供借鑒。
江蘇抗戰(zhàn)損失統(tǒng)計的地域問題
上海原是江蘇的一部分,民國以來成為直轄市。抗戰(zhàn)爆發(fā)前,江蘇有60縣,南京是中國首都,鎮(zhèn)江為江蘇省會。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中國行政區(qū)劃的變動,江蘇的轄區(qū)也有了變化。1958年,原屬于江蘇的10縣(上海縣、川沙縣、南匯縣、寶山縣、金山縣、青浦縣、奉賢縣、松江縣、嘉定縣、崇明縣)被劃歸上海市,蕭縣、碭山縣劃入安徽。劃入上海10縣之名稱又不斷變化,如上海縣后成為上海的閔行區(qū)。行政區(qū)劃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當今抗日戰(zhàn)爭史與戰(zhàn)爭損失的調(diào)查與研究。上海的學者張銓等所著《日軍在上海的罪行與統(tǒng)治》,將寶山縣、嘉定縣、上海縣、松江縣納入上海研究的視野,而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主編的《侵華日軍在江蘇的暴行》,也記述了日軍在寶山、嘉定、南匯、松江所犯的暴行。1938年偽江蘇省政府所作的《江蘇各縣災(zāi)況調(diào)查統(tǒng)計圖》,以及戰(zhàn)后江蘇省政府開展的損失調(diào)查統(tǒng)計,均將上海10縣納入江蘇統(tǒng)計范圍。為尊重歷史,有關(guān)江蘇抗戰(zhàn)與損失的研究,應(yīng)按1937—1945年江蘇所轄地域為研究對象。如按現(xiàn)在轄區(qū)研究,必須予以說明。
再如,由于南京當時是中國的首都,南京巨大的生命財產(chǎn)損失是否納入江蘇的統(tǒng)計,當時江蘇省政府在南京清涼山開辦的省立國學圖書館的損失是納入江蘇還是納入南京的損失統(tǒng)計,都需要界定與說明。
江蘇抗戰(zhàn)損失的歷次調(diào)查
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不久,江蘇的部分工廠、學校內(nèi)遷。上海淪陷后,隨著政府西撤與中國軍隊的退卻,江蘇迅速淪陷,當時無暇顧及損失統(tǒng)計。江蘇大部淪陷后,一些賑災(zāi)組織為了繼續(xù)救災(zāi)事宜,對部分縣市開展調(diào)查。1938年3月—6月,由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轉(zhuǎn)化而成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The Na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Committee)為做好賑濟的發(fā)放,委托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史邁士(Smythe)主持調(diào)查南京附近的災(zāi)情。南京市區(qū)的家庭調(diào)查以每50家調(diào)查一家,共計調(diào)查949家;鄉(xiāng)村調(diào)查及于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5縣,調(diào)查沿主要路線每3村調(diào)查1村,每10家調(diào)查1家,共計調(diào)查905家。調(diào)查結(jié)果編成報告《南京地區(qū)的戰(zhàn)爭損害》(War Damage in NakingArea),也稱《南京戰(zhàn)禍寫真》。南京市區(qū)每戶平均損失1261.77元,江寧、溧水、六合、江浦、句容等縣農(nóng)戶平均損失318.91元。在調(diào)查涉及的100天里,上述5縣農(nóng)村死亡人數(shù)為3.1萬人,每7戶中就有一人被殺害。江浦縣被害人數(shù)比例最高,占總?cè)丝诘?.5%。到1938年3月底,農(nóng)村被抓人口仍有13.3萬人未能歸家。①上述統(tǒng)計不全,也失之過小,但畢竟為江蘇損失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樣本。
透過戰(zhàn)時敵偽的檔案,也能了解江蘇損失的部分情況。如淪陷初期各市縣偽政府及衛(wèi)生局關(guān)于掩埋尸體的報告,以及大量因家人被屠殺或房屋被毀而衣食無著的貧民要求救濟的呈文。
為恢復社會穩(wěn)定以利殖民統(tǒng)治,偽江蘇省政府曾對部分縣進行災(zāi)況調(diào)查。1938年12月,由偽江蘇省政府第二科編制的《江蘇各縣災(zāi)況調(diào)查統(tǒng)計圖》顯示,蘇南常熟等15縣加之蘇中南通縣、如皋縣,難民達3921355人,死亡76941人;句容等16縣財產(chǎn)損失73090萬元;丹陽等13縣被毀房屋257588間;金壇等10縣被毀農(nóng)具182781件;青浦等12縣損失耕牛34590頭;青浦等9縣農(nóng)作物損失71043擔。統(tǒng)計與實際相距甚遠,如南通縣死亡人數(shù)僅列9人,如皋縣財產(chǎn)損失48元,被毀房屋江寧1620間、吳縣77間、句容15990間。而同年國際救濟委員會調(diào)查則為,江寧平均每戶完全毀壞1.90間,計毀房屋155000間;句容被毀31300間。②雖然偽政權(quán)的統(tǒng)計偏小,從中也可見江蘇損失之一斑。
為了清算日本侵華罪行,以待戰(zhàn)后向日本索賠,并“將此空前慘痛之事跡,翔實記載,昭告后世”,1938年11月在重慶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黃炎培等人提議從速設(shè)立抗戰(zhàn)公私損失調(diào)查委員會,“調(diào)查前方、后方、直接間接公私損失,填具表式,報告政府”。1939年7月,行政院制頒《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辦法》及《查報須知》,通令中央各機關(guān)及各省市縣政府分別調(diào)查具報,并指定國民政府主計處審核匯編所有材料。為便于統(tǒng)計分析,主計處按期編制《抗戰(zhàn)時期各種損失調(diào)研材料》以供參考。
江蘇戰(zhàn)時大部淪陷,對損失的調(diào)查與了解自然十分有限,收集淪陷區(qū)經(jīng)濟情報便成為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的重要部分。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最先倡導并一度派員駐淪陷區(qū)城市上海等地搜集資料,編有《淪陷區(qū)經(jīng)濟概覽》。中央調(diào)查統(tǒng)計局特種經(jīng)濟調(diào)查處也按期編印《敵偽經(jīng)濟匯報》。因淪陷區(qū)材料難以搜集,因此收集的資料大部為報刊所載有關(guān)經(jīng)濟文章、報道的摘要。如現(xiàn)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于1939年7月20日編制的《抗戰(zhàn)時期各種損失調(diào)研材料》(第2期),就是關(guān)于江蘇松江、上海、蘇州、無錫、常州、鎮(zhèn)江、南京等市工廠企業(yè)損失的報刊文章剪貼。③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委員會成立后,加強了淪陷區(qū)經(jīng)濟情報的搜集工作,指派委員分任各淪陷區(qū)損失與敵人破壞、盜取行為的調(diào)查估計,委托淪陷區(qū)特務(wù)機關(guān)與游擊部隊查報。如戰(zhàn)時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所作的《1940—1943年南京市敵偽教育工作調(diào)查報告》,就是由中統(tǒng)特務(wù)機關(guān)派人在南京暗中調(diào)查而成。由于戰(zhàn)時江蘇大部為敵偽控制,蘇北部分地區(qū)一度為省府主席韓德勤勢力影響所及,蘇中及蘇北大部為中共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因此戰(zhàn)時江蘇無法進行系統(tǒng)的調(diào)查。
抗戰(zhàn)勝利后,為向日本索賠提供損失數(shù)據(jù),國民政府著令迅速開展損失調(diào)查。戰(zhàn)后江蘇國共分治,軍事對峙,不久又成為全面內(nèi)戰(zhàn)的起點,因此難以像其他省區(qū)那樣求得較完備的損失統(tǒng)計。省府欲將調(diào)查施及全省,而蘇北蘇中大部為中共蘇皖邊區(qū)政府轄區(qū)。蘇皖邊區(qū)政府于1945年11月成立,轄江蘇32縣、安徽18縣、河南3縣。1945年12月,蘇皖邊區(qū)政府又將53舊縣調(diào)整為72個縣,分屬8個行政區(qū)。其時,蘇皖邊區(qū)政府也開展了部分損失調(diào)查,損失以實物數(shù)量統(tǒng)計,而沒有折合成貨幣單位。1946年2月,統(tǒng)計損失共為:被殺害人口239387人,殘廢54147人,被抓壯丁133500人,急需救濟4384615人;損失房屋2966368間、糧食62079284擔、衣被40879162件;損失牛馬363923頭、豬羊2656563頭、農(nóng)具1108867件、棉花1291500擔。④蘇皖邊區(qū)政府的調(diào)查,主要是了解災(zāi)情以爭取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援助,特別強調(diào)“人民對于救濟總署之要求”,對金融、工業(yè)、教育、文化損失缺少詳實統(tǒng)計。加之縣政區(qū)變化較大,而其中南通、崇明等縣又納入省府統(tǒng)計范圍,因此蘇皖邊區(qū)的損失調(diào)查只能作為現(xiàn)在研究的參考。事實上,從日本投降至1946年6月全面內(nèi)戰(zhàn)爆發(fā),蘇皖邊區(qū)一直處于國民黨軍隊進逼的最前線,鞏固解放區(qū)、為生存而戰(zhàn)處于壓倒一切的地位,無暇進行大規(guī)模、長時間、深入而細致的損失調(diào)查,這就為現(xiàn)在抗戰(zhàn)損失研究帶來了困難。
損失統(tǒng)計的缺漏問題
抗戰(zhàn)勝利后,為向日本索賠,需提出各項戰(zhàn)爭損失的數(shù)字及有關(guān)資料。1945年10月12日,行政院將資料整理編制成《財產(chǎn)損失報告表》和《人口傷亡報告表》上報。由于是戰(zhàn)時統(tǒng)計資料的匯編,缺漏甚多,淪陷區(qū)損失偏于估計且大部未列入。“淪陷地區(qū)如江蘇、河北等省在三十三年(即1944年)以前之人口傷亡,多數(shù)未據(jù)查報”,《人口傷亡報告表》中江蘇人口傷亡僅290人。于是國民政府決定在全國范圍內(nèi)全面調(diào)查。1945年11月22日,行政院頒令《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實施要點》,明確劃分中央各部會及地方的職責、調(diào)查事項,并限3個月內(nèi)辦理完畢。各省成立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委員會,統(tǒng)一印刷表格章則23種,組織調(diào)查專員分赴實地追查。資料整理后再按類別上報。如教育事業(yè)損失,至1946年6月,戰(zhàn)后教育部對各地不斷上報損失材料進行了五次匯編。第五次匯編統(tǒng)計,戰(zhàn)時全國教育事業(yè)總損失為國幣4748871585686元,以1945年8月中央銀行外匯牌價國幣2,070元折合1美元計,為美金2374435793元。其中江蘇中小學教育損失計國幣502847514110元。上述統(tǒng)計不包括東北、港臺地區(qū)和中共解放區(qū)的損失。⑤至于人口傷亡統(tǒng)計,由于統(tǒng)計復雜,頗費時日。為備遠東委員會討論日本賠償參考,國民政府曾組織專家對平民傷亡數(shù)予以估算,共計傷亡約8609852人,其中江蘇傷亡594545人(死亡370977人,重傷67551人,輕傷156006人);南京市傷亡205784人(死亡155338人)。⑥該估算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如經(jīng)調(diào)查與法庭判定,在南京大屠殺慘案中遇難的同胞就達30萬之多。
由于戰(zhàn)后特定的政治格局與調(diào)查時間的限制,有關(guān)江蘇抗戰(zhàn)損失統(tǒng)計也只能作為研究的參考。
《江蘇省公私文物損失數(shù)量及估價目錄》所列書籍損失僅為:公61851冊另2部、私70419冊另139種1部。⑦筆者研究發(fā)現(xiàn),該統(tǒng)計缺漏甚多,就圖書損失而言,鎮(zhèn)江圖書館損失圖書6萬冊、蘇州圖書館損失圖書12798冊,均未列入。縣立圖書館損失也僅統(tǒng)計常熟、昆山和無錫縣3縣圖書館的損失。至于學校圖書損失,僅登記私立松江松筠女子職業(yè)學校損失8000冊、昆山石浦鎮(zhèn)中心國民學校損失1部。
究其原因,其一,申報時間過于緊迫。全國公私文物損失登記自1945年10月26日起,要求于1945年12月底截止。雖有延緩,實際上1946年2月教育部便匯總各地材料制表擬報遠東國際委員會。江蘇大部為新收復區(qū),內(nèi)遷的部分學校及圖書1945年底未能回遷原地,1946年3月鎮(zhèn)江圖書館館舍還作為日本士兵的羈押地,損失調(diào)查自然無從談起。從江蘇省檔案館檔案可見,江蘇省縣級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表填報一般在1946年2月以后,文物損失統(tǒng)計自然不全。南京市的損失調(diào)查一再延期至1947年8月,可在此前的1947年5月20日,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在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期間就對外公布了中國抗戰(zhàn)損失的各項統(tǒng)計。此后,內(nèi)戰(zhàn)蔓延與時局急劇動蕩,國民政府再也沒有進行損失調(diào)查與統(tǒng)計。可見,中國抗戰(zhàn)損失(包括江蘇)有估算的成分。其二,蘇中、蘇北為國共軍事嚴重對峙地區(qū),難以求得完備周詳?shù)慕y(tǒng)計,而部分縣根本沒有統(tǒng)計。如1946年3月,淮安縣、漣水縣、阜寧縣等縣報告,因?qū)僦泄舱碱I(lǐng)區(qū),“抗戰(zhàn)損失,無法填報。”其三,江蘇與南京是重災(zāi)區(qū),日軍侵占期間,制造血腥屠殺,很多居民被殺光乃至絕戶,大量建筑被焚毀,許多損失無從知曉;因交通工具奇缺,至1946年初,遠走他鄉(xiāng)的民眾很多未能返回故里,加之難民居無定所,要按時申報損失,實屬困難;文物損失調(diào)查手續(xù)過于繁瑣,在申報時不僅要填報受損文物的名稱,尚須提供文物照片、圖樣或票據(jù),損失的時間、地點,更要填報文物遭損失時施暴者即日偽機關(guān)或部隊名稱、日偽負責人姓名以及文物目前下落等,并附有當?shù)赜嘘P(guān)部門的證明。日軍入室搶劫,絕不可能開具收條,居民躲避尚恐不及,豈能強求日軍報告其部隊名稱和長官姓名,因而“公私收藏家對文物損失之申報均不踴躍”。由上可見,江蘇抗戰(zhàn)損失研究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wù)。
注釋:
①路易斯.S.C.史密斯:《南京戰(zhàn)禍寫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9頁。
②《抗戰(zhàn)時期各種損失調(diào)研材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761-227。
③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主編:《侵華日軍在江蘇的暴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388頁。
④《蘇皖邊區(qū)人民抗戰(zhàn)八年中所受災(zāi)害及對于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之要求》,《淮陰黨史資料》總第11輯。
⑤《全國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guān)戰(zhàn)時財產(chǎn)損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584。
⑥《抗戰(zhàn)八年全國分省人民傷亡估計總表》,遲景德:《中國對日抗戰(zhàn)損失調(diào)查史述》,國史館印行:第140頁。
⑦《江蘇省公私文物損失數(shù)量及估價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1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