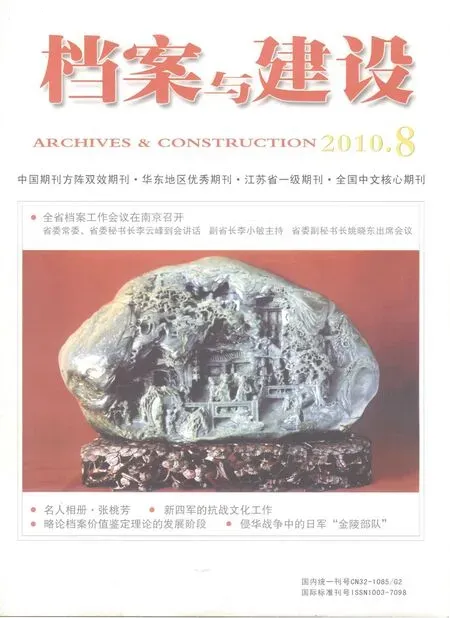略論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的發展階段
□王仁秋 鄒吉輝
檔案價值鑒定理論是認識檔案管理和利用規律的科學總結,是檔案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隨著社會和檔案實踐與理論的發展而發展。本文簡要論析其發展階段與關系。
一、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發展歷程簡述
檔案價值鑒定理論是檔案工作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也是檔案人對檔案工作規律長期探索的認識積累。縱觀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孕育期、誕生期、成長期、變革期四個階段。現簡述如下:
(一)孕育期(中世紀—19世紀)
檔案價值鑒定理論孕育于檔案整理實踐和理論。文獻資料和實踐經驗證明,人們對檔案利用價值的感知和重視經歷了從檔案內容到形成者社會職能的漫長的歷史過程。在檔案數量極少與利用率極低的上古時代,文件、檔案、圖書沒有嚴格的區別,實行一體化管理,檔案整理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也就沒有檔案價值鑒定的需要。隨著文件、檔案、圖書生產量、利用量及其管理難度的不斷增大,三者分離已是大勢所趨,一體化管理逐漸解體,于是中世紀出現了相對獨立的檔案管理工作,檔案整理的需要也就隨之日益凸顯出來。當此之時,管理者憑著檔案利用的實踐經驗所形成的對檔案價值的直觀感受,著眼于借鑒解決具體問題的歷史經驗,開始了以內容聯系為指向的檔案整理工作,于是就有了檔案整理的“事由原則”。倘仔細解讀這一整理原則,就會發現它的出現,一是基于對檔案內容的利用價值的實際需要,二是基于對檔案內容利用價值鑒定的朦朧思想(潛在意識)。其后的“來源原則”(全宗理論)則從機構職能的社會作用方面為人們提供了認識檔案價值的新視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檔案整理及其“事由原則”、“來源原則”實際上也蘊含了一定的檔案價值鑒定思想,至今仍有學者把檔案管理業務歸納為“六個環節”,其中檔案整理工作就包含著檔案鑒定內容,由此亦可證明檔案整理一開始就孕育了檔案鑒定。
(二)誕生期(20世紀初葉)
19世紀末,荷蘭檔案學者繆勒、斐斯和福羅英合作出版了《檔案的整理與編目手冊》(簡稱《荷蘭手冊》),該書的問世既宣告了以“來源原則”為核心的檔案整理理論的正式確立,也充當了催生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的助產士。20世紀初,普魯士檔案學者邁斯奈爾提出“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的觀點(通稱“年齡鑒定理論”),檔案學界公認該觀點標志著“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的誕生,開啟了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研究和建設的先河。
(三)發展期(20世紀20年代—50年代)
這一階段在“來源原則”和“年齡鑒定理論”等檔案學理論的影響下,出現了“行政官員決定論”、“職能鑒定論”和“雙重價值論”;也在經濟學理論的影響下出現了“效益因素鑒定論”。
1922年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在其代表作《檔案管理手冊》中提出鑒定應由行政官員自行決定的主張,即所謂“行政官員決定論”,試圖解決檔案價值鑒定主體問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蘭檔案學者卡林斯基提出了“職能鑒定觀”,認為檔案價值大小與形成機關地位和職能重要程度具有正相關性的特點,主張檔案文件價值及保管期限應按照文件形成機關在政府機構體系中地位和職能的重要性來確定。
1946年,美國檔案學者波爾提出把保存費用作為檔案鑒定要素之一,但這種實用主義觀點不僅沒有引起重視,反而遭到了一些檔案人員的批評。
1956年,美國檔案學者謝倫伯格出版其代表作《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提出公共文件具有第一價值和第二價值的鑒定理論(即“雙重價值論”),第一價值是對原機關的原始價值,包括行政管理價值、法律價值、財務價值和科技價值;第二價值是對其他機關與個人利用者的從屬價值,包括證據價值和情報價值(也稱研究價值)。筆者以為,謝倫伯格所謂“第一價值”當為“文件價值”(或謂“歸檔文件價值”),“第二價值”才是檔案價值。
(四)變革期(20世紀50年代后)
這一階段,由于文件數量的驚人增長、文件類型的日益復雜,社會對檔案利用范圍的擴大,給鑒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加上后現代主義思潮和新興科學技術的影響,檔案學者和管理者對鑒定的新理論、新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在檔案價值鑒定的認識上有了一些新變化,出現了“利用決定論”、“宏觀鑒定論”等要求變革的新觀點。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檔案學者菲斯本、布里奇弗德等提出了“利用決定論”,他們主張一切從利用者角度出發,強調學者需求是判斷文件價值的決定性標準。
60~80年代,由于謝倫伯格等人在50年代就倡導檔案價值鑒定應考慮檔案保管費用,波爾的檔案鑒定效益觀才在60年代引起廣泛關注。美國布里奇福特在《檔案與手稿:鑒定和登記》中明確提出了“效益因素鑒定標準”,他認為檔案鑒定應充分考慮存儲、保管、處置文件費用等因素,并強調一種嚴格而實在的費用和核算是所有例行鑒定工作的一個必要條件。美國的弗蘭克·博爾斯和朱莉婭·揚在1985年第二期《美國檔案工作者》雜志上撰文提出保管費用是檔案鑒定標準之一。此后,效益標準作為一種非文件價值關系因素的鑒定標準,被各種鑒定體系廣泛采用。
80~90年代,出現了“宏觀鑒定論”,這一觀點主要包括德國檔案學者布姆斯提出的“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美國檔案學者塞穆爾斯提出的“文獻戰略”和加拿大檔案學者特里·庫克提出的“宏觀鑒定戰略”,他們都立足于宏觀角度,超越傳統鑒定理論中的價值標準,認為檔案價值是社會自身價值的反映,強調職能鑒定標準。
二、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發展的歷史背景
檔案價值鑒定理論誕生至今已有百余年歷史,各種觀點的產生,無不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時代印記,反映了一定社會認識和實踐的發展水平,顯示了檔案價值鑒定理論建設中各種關系協調發展的過程。
(一)檔案老與新的關系
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老檔案在不斷消亡,新檔案在與日俱增,這是文件生命周期的自然現象和檔案資源變化的必然規律。因此,自有檔案工作以來,如何處理新、老檔案關系的問題就一直困擾著檔案管理者。直到1901年,邁斯奈爾主張“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第一個賦予高齡檔案“免鑒權”,體現了“喜新不厭舊”的價值理念,才從認識和實踐上破解了這一難題,成為開創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第一人。此后,不少國家根據這一理論規定了本國檔案的“禁毀年限”,有效地保護了高齡檔案,合理調整了檔案結構。
(二)價值鑒定標準的關系
在檔案價值鑒定標準上,先后出現了時間標準、來源(職能)標準和事由(問題)標準、效益標準,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繼承關系或內在聯系。
首先出現的是時間標準。邁斯奈爾關于“高齡案卷應當受到尊重”的主張,實際上就是給出了一個檔案價值時間判定標準,即在檔案價值之間劃定了一條時間界限,根據這條界限把檔案分成“可免鑒”和“不可免鑒”兩類,高齡檔案享有“免鑒權”,非高齡檔案不享有“免鑒權”。德國布倫內克發揚光大了這一鑒定思想。
其后出現的是來源(職能)標準和事由(問題)標準。這兩個標準都是由卡林斯基提出的,其中來源標準(“職能鑒定論”)借鑒了邁斯奈爾和布倫內克的鑒定思想,事由標準借鑒了布倫內克的“自由來源”理論。卡林斯基按照來源標準把檔案保存價值分為A、B兩類,最高行政機關的文件價值最大,屬于A類,需永久保存;低級機關的文件價值較小,屬于B類,可保存一定年限后予以銷毀;并倡導在同類檔案中按照事由標準鑒定單份文件價值。這兩個標準雖然在認識和實踐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但其進步意義卻是非常明顯的:一是發展了邁斯奈爾的來源鑒定思想,二是引入了布倫內克的“自由來源”思想,既豐富了檔案價值鑒定理論,又增強了相關領域理論的聯系性和協調性,實現了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的跨越式發展。
再后出現的是效益標準。保管費用一直是制約檔案工作發展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廣大檔案學者的關注,美國檔案學者率先提出了“效益因素鑒定”觀,主張檔案鑒定應考慮保管費用,這一觀點后來得到各國檔案界的認同。把效益因素作為檔案價值鑒定的一種標準,在一些檔案學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認為效益標準是一種非檔案價值關系因素的鑒定思想。其實不然,從表象上看,保管費用與檔案價值的確沒有直接關系,但檔案價值大小(保管期限長短)與保管費用多少成正比,即檔案價值越大所需保管費用越多,反之亦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鑒定檔案價值就是決定保管投入,因此,效益也就與時間、職能、事由一樣理所當然成為檔案價值不可或缺的關系因素了。
(三)價值鑒定主體的關系
檔案價值鑒定由誰鑒定,不同時期的檔案學者有不同的認識,經歷了由形成者、管理者、利用者從單一到綜合轉變的歷史過程。
早期觀點——形成者鑒定檔案價值。詹金遜認為鑒定應由行政官員自行決定,反對檔案人員參加鑒定和挑選文件,首次明確了價值鑒定主體。
其后觀點——形成者鑒定文件價值、管理者鑒定檔案價值。謝倫伯格在“雙重價值論”中主張“文件原始價值的評定應由文書工作者和其他的機關官員負主要責任”(即形成者為文件價值鑒定主體),原因是“機關官員保存文件是為了供行政、法律和財務方面的現行使用”;檔案工作者應該為鑒定文件的從屬價值承擔最終的責任(即管理者為檔案價值鑒定主體)。可見,謝倫伯格在批判和借鑒詹金遜鑒定觀點的基礎上,根據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把價值鑒定區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并按照價值實現方式確定了不同的鑒定主體,構建了由形成者(文書工作者和其他的機關官員)、管理者組成的價值鑒定基本體系,這在價值鑒定理論和實踐上無疑又是一次跨越式發展。
再后觀點——利用者鑒定檔案價值。該論源于謝倫伯格關注史學研究需要的思想,其后繼者菲斯本等人則進一步明確提出“利用決定論”,主張一切從利用者角度出發,突出強調學者(歷史學家)需求是判斷檔案價值的決定性標準。顯然,他們認為利用者才是掌握檔案價值鑒定權的唯一人選,而檔案管理者只不過是利用者的代理人罷了,即代替利用者行使檔案價值鑒定權。把利用者需求引入檔案價值鑒定范疇,其積極性在于凸顯了檔案和檔案工作的社會性,其局限性在于狹隘的價值觀,必然導致價值鑒定隨意性、結構體系零碎性和歷史原貌破壞性等嚴重后果。因此,該觀點后來遭到了美國檔案界的批評和否定。
我國實行的“三結合”鑒定工作方式,在吸收來源思想合理成分的同時,兼顧了檔案形成者、管理者、行政者各方特點,通過優勢互補和縱橫互動,為鑒定標準把握的準確度、價值區分的合理度、鑒定工作的穩定度等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為世界檔案價值鑒定理論和實踐提供了中國模式。
(四)利用價值形態的關系
檔案有何利用價值及其具體表現形態,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自有檔案價值鑒定工作以來,檔案學者就在努力不懈地探索,據現有資料分析,大致經歷了一個從近到遠、從粗到細、從淺到深、從經驗到理論、從模糊到清晰的認識轉變過程。
在檔案價值鑒定理論誕生前,人們對檔案利用價值的認識尚處經驗階段,從利用實踐中看到的多是形成者近期查考的憑證價值,因此大多對檔案持“喜新厭舊”的態度。
邁斯奈爾的“年齡鑒定理論”,揭示了檔案價值的時間形態,喚醒了人們重視檔案長遠價值的意識,使檔案利用價值認識開始步入理論階段。
無論是早先反對鑒定,還是后來提出“行政官員決定論”,詹金遜都認為檔案“證據的神圣性不可侵犯”,至此,學者看重的仍是檔案價值的證據形態。
謝倫伯格的“雙重價值論”,在繼承來源思想的基礎上,借鑒了邁斯奈爾和詹金遜的價值觀,第一次根據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揭示并論述了價值階段性和不同階段價值的存在形態、作用范圍、實現方式等,構建了由現行文件價值(即原始價值——行政、法律、財務和科研用途)、近期檔案價值(證據性價值)、長遠檔案價值(情報性價值)組成的價值基本體系(文檔價值鏈),從而使檔案價值鑒定理論實現了從粗放、零散、模糊到精細、系統、清晰化的歷史性變革。謝倫伯格因此成為世界檔案鑒定理論史上一位劃時代的大師。
(五)價值特性的關系
檔案價值有何特性,對此認識也經歷了“實用性”→“記憶性+實用性”的歷史性轉變。
檔案價值“實用性”,就是把檔案僅僅視為一個歷史經驗基因庫,這一認識建立于粗放型經驗管理階段的實踐基礎。在全宗理論(來源思想)產生以前,人們大多是從借鑒歷史經驗、查找辦事憑證等實用角度來感知檔案價值的,并對檔案價值的感知也僅停留于實踐經驗表層,尚未形成明確的檔案價值鑒定概念。這種基于實用感覺的潛在的價值鑒別意識,卻不自覺地幫助人們把檔案整理從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認識,實現了對檔案整理認識的飛躍,產生了檔案整理的事由原則。
檔案價值“記憶性+實用性”,則把檔案視為一個歷史思想基因庫,這一認識建立于精細化智能管理階段的實踐基礎。全宗理論出現以后,人們發現社會的發展變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又具體反映在每一個組織機構的歷史沿革、職能活動的有機聯系之中,而不是反映于一個個獨立的社會事件。因此,作為記錄社會發展過程的檔案,從宏觀上來看,應該以一個組織機構為一個最大管理單位(即全宗,下同),通過反映每一個組織機構的來龍去脈來維護整個社會的歷史全貌,而不應以一個獨立的社會事件為一個最大管理單位,因為一個個獨立的社會事件只能維護社會的一個個歷史片段,難以維護社會的歷史全貌;從微觀上來看,應該以一項具體業務(問題)為一個全宗內最小管理單位,通過反映一項項具體業務(問題)的來龍去脈來維護整個組織機構的歷史全貌。基于此,人們先在檔案整理,后在檔案鑒定中,選擇來源思想作為宏觀策略,選擇事由思想的合理成分作為微觀戰術,逐漸脫離了檔案價值“實用性”的片面認識,形成了檔案價值“記憶性+實用性”的全面認識。其間貢獻最杰出者一為邁斯奈爾,其“年齡鑒定理論”首開認識先河;一為謝倫伯格,其“雙重價值論”建成理論體系。
(六)價值形成及鑒定方式的關系
隨著文件數量的幾何級數增長、行政機構改革的頻繁發生、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檔案價值形成及鑒定方式經歷了由個體價值微觀鑒定到群體價值宏觀鑒定的歷史性轉變。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檔案鑒定理論和實踐對價值形成及鑒定方式的基本認識可概括為“個體價值微觀鑒定”,即認為檔案價值形成及鑒定或均取決于原機關行政官員(詹金遜觀點),或均取決于利用者歷史學家(謝倫伯格觀點)。
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檔案鑒定理論和實踐對價值形成及鑒定方式的基本認識逐漸轉為“群體價值宏觀鑒定”。
首先是布姆斯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社會分析與職能鑒定論”,認為檔案價值應當是社會自身價值的反映(即取決于人民大眾),90年代初,該理論基本成熟,主張檔案應體現文件產生時期的社會價值(即以文件形成者職能來體現社會價值),檔案人員在鑒定時需要對文件形成者,特別是其職能進行全面分析。
其次是塞穆爾斯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文獻戰略”,要求以文件的主題作為主要鑒定標準,但因其未脫離“個體價值微觀鑒定”的傳統窠臼(即缺少確定主題的適當方法,適用范圍較窄),在北美檔案界引起爭議。于是在90年代初,她引入“機構職能分析”的觀點來完善該理論,認為鑒定起點不是檢驗具體文件,而是分析文件產生背景,特別是現代社會機關頻繁變動的現實。只有將鑒定著眼點從形成機關的組織結構轉向機關職能,才能準確地判斷檔案文件價值,即依據文件形成機關職能來判斷檔案價值。
再次是特里·庫克于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的“宏觀鑒定戰略”,主張檔案人員在鑒定前需要了解整個社會的運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過程,通過鑒定來準確反映社會發展趨勢與文件形成者及其職能的有機聯系。該理論不再局限于傳統理論中的價值標準,提出應全面考慮社會結構、文件形成過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職能等多種因素,從而使鑒定重點由根據研究目的判定文件價值轉變為根據文件形成者的職能和結構來鑒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來源的重要性。1991年加拿大國家檔案館運用這一理論實施“新宏觀鑒定接收戰略”,其基本思想是,檔案應體現文件形成的相互聯系,檔案價值取決于社會結構,通過社會職能得以體現。為此,采取了更為宏觀的鑒定方法:以文件有機聯系為基礎,以文件來源為中心,要求分析和鑒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計劃、活動和業務的重要性。可見,該鑒定方法的著眼點不再是單份文件的內容或價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職能、任務或活動,顯然超越了傳統理論對文件內容的關注,轉為從形成機關職能、計劃、業務、活動等所表現出來的“宏觀聯系”來關注文件,即依據文件形成機關的職能對檔案文件進行宏觀鑒定。
“群體價值宏觀鑒定”的特點一是在借鑒卡林斯基的“職能鑒定”理論的基礎上,吸收了謝倫伯格鑒定思想的合理成分,引入了后現代哲學的多元價值觀,擴展了檔案價值構成及其鑒定的視域,突出了檔案價值形成的宏觀聯系性。二是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調整視角,更加關注檔案價值生成的社會歷史環境及其發展變化,即把檔案價值鑒定目標定位由形成者自利型轉向形成者自利與社會公益結合型,從而創新檔案價值鑒定理論,使之與時俱進。一言以蔽之,它“反映了現代社會生活聯系日益緊密且呈一體化的宏觀趨勢”。其不足之處是在鑒定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即難以具體化為可供操作的鑒定標準,故鑒定結果不免浮泛、粗放。
總之,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的發展始終與社會發展進程及其對檔案貢獻率的要求程度密切相關,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有可能把握檔案價值鑒定理論科學發展的規律和走向。
①黃坤坊:《歐美檔案學概要》,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②黃霄羽:《外國檔案鑒定理論的歷史發展及其規律》,《中國檔案》2003年第9期:28-35頁。
③傅榮校:《檔案鑒定理論發展規律論》,《檔案學通訊》2003年第6期。
④陳兆祦、黃坤坊:《外國檔案鑒定工作的發展與啟迪》,《檔案與建設》2003年第4期。
⑤張關雄:《外國檔案鑒定工作的歷史分期與鑒定理論述評》,《山西檔案》1995年第6期。
⑥鄒吉輝:《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化歷程回眸與啟示》,《檔案時空》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