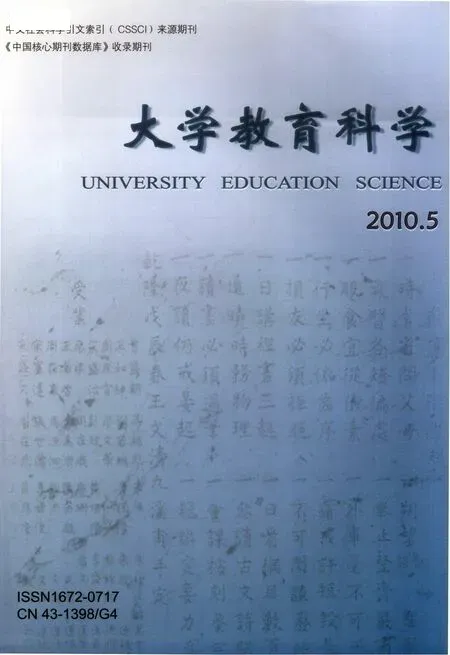被縛的大學科研及其解放*
劉 皛
(湖南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被縛的大學科研及其解放*
劉 皛
(湖南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十九世紀早期,科學研究正式成為大學的一項重要職能,并通過研討班、實驗室、研究所等形式逐步制度化,大學演變為一個龐大的科研基地,成為人類科學發展的發動機。大學通過行使科研職能培養具有反思與批判精神的學者,促進知識的創新與超越。大學科研對于人類思想和精神的意義,恰如帶給世人知識火種、開啟人類智慧之門的天神普羅米修斯,就其在中國所處的境況而言,同樣也遭受著與普羅米修斯相同的“被縛”厄運。
一、“被縛”現象種種
在我國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政府是科研活動的主要控制者和管理者,擁有大學科研資源的配置權,它通過設立名目繁多的課題項目來劃撥科研經費,科學研究很大程度上被框定在課題項目當中。在這樣的科研管理體制下,大學科研備受束縛,具體表現為:“跑”出來的課題與項目、“趕”出來的論文與報告,“堆”出來的研究成果。
同行評議在科學研究的評價體系中具有較高地位,科研的精英性和高深性決定了只有相關學科領域內的專家學者才能裁決科研成果的優劣。在中國的人情社會當中,同行評議已面目全非,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會大大干擾同行評議的公正性。“跑課題”、“跑項目”是評審和獎勵活動中必須的一環,導致許多情況下評價不是基于科研成果本身,而是根據研究者的資歷和背景,甚至是官階和層級。被異化的同行評議當中,包含了太多的人情因素和利益勾連,直接影響著客觀公正的評價準則。研究者申請到課題與項目之后,就要按照申請課題時所做的承諾,定時、定量地產出科研成果。而思想只有在自由狀態下才能產生創造力,如果在研究者腦袋上套一個時間“緊箍咒”,無限的思想面對有限的時間,必將使科研成果不得不依靠“催生”。在時間的限制下,論文和報告得靠“趕”;在數量的限制下,研究的成果需要“堆”;在時間和數量上達標的科研成果,其質量卻難以保證。同時,在科研評價體系中,對論文的發表也有剛性要求,對刊物級別的限制使論文發表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相關利益鏈條孕育而生。
韋伯在《以學術為業》中說到:“如果一個人不能用熱情去做一件事,這件事對于作為一個人的他來說就毫無價值。……熱情是決心,亦即‘靈感’的前提。”[1]在大學科研“跑”、“趕”、“堆”的現象當中,科學研究的熱情可謂冰消瓦解,所制造出來的科研成果價值幾何讓人質疑,更談不上其中能夠有多少“靈感”帶來的創新之處了。科學研究所需要的“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被束縛,科學道德與學術責任開始動搖。
二、“被縛”原因分析
“被縛”現象概而論之,即是缺乏理性傳統的個體被拋入邏輯顛倒的制度漩渦,裹挾其中,只能隨大流而動。可見,大學科研的“被縛”,一方面源于邏輯混亂的科研體制;另一方面,“重道輕理”的文化傳統也難辭其咎。
我國的科研體制以課題制為核心,課題制圍繞科研評價活動展開,科研評價的結果是資源配置的前提,也是科研的指揮棒。在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引導下,科研活動成為了爭奪資源、爭取經費的斗爭,國家將資源和經費投入其中,在一個短暫的研究周期結束后,生產出數量眾多的“科研成果”,但其中真正有價值的卻屈指可數。結果導向型的科研評價體系是邏輯混亂的,這在評價的主體、標準和手段上均有體現。評價的主體雖然由各學科資深學者組成的專家評議組充當,但由于科研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為了實現對資源利用方法及途徑的完全掌控,科研評議團隊由政府出面組建,因此,真正的評價主體還是政府。評價的標準是量化的、等級化的,這就有悖于科研活動自身的唯一性、創新性和不確定性。評價的手段主要是依靠同行評議,而在一個注重人情世故的行政化學術共同體里面,同行評議被異化了,拼關系、拼地位、論資排輩的現象不可避免地出現在科研評價之中。在這些邏輯顛倒的現象背后,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政府對科研資源的壟斷,科研活動被禁錮在政府構筑的科研體制框架內。
科研“被縛”與文化傳統的羈絆也密不可分。在中國傳統的士人文化中,強大的道德傳統對應著虛弱的知識傳統,特別是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在中國傳統士人眼中“不外象數形下之末”,甚至被狹隘地以為是“奇技淫巧”。知識在中國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領域,“為知識而知識”、“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在中國缺乏根基,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擾和攻擊。市場經濟與商品社會的發展如江水洪流來勢迅猛、泥沙俱下,從事科研活動的學者如果沒有堅定的科學信念,難免不被裹挾其中,失去理性的判斷力。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以“道”自重,但道”之無形使之僅能以學者的個體人格作為擔保,一旦孤立的個體面對強大的政治權勢壓迫,也難免不會“曲學阿世”。科學不是名利驅動的產物,也不是向外界牽制低頭的妥協者,它象征著尊重事實、追求真理的態度和精神。“重道輕理”的文化傳統影響下,理性的質疑、批判精神相對匱乏。
三、解縛之途
大學科研的“被縛”根源于體制和傳統,解縛之途也取徑于此。但從影響程度上看,二者仍有主次及顯隱之分。中國近代以來的科學發展,從“五四”前期中國科學社成立及《科學》月刊問世,至今約百年歷史,中國學人對科學的理念、精神、方法、內容已有全新的認識,雖然認識的深厚程度不及西方,但隨著思想領域的愈加民主開放,科學精神終會由表及里,最終達至滲透貫通。因此,思想領域的開放是科研解放的前提,大學科研的解放,首要的是通過科研體制的改革,為思想提供一個寬松的生存空間。
布爾迪厄認為,科學場域是兩種資本并存的場所:一種是科學本身的權威性資本,另一種是施加于科學世界的權力資本。后一種資本可以通過不是純粹的科學途徑 (即尤其是通過科學世界所包含的體制機構)來積累,它是施加科學場域的現世權力的官僚根源的體現[2]。科學場域要獲得更大的自主,必須要削弱體制所帶來的權力資本。因此,要推進科研體制改革,首先,也是核心的問題是權力關系的轉變,即政府把科研評價及監管權交給“第三方”中介機構。如果政府既是科研資源的掌控者又是科研評價和監督的操盤手,合二為一的角色定位就容易導致“權力尋租”,只有把評價與監管的權力讓渡給第三方中介機構,才能夠保證評價的客觀公正和監管的及時到位。美國大學的科研評價與撥款體系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作為政府資助基礎研究的主要渠道,以科學共同體當中的科學家所組成的第三方“同行評議”為指導,將科研經費劃撥給大學。其次,要在科研評價制度上端本澄源。“同行評議”的結果不是要專家都認同研究的成果,而是讓專家評議組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對研究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和監督,其目的不是考察成果的內容和數量是否達到既定的標準,而是在于鑒定研究的方法是否運用得當、研究的過程是否合乎邏輯、研究的結果是否經得起推敲。評價制度改革的關鍵是革除重數量、輕質量,重結果、輕過程的評價原則,增加評價的多元性和靈活性。再次,要開辟多樣化的科研籌資渠道。政府是“一位長期的,也許甚至是永久的贊助者,他有時慷慨,有時漫不經心,有時十分冷淡,毫不在乎,相當反復無常和易變,片面地采取行動,從來不能完全依靠,總要仔細留神”[3](P178)。大學科研的財政命脈如果僅僅依靠政府來維系,必然受到極大的限制。科研資助渠道的多樣化,能夠提高大學科研的穩定性與自主性,規避政府科研撥款中的不穩定因素。“大學達到能多樣化籌資的程度,特別通過第三條非政府撥款的資金源流,大學就處于能在內部把資金滾動流向科研和最以科研為中心的教學階段的地位。”[3](P263)科研經費來源的多樣化還能夠加強大學與地方、大學與產業之間的密切合作,從而促進大學、政府、社會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
大學科研的解放要圍繞制度的變革而展開,制度的變革意味著利益格局的調整、權力結構的變化,并與其他相關制度的變革相伴而生。因此,大學科研的解放勢必與大學整體的解放相輔而行。
[1][德]馬克思·韋伯.倫理之業 [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0.
[2][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科學之科學與反觀性 [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95.
[3][美]伯頓·克拉克.探究的場所——現代大學的科研與研究生教育 [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010-05-10
劉 皛 (1983-),女,云南昆明人,湖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