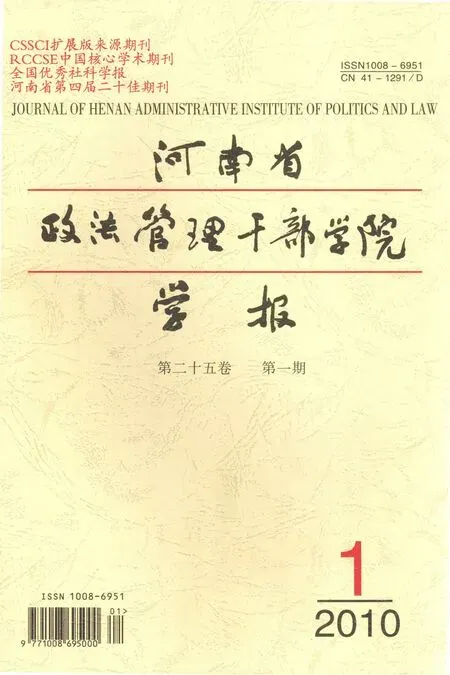論“客觀處罰條件”的若干問題
黎 宏
(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4)
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犯罪構成是具有社會危害性、違法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的類型,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唯一標準;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就意味著該行為達到了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必然要承擔刑事責任,不存在行為雖符合犯罪構成但沒有達到應受刑罰處罰程度的情形,換言之,在我國的犯罪構成當中,沒有德日刑法學中所謂“客觀處罰條件”的存在余地。但是,近年,有些學者提出,我國刑法的規定當中,盡管沒有客觀處罰條件概念的存在余地,但類似于“客觀處罰條件”的內容卻是存在的,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丟失槍支不報罪中的“造成嚴重后果”、第三百九十七條濫用職權罪中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等都屬于此,并受德日刑法學中的“客觀處罰條件”論的啟發,將這些內容定義為“超過的客觀要素”或者“犯罪的附加要件”,認為它們雖是犯罪構成的內容,但和作為該罪的主觀要件的故意、過失無關①張明楷:“‘超過的客觀要素’概念之提倡”,載張明楷、黎宏、周光權著:《刑法新問題探究》,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7頁以下。另外,提倡類似見解的論文還有,劉士心:“犯罪客觀處罰條件芻議”,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 1期;陸詩忠:“芻議‘客觀處罰條件’之借鑒”,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 5期;梁根林:“責任主義原則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觀處罰條件的考察”,載《清華法學》2009年第2期。。
可是,在日本,近年,對傳統的客觀處罰條件概念進行批判,主張將其還原為違法要素,同樣受責任原則的支配,在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內的見解日漸有力[2];同時,在我國刑法當中,所謂“超過的客觀要素”或者“犯罪的附加要件”在具體犯罪構成當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是否獨立于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范圍之外的客觀要素?其和我國刑法所堅持的責任原則該如何統一協調?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當中,沒有“超過的客觀要素”存在的空間,也沒有必要提倡這種概念。以下,結合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和刑法規定,對上述觀點進行簡要說明。
一、“客觀處罰條件論”
和德日等國不同,在我國,成立刑法當中所規定的犯罪,多數情況下,僅僅有違反行為還不夠,該行為還必須“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即便在一些不要求“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犯罪當中,就實際的應用而言,司法機關在是否成立犯罪的認定上,也往往有一定結果的要求。如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偽造貨幣的”,成立偽造貨幣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金。僅從法條規定來看,成立本罪,似乎只要具有偽造貨幣的行為就夠了,沒有其他要求。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當中,并非如此。成立本罪,偽造貨幣的總面額必須在 2000元以上不滿 3萬元或者幣量在 200張 (枚)以上不足3000張(枚),否則就不能成立本罪①參見 2000年 9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1條。。換言之,在我國,刑法明文規定,成立犯罪,行為通常必須已經造成一定的實際損害結果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這一點,和刑法當中僅僅將實施一定行為作為犯罪成立要件(過失犯除外)的日本相比,存在著巨大差別。
由于刑法明文規定行為只有在“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等場合才能成立犯罪,因此,這種“嚴重后果”或者“其他嚴重情節”在具體犯罪構成當中,屬于何種要件,處于什么地位,難免有爭議。有學者將其作為客觀處罰條件對待,如認為盜竊罪中的“數量較大”、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當中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之類的要件是客觀處罰條件,在不具備客觀處罰條件的情況下,可以成立犯罪,但是,不應受到刑罰處罰[3]。另有學者盡管沒有使用“客觀處罰條件”一語,但也認為盜竊罪中的“數量較大”、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當中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之類的要件是獨立于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不屬于行為人主觀認識的內容,和確定行為人的故意或者過失沒有關系,而僅僅是表明行為對法益侵害程度的數量要件,并依據這種觀點創設了自己的犯罪論體系②陳興良:《陳興良刑法教科書之規范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6頁、第 97頁。按照陳教授的理解,犯罪成立要件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即罪體(主體、行為等),罪責(故意、過失等)和罪量(數額、情節),即將罪量作為獨立于成立犯罪的行為、主體和故意、過失之外的要件。。這兩種觀點,盡管在用語上略有差別,但在認為盜竊罪中的“數量較大”、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當中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等都是獨立于犯罪成立要件之外的獨立要件,不在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范圍之內的一點上,具有相同之處,因此,可以看做為同一種觀點。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值得商榷。其不僅違反了我國有關犯罪構成的基本理論,而且,還有誤導司法實踐之虞。
首先,上述觀點錯誤地理解了所謂客觀處罰條件,將犯罪結果和客觀處罰條件混為了一談。所謂客觀處罰條件,是指和犯罪成立無關,僅僅與行為人是否受罰有關的客觀事實。一般認為,這種事實不能還原為犯罪成立條件,而只能理解為一種政策性事由,換言之,所謂客觀處罰條件,是和是否成立犯罪無關,只是和是否對行為人予以刑罰處罰有關的事實[4]。這種客觀事實,顯然和盜竊罪中必須造成“數額較大”的財物被盜等不可同日而語。在我國,按照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犯罪只能是嚴重危害社會,依法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其中,“嚴重危害社會”的法律表現,就是侵犯了“數額較大”的財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行為人僅只實施了某種危害行為,但是沒有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后果的話,就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按照我國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不能被認定為犯罪。可見,引起或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結果,是判斷行為是否嚴重危害社會的前提,是具體犯罪的成立條件。既然如此,就決不能說“數額較大”、“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是和犯罪成立無關的客觀處罰條件。
3.5.2 局部麻藥和放射線的應用 口腔治療采用的麻醉一般都是局部麻醉,使用的麻藥是利多卡因或阿替卡因,且用量較小,不會導致胎兒畸形,孕婦可以放心使用。研究表明,電離輻射劑量<5 mrad時不會對胎兒造成危害。拍攝一張普通牙片的輻射劑量僅為0.1 mrad,所以為了協助診斷,必要時孕婦佩戴頸圍和鉛放射服可以拍攝牙片。
其次,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當中,不可能有所謂客觀處罰條件或者與其類似的因素存在的空間。我國的刑法理論認為,犯罪構成是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唯一標準,行為人的行為只要符合刑法分則所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就毫無例外地構成犯罪,應當受到刑罰處罰,不可能出現行為符合某具體犯罪構成之后,還要考慮該行為是不是符合其他條件,然后再決定是否對其刑罰處罰的情形。因為,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成,是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程度的侵害行為和應當作為犯罪加以嚴厲譴責的主觀責任的統一,是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統一,行為符合犯罪構成,就意味著該行為無論是在客觀要件還是主觀要件上,都達到了成立該種犯罪所必要的、值得刑罰處罰的程度,而不可能出現行為在形式上符合了犯罪構成但在處罰上還要考慮其他條件的情形[5],這是從我國刑法第十三條有關犯罪概念的規定當中所得出的必然結論。而上述兩種觀點恰恰在此有問題。其認為在犯罪構成之外,還存在決定行為是不是要受到刑罰處罰的所謂客觀處罰條件,將成立犯罪和是否要受到刑罰處罰割裂開來,無視犯罪就是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違法行為的基本定義,直接違反了我國犯罪構成的基本理論和我國刑法第十三條有關犯罪概念的規定。
再次,按照這種觀點,會得出很荒謬的結論來。如在行為人盜竊了一個價值 300元錢的財物的場合,按照上述觀點,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已經成立盜竊罪或者已經符合盜竊罪的犯罪構成,只是因為所盜竊財物的價值太小,數量不夠①按照 1998年 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1)款的規定,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 500元至 2000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所以才不予以處罰。這種結論顯然不符合我國刑法有關盜竊罪的規定。
二、“超過的客觀要素論”
有學者認為,盡管我國刑法當中,不存在德日刑法當中所謂的客觀處罰條件的存在空間,但是,類似于德日刑法中所謂的客觀處罰條件所說的事實還是存在的。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所規定的丟失槍支不報罪②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依法配備公務用槍的人員,丟失槍支不及時報告,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作為成立要件之一的“造成嚴重后果”,就是如此。因為,“本罪中的‘造成嚴重后果’雖然是構成要件,但不需要行為人對嚴重后果具有認識與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造成嚴重后果’便成為超出故意內容的客觀要素,屬于‘超過的客觀要素’”③張明楷:“‘超過的客觀要素’概念之提倡”,載張明楷、黎宏、周光權著:《刑法新問題探究》,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7頁。。這個觀點,從與德日刑法理論中所存在的“超過的主觀要素”相對應的角度出發,論證了與客觀處罰條件類似的“超過的客觀要素”的存在。即“超過的主觀要素”概念表明,有些主觀要素不需要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客觀事實;同理,有些客觀要件也不可能存在與之相應的主觀內容,這便是作者所提倡的“超過的客觀要素”④張明楷:“‘超過的客觀要素’概念之提倡”,載張明楷、黎宏、周光權著:《刑法新問題探究》,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7頁。。這個觀點,跳出了德日刑法學當中長期以來一直受到非議的、為了說明客觀處罰條件不是犯罪構成要件,就先說明其不是故意、過失的認識對象,但在說明故意的認識內容時,又主張其受作為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的制約的循環論證的窠臼,讓人耳目一新。
但是,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的丟失槍支不報罪當中的“造成嚴重后果”果真就是所謂不在行為人認識范圍之內的“超過的客觀要素”嗎?答案是否定的。
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的丟失槍支不報罪,是指“依法配備公務用槍的人員,丟失槍支不及時報告,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和盜竊罪中行為人的盜竊行為直接引起了他人占有的財物被盜、故意殺人罪中行為人的行為直接引起了他人的生命被剝奪的情況不同,在丟失槍支不報罪中,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嚴重后果”,不是由丟失槍支的行為人本人所引起的,而是指其他犯罪分子利用該丟失的槍支所造成的[6],這種結果能否看做為行為人本人的不報告行為所引起的危害結果,成為問題。在國外,之所以將“就任公務員”看做為事前受賄罪的客觀處罰條件、將“確定宣告破產”看做為欺詐破產罪的客觀處罰條件,就是因為“就任公務員”是受賄行為人以外的、具有任命權的第三人的行為結果,而“確定宣告破產”也是欺詐破產行為人以外的法院的行為結果。這種將行為人以外的第三人實施的行為事實作為決定行為人是不是構成犯罪的情形,對于行為人而言,當然是其難以預料的,所以,應當放在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外。這也是承認客觀處罰條件的最主要理由[7]。
但本文認為,這種由第三人所引起的結果,是決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重要因素,屬于該罪的構成要件結果,應當在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范圍之內。理由如下:
一方面,由行為人之外的第三人所引起的結果,在表明不報告行為具有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的一點上,和行為人本人引起危害結果的場合一樣,二者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二者之間的不同僅僅在于,在以發生犯罪結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當中,行為的因果發展趨勢由于和行為對象相遇而引起了法益侵害,而在以客觀處罰條件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當中,同樣的行為因果發展趨勢由于和“客觀處罰條件”相遇,而使得先前已經存在某種危險增大到了可罰的程度[8]。如在故意殺人罪當中,由于子彈射中被害人、奪走其生命而使該行為的危險達到最高程度而成為現實即既遂,同理,在丟失槍支不報罪中,由于丟失槍支不報者之外的其他人“造成嚴重后果”,使得先前的丟失槍支不及時報告行為當中所潛在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險,轉化為了現實的可罰的危險。
另一方面,并不是只有和行為人的行為有因果關系的要素才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具有影響。如刑法第三百四十條所規定的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行為人只有在“禁漁區”、“禁漁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撈水產品,情節嚴重的場合,才能成立犯罪。這里,“禁漁區”、“禁漁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盡管是決定行為是不是具有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的要素,但其和捕撈行為之間,顯然不具有因果關系。可見,那種認為只有和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事實才是影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見解,是不妥當的。
既然“造成嚴重后果”在丟失槍支不報罪的構成要件當中如此重要,那么,從刑法第十四條規定的立場來看,其當然應當在行為人的認識或者說預見的范圍之內。因為,行為人只有在對自己行為所可能引起的危害結果有認識和預見時,才能明白自己的性質,從而打消其實施該行為的念頭。行為人若只是對自己的行為性質有認識,而對于該行為所可能具有的后果沒有認識,那么,就是屬于行為人不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結果的情形,不符合刑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因此,從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故意的角度來看,也必須說,“造成危害后果”,是成立故意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相反地,將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當中的“造成嚴重后果”之類的要件作為“超過的客觀要素”,將其放在行為人的主觀認識之外的做法,也違反了近代刑法所主張的責任原則。責任原則的基本意思是:行為人只對在行為時所認識到或者所能夠認識到的外部事實承擔責任。如行為人在對遠處的物體開槍時,如果根本沒有意識到或者也不可能意識到對象是“人”的時候,即便客觀上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結果,但也不得以故意殺人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從我國刑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以及第十六條的規定來看,我國刑法也堅持了這一點。即成立犯罪,行為人必須對客觀的犯罪具有認識或者預見,或者具有認識或者預見的可能性,否則,即便造成了客觀侵害結果,但也不能成立犯罪。就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所規定的丟失槍支不報罪而言,“造成嚴重后果”可以說是成立該罪所必不可少的結果,屬于該罪的客觀構成要件。既然如此,怎么能將其排除在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外呢[9]?
對于上述觀點,最近有學者撰文主張,責任原則并非沒有任何例外的教條。客觀處罰條件是基于刑法以外的目的設定即控制風險的公共政策需要而設置的犯罪成立條件,是責任主義原則的例外,提倡合目的、有節制地對刑事責任原則創設諸如客觀處罰條件等必要的例外[10]。但是,在我看來,該文存在兩方面的嚴重缺陷:一是該文對于所謂“客觀處罰條件”存在誤解。其將盜竊罪中的“數額較大”、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當中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等都作為“客觀處罰條件”,這顯然沒有超出我國傳統觀念將“犯罪結果”和“客觀處罰條件”混為一談的窠臼;另一方面,對責任原則的例外存在誤解。作為近代刑法基本原則的主觀責任原則,盡管說在關注社會防衛、強調刑罰的一般效果的英美等國,具有刑法客觀化優先、責任原則弱化的跡象,但是,這種理解可能是一種誤解。實際上,即便在英美的學者也認為,“事實上,說犯罪這種法律上所禁止的行為,是以無過錯責任的基礎來加以禁止的,除非被告人提出證據,清楚地證明沒有過錯”,“任何刑事責任情形都不可能完全不需要犯罪意圖”[11]。承認作為責任原則的例外的客觀原則或者說嚴格責任,長期來看,不僅難以實現其追求一般預防的初衷,反而有弱化一般預防效果以及特別預防效果的趨勢。因為,客觀責任和嚴格責任是對沒有主觀責任的人進行處罰,使人們對法律產生不信任感,結果讓一般人喪失守法意識,而且就受到處罰的行為人而言,由于其運氣不好而受罰,刑罰對其難說具有感召力,因此,也難以奢求刑法對其具有防止再犯的特殊預防效果[12]。這樣說來,擴大責任原則例外的應用范圍,并不是一件好事。
實際上,提倡超過的客觀要素的學者并不完全否認“造成嚴重后果”之類的要素和故意、過失之間存在某種關系,只是主張二者之間只要像結果加重犯的場合一樣,行為人對于結果具有認識可能性即過失就可以了[13]。但是,這種看法自我矛盾。因為,行為人既然格外強調上述要素是不在行為人認識范圍之內的“超過的客觀要素”,何來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發生該結果的可能性的認識呢?而且,和結果加重犯不同,在所謂“超過的客觀要素”成為問題的犯罪類型當中,基本危害行為 (如丟失槍支不報罪中的“丟失槍支不及時報告”行為)本身并不是犯罪(單純的丟失槍支不報行為是違反《槍支管理法》的一般違法行為),不具有值得刑罰處罰程度的可罰性,這就意味著行為人僅對基本行為有認識而對所發生的后果沒有認識的場合,還不足以喚起其違反刑法規范的意識,不符合成立該罪所要求的主觀要件;而在結果加重犯如故意傷害 (致死)罪的場合,基本行為即故意傷害行為本身就是犯罪,行為人只要對該行為具有認識,就可以說其具有刑事違法性的意識,符合成立犯罪所需要的主觀要件。因此,比照結果加重犯,認為在將類似于客觀處罰條件要素的犯罪類型當中,行為人不要求對該要素具有認識,只要具有認識可能性的觀點在說理上也具有值得商榷之處。
在我國,提倡“超過的客觀要素”的學者認為,承認超過的客觀要素,能夠解決部分犯罪中不能區分此罪與彼罪,也不能做到罪刑相適應的問題。如刑法第三百三十條規定的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行為人都是出于故意實施妨害傳染病防治的行為,并且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但法定刑較低: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 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認為本罪由故意構成,即對引起甲類傳染病的傳播持希望或者放任態度,那么,就不能對本罪與危害公共安全罪進行合適區分,也不能做到罪刑相適應[14]。
筆者認為,上述看法也值得商榷。在堅持將行為及其危害結果等客觀因素作為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基礎的客觀主義刑法觀的時候,此罪與彼罪的區分,罪刑是否相適應,首先是根據犯罪行為所侵害的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這些外在因素來考慮,而不是從行為人的主觀方面來考慮,否則,就會落入心情刑法的陷阱。從行為的客觀特征來看,“拒絕供應符合國家規定的衛生標準的飲用水”的行為并不能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投放危險物質罪的行為之間畫等號;而“拒絕按照衛生防疫機構提出的衛生要求,對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污水、污物、糞便進行消毒處理”,其危害性,就馬上達到了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的程度。因為,從行為分類上講,“不消毒處理”或者“拒絕供應”都是拒不履行作為義務的不作為,而與此接近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實行行為通常則是作為,二者之間具有行為結構上的差異,不能同等看待。換言之,盡管行為人對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持希望或者放任態度,但仍不能作為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主要是因為這兩種犯罪在實行行為上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實際上,在行為人明知自己違反《傳染病防止法》規定的不作為行為極有可能“引起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有傳播危險”,而故意拒絕接受檢疫、強制隔離或者治療,情節嚴重,足以和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實行行為同等看待的時候,也完全可以看做以不作為的形式實施通常以作為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①參見 2003年 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若干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
從理論上講,某種犯罪在主觀上,到底是要求故意還是過失,其判斷標準并不在于行為人是不是希望或者放任結果發生這種意志要素,而是取決于行為人對行為以及可能發生的結果是否具有認識和預見。盡管在故意的本質上,國外學說中有多種理解,但是,現在,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行為人只要對行為和結果有能喚起其違法性程度的認識和預見,而沒有打消實施行為的念頭,就足以表明行為具有故意[15]。我國刑法第十四條有關犯罪故意的規定也體現了這一觀念。將“放任”犯罪結果發生這種淡化行為人追求或者希望發生某種結果色彩的形式也作為故意的意志要素,就是其體現。因此,在我國刑法對于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具體犯罪到底是故意犯還是過失犯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其判斷,主要還是看行為人對于可能發生的結果有沒有預見。有預見而不制止的場合,就是故意;能夠預見也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的場合,就是過失;在沒有預見也不可能預見的場合,當然也談不上制止了,也就無所謂過失。行為人對于可能發生的結果有沒有預見,主要是看法條對于行為人違反規范態度的描述以及對其違反規范態度的評價(主要標志是法定刑的輕重高低)。如就丟失槍支不報罪而言,法條對于行為人違反規范態度的描述是,在行為人明知槍支是一種危險物品,失控的話可能會造成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情況下,仍然“不及時報告”,這顯然是行為人明知故犯、故意而為的態度,因此,屬于故意犯罪形態。
至于說丟失槍支不報罪的法定刑很輕,這主要是因為丟失槍支不報罪,客觀上就是一個不及時報告的行為,其和自己用槍殺人的行為相比,其社會危害性要小得多,難以對其進行很嚴厲的譴責。雖然在本罪當中,也有“造成嚴重后果”的情節,但該種后果并不是不報告者本人所引起的,而是由其之外的其他人所引起的;同時,不報告也并不必然引起“造成嚴重后果”。有時候,行為人即便報告了,但也仍然難以找到該槍支。當然,在行為人明知自己的槍支被某犯罪分子偷走之后將要用于殺人,卻仍然不及時報告,以致“造成嚴重后果”的場合,就恐怕不是一個丟失槍支不報罪所能評價得了的。
三、結論
在德日刑法學當中,傳統觀點所主張的、獨立于犯罪概念之外但對犯罪處罰具有重要影響的客觀處罰條件概念正在消失,日漸被看做存在于犯罪概念當中,說明行為的違法性的要素之一;同時,傳統觀念上所稱的其不受責任原則制約的觀念也在逐漸改變,主張就所謂屬于客觀處罰條件的事實而言,行為人必須對其要有認識、預見,至少必須具有認識、預見的可能[16]。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情況也是如此。在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當中,根本就沒有屬于客觀處罰條件的“超過的客觀要素”的存在余地;從犯罪是應受刑罰處罰程度的社會危害行為的角度來看,所謂“超過的客觀要素”,作為和行為人的實行行為具有某種關系的結果,是表明該行為達到了應受處罰程度的具體體現,作為說明該行為達到了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程度社會危害性的標志,應當在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內,而不可能超出其外。
相反地,如果說該因素存在于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外,是獨立的超過的客觀要素的話,可能會引起一系列的理論上的混亂。
首先,可能會混淆犯罪故意和一般違法故意之間的區別。眾所周知,刑法上的犯罪故意和一般違法行為的違法故意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的場合,行為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引起犯罪結果,即應受刑罰處罰程度的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后者的場合,則不要求行為人的認識要達到這種程度。說“客觀處罰條件”或者說是“超過的客觀要素”不在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內,就意味著在以上述因素為構成要件要素的犯罪類型當中,行為人只要對一般違法行為有認識,即便沒有認識到該行為可能導致值得刑罰處罰的結果,也能說行為人具有故意,這實際上是承認“只要具有屬于一般違法行為程度的認識,就是具有犯罪故意”的觀點,取消了二者之間的區別。
其次,會導致追究偶然責任。所謂偶然責任,實際上是結果責任的一種表現形式,它不要求行為人對與行為有關的結果具有預見,只要客觀上發生了危害結果,行為人就要受到處罰。客觀處罰條件或者說是超過的客觀要素盡管是客觀的構成要件要素,決定行為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可罰性,但是,由于不要求其在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內,因此,即便行為人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某種危害結果,但只要不幸引起了該結果的發生,行為人仍然要承擔刑事責任。如配備公務用槍的人在丟失槍支之后,不及時報告,如果該槍支被他人利用,造成人員死傷等結果的話,就構成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所規定的丟失槍支不報罪;但是,如果該槍支沒有被人利用,或者盡管被利用但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話,就不構成犯罪。換言之,本罪中,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不在于行為人本人是否具有主觀上的過錯,而在于其運氣。這實際上是對刑法所主張的主觀責任原則的公然破壞。
再次,會破壞構成要件規制故意的機能。近代刑法以處罰故意犯罪為原則,以處罰過失犯罪為例外,因此,成立犯罪,行為人原則上必須具有故意,即行為人具有故意是成立犯罪的前提。但是,由于故意的內容是對符合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的認識和實現的意思,因此,在結局上,決定成立故意所必要的事實范圍的還是構成要件。換言之,構成要件具有規制故意內容的機能。但是,將作為犯罪成立要件重要組成部分的客觀處罰條件的內容,排除在故意的認識范圍之外,顯然是對構成要件規制故意內容機能的破壞,引起的直接結果是將一些包含有以故意違反法規為實行行為的犯罪認定為故意犯罪①如交通肇事罪就是如此。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行為人只要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就能構成。這里,如果不考慮行為人對所發生的后果是不是具有認識的話,完全可以根據行為人故意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認定其為故意犯罪。。
筆者認為,在將“造成嚴重后果”之類作為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時候,這種要件必須在行為人的認識范圍之內。按照刑法第十四條的規定,這種認識不要求一定是確定的認識,也可以是一種可能性的認識即認識到可能發生該種結果 (相反地,主張“客觀的超過要素”論的學者認為,對類似于客觀處罰條件的要素只要具有認識的可能性就可以了,即對該要素可以沒有認識),因此,在行為人對于自己的行為所可能引起的嚴重后果,確實沒有認識 (預見)的時候,不構成犯罪。當然,如何判斷行為人是不是具有該種認識,則需要具體分析。就丟失槍支不報告,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而言,通常來說,行為人對所可能發生的后果是有預見的。因為,這里的行為人不是一般人,而是依法配備公務用槍的人。這些人對于槍支的性能、使用規則、管理規則等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對于在丟失槍支之后不報告,可能會引起的嚴重后果,應當說是有充分認識的。但在行為人提出反證,令人信服地說明,其對不報告行為所引起的后果,確實沒有認識 (預見)的時候,便不得不說,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本罪。同樣,就玩忽職守罪、違法發放貸款罪等犯罪而言,也必須如此考慮。這種考慮,和將上述要件作為“客觀處罰條件”或者“超過的客觀要素”的觀點,在最終結論上,可能不會有太大差別,但是,筆者認為,這種思考方法更加合乎刑法規定,更加合乎責任原則,因此,更加合理妥當。
[1][德 ]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667;[日 ]大冢仁.刑法概說總論[M].馮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439;[日]大谷實.刑法總論 (新版第二版)[M].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81、458.
[2][日]松原芳博.犯罪概念與可罰性——客觀處罰條件和一身的排除處罰事由 [M].成文堂. 1996.28.
[3]高銘暄,王作富.我國新刑法的理論與實踐[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593.
[4][12][日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 [M].劉明祥,王昭武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64,158.
[5][6]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66,377.
[7][8][日 ]曾根威彥.處罰條件[A].[日 ]阿部純二,等.刑法基本講座第 2卷構成要件論[C].法學書院,1994.320,320.
[9]黎宏.刑法總則問題思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80頁以下.
[10]梁根林.責任主義原則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觀處罰條件的考察[J].清華法學,2009,(2):39頁以下.
[11][美]道格拉斯 .N.胡薩克.刑法哲學[M].謝望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4.214、217.
[13][14]張明楷.“超過的客觀要素”概念之提倡[A].張明楷,黎宏,周光權.刑法新問題探究[C].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75,72.
[15][日 ]大谷實.刑法總論 (新版第 2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06.
[16][日]前田雅英.刑法總論講義 (第 4版)[M].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98;[日]山口厚.刑法總論(第 2版)[M].有斐閣,200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