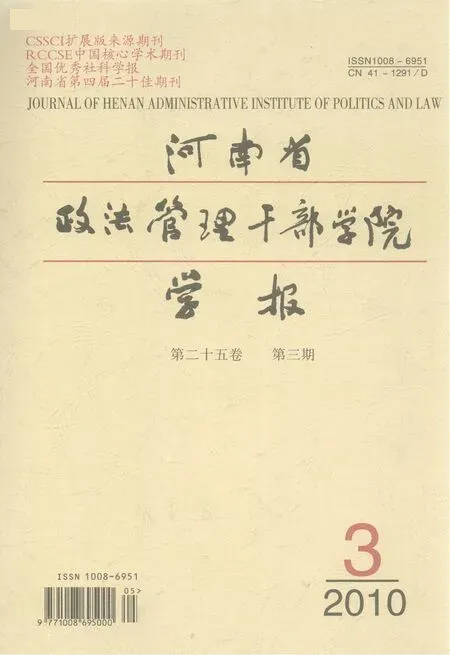刑法總論專題研究(一)
[日]松原芳博著 王昭武譯
(1.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日本東京 1698050;2.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江蘇蘇州 215006)
刑法總論專題研究(一)
[日]松原芳博著 王昭武譯
(1.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日本東京 1698050;2.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江蘇蘇州 215006)
編者按: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松原芳博教授自去年 4月開始在日本《法學·ミナ-》連載《刑法總論專題研究》(每月一期,尚處于連載之中),對日本刑法總論中的重要問題,有別于傳統教科書的體例,作了頗具個人色彩的理論性解說。其特點主要在于,其一,重視犯罪論體系,強調犯罪論體系應該真正成為解釋論解決相關問題的指南;其二,力圖將罪刑法定主義、法益保護主義、責任主義等刑法基本原則滲透至刑法理論之中;其三,立足于法益侵害說(結果無價值論),主張貫徹法益保護主義與自由保障機能;其四,以現代社會中的刑法作用為基點,關注當下的日本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的動向。蒙日本評論社與松原教授無償轉讓版權,由蘇州大學王昭武副教授翻譯,本刊欲以連載,以饗讀者,冀望國外知名學者的這種最新研究成果能多少有助于我國刑法學對相應問題的研究。
刑罰;刑罰總論;刑罰意義;刑罰目的;刑法原則
一、刑罰的意義與目的① 本文原載于日本《法學·ミナー》2009年4、5、6月號(總第652、653、654期)。蒙日本評論社無償轉讓版權,特翻譯以饗讀者。
(一)犯罪與刑罰
例如,因實施了傷害這一犯罪,犯此罪者被科處了 3年懲役這一刑罰。由此可見,犯罪與刑罰作為一對社會現象,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在法律上又處于要件與效果的關系。將犯罪與刑罰作為法律上的要件與效果聯系在一起的,就是刑法(廣義)。
(二)刑罰的概念
那么,究竟何謂“刑罰”呢?刑法第 9條對此作了規定:主刑有屬于生命刑的死刑,屬于自由刑的懲役、禁錮、拘留,屬于財產刑的罰金、科料;附加刑有針對財產犯罪的沒收。歷史上還曾有流放孤島這種流刑、鞭打這種身體刑,伊斯蘭教諸國現在仍保有身體刑。從上述具體刑罰的共同特征來看,對“刑罰”可作如下定義:是以犯罪這一違法行為為理由,由國家有意施加的害惡,其中內含對違法行為的非難。對這種刑罰的共同屬性可稱之為“刑罰的概念”,或者,在不具有這種屬性即不能謂之刑罰這一意義上,又可稱之為“刑罰的本質”。
征收所得稅、《傳染病預防法》上的隔離,雖屬于可強制執行的不利益處分,但在不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不伴有任何非難這一點上,有別于刑罰。另外,基于民法上的不法行為的損害賠償,盡管也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但那不過是通過補償被害人的損失,以謀求當事人之間負擔的公平,而并非有意地施加害惡,也并非必然地內含非難。
另外,基于《少年法》的送至少年院、基于《心神喪失者醫療觀察法》的入院措施,雖也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此類措施以保護、教育、治療為內容,而非“害惡”,也并非有意地對行為人施以非難。不過,送至少年院是為了社會的安全,強制性地剝奪違法行為人的自由,事實上也多少伴有社會性的非難,從這一點來看,將其作為與刑罰性質完全不同的東西來處理,這多少有些危險。并且,《獨占禁止法》與《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課征金①這里的課征金,是針對違反《獨占禁止法》的行為,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命令交付的一定數額的金錢。也稱為“進口課征金”。大致相當于我國的“罰款”。——譯者注、《道路交通法》上的反則(違章)金、訴訟法與行政法領域的過料等,不僅以違法行為為前提,還屬于以此為理由而有意施加的“制裁”,這一點,在制度性質上接近于刑罰。對于課征金與過料,盡管可解釋為,在不伴有倫理非難這一點上不同于刑罰,但既然是以違法行為為理由的不利益,就不可否認,其內含非難,與刑罰的差異無外乎體現在非難的質與量上②③重加算稅與懲罰性損害賠償,也是以違法行為為理由而有意地施加不利益,可以說,部分帶有刑罰性質。。對于這些事實上或制度上部分具有刑罰性質的制裁,要求與其根本性質相適應,適用刑法的基本原則,并給予刑事程序法上的保障,除此之外,刑罰與其他類似刑罰的制裁之間是否形成了二重處罰,也需要研究。
(三)刑罰的正當化理由
1.社會機能、形式合法性、實質正當性。
有意對人施加害惡,這無疑是“犯罪”,原本不被允許。盡管如此,作為害惡的“刑罰”何以存在,又基于什么理由而被正當化呢?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想必可以從滿足社會組成成員的心理需求與確認其歸屬意思,以及政治權力的確證等機能方面,來說明刑罰的存在理由。分析刑罰在現實社會中的事實性機能,這無疑具有一定意義,但那并不能顯示刑罰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從民主主義的角度來看,刑法是國民的代表經過正當程序而制定,由此也能說明刑罰為何被正當化。但是,這種形式合法性,只是刑罰正當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這里就必須考問其實質正當性,也就是,能否比照法的理念合理說明刑罰的存在理由。
2.報應刑論。
正如前述“刑罰的概念”中所看到的那樣,所謂刑罰,在概念上,可謂之針對犯罪的、內含非難的害惡,在此限度之內,可稱之為“報應”,對此并無異議。不限于此,從實現正義的視點來看,認為刑罰屬于針對犯罪的當然的“回報”,這本身就是刑罰的正當化理由,這就是報應刑論。根據刑罰是對犯罪的哪一側面的“回報”,還可將報應刑論細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立場為,刑罰是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具體損害的代償,由此將刑罰正當化。從曾經存在的氏族間的復仇、報仇中,可找出其原型。在這種“被害報應”中,問責主體是被害人以及作為其人格繼承者的遺屬,國家的定位為其代行者;在犯罪論上,重視結果的重大性,不處罰未遂犯與危險犯,但另一方面,故意加害、過失加害以及由未成年人、心身喪失者所實施的加害,在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害這一點并無不同,因而作同等處罰。
這種被害報應的背景在于,利益總和意味著一定的加減為零 (zero-sum)狀況與等價交換。如同經濟交易的情形所反映的那樣,總量一定的財物關系到復數當事人之時,一方當事人的不利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當事人的利益。是否是因為這種加減為零(zero-sum)狀況的經驗已深入到我們的潛意識中,從而抱有加害人的不利益就等于被害人的利益這種印象呢?但實際上,圍繞刑罰的利益狀況并不是加減為零(zero-sum),即便對加害人科以刑罰,被害人的損害也不會由此得到彌補,因此,不能簡單地將二者視為等價交換的對象。
第二種類型的立場為,神與主權者的權威被犯罪所冒犯,或者,法秩序被犯罪所攪亂,刑罰正是對此的反動,由此將刑罰正當化。其原型可以從中世紀的教會法與絕對王政下的刑法中找到。犯罪是對體現人倫的國家法的否定,刑罰正是通過否定犯罪而恢復法,黑格爾的這種刑罰論亦屬于此類型的報應刑。按照此“秩序報應”的觀點,問責的主體是神與國家。可以說,被害報應思想將刑法引入私法框架內,與此相反,秩序報應思想則突出了刑法的公法性質。在犯罪論上,與發生的結果相比,這種立場更重視規范違反意思,那么,雖具有違法性的意識,卻仍然實施侵犯法律的行為,這就是犯罪的基本形式。
無論是神與國王,也無論是國家與法,這種秩序報應思想均以超越性權威的存在及其倫理優越性為前提。這是因為,若不是優越的權威,就不能主張,對反抗自己的行為的反動,這本身是“正當的東西”。
第三種類型的報應刑論認為,基于自己的意思選擇了犯罪行為,刑罰就是對此追究責任,并清算此責任,并由此將刑罰正當化。康德以理性的、自律的人物形象為前提,主張對基于行為人的自由意思而實施的犯罪,以刑罰來報應,這是將行為人視為理性的存在來對待。從康德的這種刑罰論里,可找出此“責任報應”的典型。根據此觀點,刑罰被觀念為贖罪,只要能設想存在真正理性且自律的人,問責者就是行為人自身的內在超自我或者行為人的良心。然而,現實的人未必是自律且理性的,不能期待他們會自己積極地接受刑罰,因此,實際上,只能是國家成為本人的超自我,代之問責。而且,基于責任報應的觀點,在犯罪論上會更重視行為人的責任要件,可以說,這與立足于責任主義的近代刑法是相互調和的。
責任報應以自由意思的存在為前提,但是,這一點未被證明。即便我們自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但我們所有的選擇中,難道沒有隱而不顯的原因嗎?宇宙萬物均受法則性的支配,可唯有人的意思是例外,難道不是不合理嗎?另一方面,若認為人的意思是無原因的,那么,對于這種偶然的產物追究責任,難道不是毫無意義嗎?基于這些疑問,至少對從責任的清算本身中探求刑罰的積極意義的做法,我是有些抵觸的。
對于所有類型的報應刑論,一個共同的問題在于,沒有合理的目的,作為國家制度的刑罰又何以能被正當化呢?報應刑論者究竟是認為對于所有國家制度,不是從合目的性而是從正義的角度來予以正當化,還是主張盡管其他國家制度都是追求現實的目的,但唯有刑罰制度不具有現實的目的?若不將國家視為超越的存在,而將其視為實現國民利益的機構、裝置,那么,作為國家制度的刑罰,也應該作為實現國民的現實利益的手段,從合目的性的角度來將其正當化。
3.一般預防論。
一般預防論基于目的合理的刑法觀,依據對人們實施犯罪的預防效果,而將刑罰正當化。中世紀殘虐的公開刑,是以刑罰執行所產生的威嚇為目的的。但是,這種“儆戒”,是將受處罰的個人作為實現犯罪預防這一社會利益的手段而加以利用,這一點存在問題。對此,費爾巴哈主張刑罰“預告”的抑制作用,也就是,事先設想出經濟學意義上的合理的人物形象,提出若事先預告,刑罰所造成的苦痛要超過由犯罪所得到的快樂,那么,就理應避免人們實施犯罪。如果刑罰預告的心理強制得以完全實現,從此誰也不再實施犯罪,這的確不會出現將個人利用于公益這一問題。但現實情況是,盡管預告了刑罰,仍然有人實施犯罪。為了實證刑罰預告是嚴肅真實的,就必須處罰違反者。對違反者的處罰,就正是出于擔保一般預防的效果這一公益目的而利用了個人。不過,違反者是盡管存在刑罰預告而仍然違反,因此,也只能是甘愿忍受被利用于公益。
對于這種通過比較快樂與不快樂或者進行利害盤算,而試圖讓人們形成反對動機的“抑制刑論”或“消極的一般預防論”,批判意見指出了以下問題:犯罪的抑制效果并未得到科學的實證,除此之外,為了期待產生對刑罰的恐懼心,這會招致無限的重刑化,更會最終導致對責任主義的違反,——因為責任主義要求刑罰與責任相適應。
這樣,各種更加關注價值性層面的作用的觀點開始抬頭。這些觀點統稱為“積極的一般預防論”,其具體內容因論者不同而迥異。
“積極的一般預防論”的第一種類型主張,刑罰的意義在于,通過維持、喚醒國民的規范意識而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對于一度抱有犯罪意思的人,消極的一般預防是為其裝上剎車,但毋寧說,更為理想的是,使規范意識深入內心,讓其不再抱有犯罪意思。而且,在日常教育與日常生活中,規范意識已一定程度上被內在化,因此,刑罰只要在對此予以補充的限度內有助于規范意識的維持即可,毋須對刑罰寄予過多期待。并且,在切斷刑罰與價值的聯系這一點上,過重的刑罰反而有礙于人們的規范意識的內在化,因而,基于內在于刑罰目的中的理由,可排除過重的刑罰。由此可見,作為刑罰的應然狀態,關注規范意識的維持、覺醒的一般預防論值得期待,但也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首先受到批判的是,國家對國民進行規范意識的訓育這種想法是一種權威主義思維。對此,作為規范意識的內容,不是以服從關系為前提的“應該遵守國家的決定”這種意識,而應將其理解為,是源于人的平等或者換位可能性的“法益尊重意識”。對于規范意識的維持、覺醒,也并非是基于他律的方法,而應該是基于觸發各人的內在超自我這種自覺的方法。第二,還存在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為了喚醒規范意識,必須使用刑罰這一“害惡”?對此,該類型的回答為,刑罰是為了傳達規范的重要性與針對犯罪行為的非難的嚴肅性。然而,僅以“嚴肅性的傳達”還不足以說明刑罰是“害惡”,不可否認,最終還得借助消極的一般預防,即由苦痛所形成的強制。第三,另一問題在于,與快樂與不快樂、利害得失的意識相比,規范意識更為復雜,而且,與害惡所形成的抑制相比,要作用于人們的規范意識,屬于作用對象的人與時期的范圍更廣,因此,其效果的可視性或者實證可能性更低于消極的一般預防。
“積極的一般預防論”的第二種類型認為,刑罰的意義在于,確保對規范或者法秩序的“信賴”。概言之,消極的一般預防是對已具有犯罪傾向的“潛在的犯罪人”進行威嚇,“積極的一般預防論”的第一種類型是試圖喚醒說不定就會實施犯罪的“一般國民”的規范意識,而本說是試圖確保說不定會成為被害人的“善良市民”的信賴。的確,對社會的安定而言,信賴法秩序這一點很重要,若喪失了自己正受到法律的保護這種現實感覺,善良市民的守法意識也許會降低。然而,若對作為“潛在的被害人”的國民的信賴的確保在“獨舞”的話,就難免不會以刑罰手段來追求國民的不安感的解消。而且,所謂作為潛在的被害人的國民的“信賴”,是就實現國民所期望的處罰而言的,所謂信賴的“確保”,難道不正是對國民處罰情感的滿足嗎?因此,確保國民的“信賴”,是由抑制以及規范意識的覺醒所形成的犯罪預防之結果,不應將其視為獨立的目的。
“積極的一般預防論”的第三種類型認為,刑罰的意義在于,對規范的妥當性的“確證”。“積極的一般預防論”的第二種類型以作為經驗事實的社會心理的“信賴”作為問題,而本說以觀念的“妥當性”作為問題,認為科處刑罰本身就是對規范的妥當性的確證。然而,這種規范確證論不過是通過“刑罰是對以預防犯罪為目的的規范的確證”這種形式,在言辭上與“預防”聯系在一起,而并沒有將現實的犯罪預防作為其目標。目的刑論致力于現實效果,一般預防論是其中的一種類型,因此,本類型并非這種意義上的一般預防論,毋寧說,應將其視為秩序報應思想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4.特殊預防論。
與上述觀點相反,特殊預防論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防止行為人本身的再犯。
首先,特殊預防最為簡潔的方法就是,將犯罪行為人從社會中隔離開來、排除出去。然而,只要認為刑法是承認犯罪行為人也是社會一員的“共生的法律”,而非針對局外人的“斗爭的法律”,就必須否定永久的隔離或者排除。另一方面,僅以暫時的隔離期內的再犯防止,要說明刑罰的正當化,顯然難言充分。
其次,通過現實科處作為苦痛的刑罰,讓行為人本人形成此后不再實施犯罪的動機,這種特別抑制也是可以想見的。然而,這是作為消極的一般預防的抑制刑在行為人身上的反映。這種特別抑制的問題點,參見前文對抑制刑的解說。
與上述“消極的特別預防論”相反,“改善刑論”或者“積極的特別預防論”的目的在于,通過執行刑罰以改善、教育行為人,并使之回歸社會。在期待行為人“新生”這一點上,此觀點無疑是人道的,也實際促進了監獄內犯罪人待遇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刑罰是害惡,是對對象人的不利益的處分,此觀點又有忽視這一點之虞。而且,為了達到改善、教育的效果,一貫是采取不定期刑,但這會使得受刑人的地位過于不安定。雖然是實施了犯罪的人,國家仍將其作為國民的一員予以教育、改善,可以說,這種設想原本就是一種權威主義思想。因此,與積極的一般預防的情形一樣,作為刑罰的正當化理由的積極的特別預防的內容應該是,以訴之于自覺這種形式來喚醒法益尊重意識。至于其他改善、教育上的舉措,就是利用了刑罰機會的行政措施,應該在征得對象人同意的基礎上方可實施①超出規范意識的覺醒這一意義上的教育、改善措施,有可能偏離刑罰是“害惡”這一概念,它考慮的完全是科處自由刑的情形,對于罰金刑等并不合適。。
5.國家方面的正當化與行為人方面的正當化。
前面已經談到,作為國家制度的刑罰,出于目的合理性的視點,因預防犯罪這一社會利益而被正當化。作為其目標的預防的程度,不是“最大的預防”,而是綜合考慮了對國民自由的限制以及經濟成本的“最合適的預防”。預防的方法也不限一個,是通過符合刑罰的性質且為憲法所許可的數個方法來謀求目的的達到,但其核心應該是,以規范意識的維持、覺醒為內容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
另一方面,處罰的對象人,作為實現犯罪預防這一社會目的的手段,而被迫作出特別的犧牲。通常情況下,為了社會利益而犧牲個人,會得到正當的補償,然而,補償了由刑罰所帶來的損失,就無法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這樣,處罰的對象人為了社會利益而不得不甘愿忍受特別犧牲,其理由難道不正是因為他基于自己的責任而實施了犯罪嗎?為此,各個行為人的刑罰忍受義務,就因為他的“責任”而被正當化②參見 H.Frister,Schuldprizip(1988)。另外,H.L.A.哈特認為,將整個刑罰制度正當化的是一般預防,將針對各個對象人的處罰正當化的是報應(H.L.A.Hart,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1968])。然而,這既是“規則工具主義”的反映,同時其含義還在于,將國家方面的正當化與處罰對象人方面的正當化置于對立位置。。“刑罰必須與行為人的責任相適應”這一責任主義,立足于行為人的視點,劃定刑罰忍受義務的界限,由此也使得刑罰為受刑者所信服。在“目的不使手段正當化”③也就是,不能將目的作為讓某種手段得以正當化的理由。——譯者注這一表述中,預防目的就正如文字所表述的那樣,是擔當“目的”的正當化,而行為人的責任則是擔當“手段”的正當化。這種刑罰忍受義務的正當化,在以行為人的責任為理由這一點上,與責任報應是相通的,但在其責任并非以“回報”為目的這一點上,又與前述責任報應劃清了界限。
誠然,從國家與社會應將實施了犯罪的人也包容其中這一點來看,處罰對象人的不利益,這作為屬于國家方面的處罰正當化理由的“最適當的預防”的一個決定要素,應該納入考慮對象之中,不應將國家與處罰對象人視為對立雙方。但是,在現實中,國家或者整個社會與個人利益相互對立的情形不在少數。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不時呈現出犯罪人與整個社會相互對立的形態。從這種現實情況來看,除了國家方面的正當化,還要求另外加上行為人方面的正當化,這種二元論也有一定道理。
當然,屬于國家方面的正當化理由的犯罪預防效果也并未被科學所證明,不過是推測其具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而已。另一方面,個人意思的自由也并未被實證,盡管是甘愿忍受刑罰這一被動層面,但以“責任”為理由而將刑罰正當化,對此也并非毫無抵觸。國家不過是人的集合體而已,由國家來處罰某人,對此總是懷有疑慮,這也正是“刑罰應限于最小限度”這一謙抑主義的理由之所在。
(四)近期的重刑化傾向與刑罰理論
近年,立法與量刑實務均在向重刑化邁進。繼2001年增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之后,2005年提高了刑法總則中的有期懲役與有期禁錮的最高刑期,同時也提高了性犯罪與暴力犯罪的法定刑,2007年還增設了汽車駕駛過失致死傷罪。而且,全國所有裁判所的死刑宣判案件在 1996年還是個位數,其后逐漸增加,2006年達到了 45起,由此可見,量刑上的重刑化傾向也非常明顯。近期的這種重刑化的背景在于,報應刑論、一般預防論、特別預防論它們各自的內部重心的轉變。
有關報應刑論,能夠看到樸素的被害報應思想的復活與責任報應思想的退潮。增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與汽車駕駛過失致死傷罪,就是順應了交通事故被害人的遺屬的要求,死刑等的量刑理由中也總是提到“被害人的感受”①最近,與被害人相比,關注焦點更集中于其遺屬,媒體更似乎在說,滿足遺屬情感就是刑罰的目的。但是,根據有無遺屬、性格、與被害人之間的關系等因素,刑罰輕重相去甚遠,這難道沒有違反生命價值的平等原則嗎?而且,若重視遺屬情感,勢必導致殺死全家比殺死部分家屬處刑更輕這種不合理的結論。。可以說,2008年導入的被害人參加制度與裁判員制度相輔相成,也是試圖直截了當地實現被害人方面的處罰要求②與此相反,也有意見認為,被害人參加制度的旨趣不在于實現被害人所希望的刑罰,而在于通過參與審判吐露心聲,以期待達到撫慰其心理的效果。但是,如果審判未能實現自己的主張,難道不是反而增加了其不滿嗎?而且,被害人與遺屬參與審判,對被告人的憤怒難道不會升級,反而造成痛苦的結果嗎(我認為,現在的媒體與輿論故意煽動被害人的憤怒,由此反而會將被害人逼入苦境)?另一方面,還有意見認為,被害人參加制度的旨趣在于回應被害人方面想知曉真相的要求。但是,當庭提出量刑意見等,與知曉真相毫無關系。不僅如此,通過公審前整理程序來鎖定爭議焦點、短時期集中取證等等,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所推進的這些舉措,與回應知曉包括行為人的動機在內的真實這一要求,反而是“逆向而行”。并且,重刑化會阻礙被告人開口,向有礙探明真實的方向發揮作用。。立足于這種被害報應思想,責任主義就得不到重視。從故意犯與過失犯之間責任程度差別很大這一點來看,對結果并無故意的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刑罰最高達到 20年,連屬于純粹的過失犯的汽車駕駛過失致死傷罪的刑罰也最高達到 7年,這就有逾越“刑罰與責任相適應”原則之嫌。以對加害人的處罰來恢復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失,原本就并非如此。毋寧說,處罰加害人并不能救濟被害人,唯有這種認識才是被害人救濟的真正的出發點。
有關一般預防,一方面,對于以物理力的露骨威嚇為內容的消極的一般預防的期待在不斷提高,同時,在另一方面,以國民對法秩序的信賴與滿足為目的的第二種類型的積極的一般預防也在持續抬頭。
2007年提高酒后駕駛罪、醉酒駕駛罪的刑罰,就正是試圖通過刑罰的威嚇力來抑制違法行為;增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汽車駕駛過失致死傷罪,以及對殺人罪更多地適用死刑,以此為代表的量刑上的重刑化,也正是以被害報應思想與威嚇思想為背景。但是,在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最多的 1970年,曾達到 16000余人,而在增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 2001年,死亡人數卻已減少到 8000余人;殺人造成的死亡人數在 20世紀 70年代,曾達到 1200余人,其后持續減少,2007年為 500余人。由此可見,不能認為現在情況特別,尤其需要通過重刑化來強化抑制效果。原本就不能簡單地認為,犯罪的一般預防效果與刑罰的輕重成正比,輕易提高刑罰,反而會鈍化國民對刑罰的感受性,最后只能是不得不再次提高刑罰。實際上,酒后駕駛罪的法定刑歷經數次改正,現在已經是提高到了創設當時的 12倍。而且,重刑化還會進一步刺激包括“封口”在內的隱滅證據、包括“逃逸”在內的逃走等行為③為了避免這種不合理,至少應該在增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的同時,對救護被害人的情形也規定減免刑罰。。實際上,增設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反而起到了促使飲酒肇事案件的駕車人積極逃逸的作用。而且,一旦逃逸,等酒醒之后再來自首,至多只能處以業務上過失致死傷罪 (依據2007年增設汽車駕駛過失致死傷罪之前的法律)與違反救護義務罪的并合罪,其刑罰反而輕于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由此就出現了“逃走合算”這種奇妙的現象①為了消除或者緩和這種“逃走合算”的問題,2007年增設了汽車駕駛過失致死傷罪,并提高了違反救護義務罪的法定刑。但由此也可看到,重刑化所引起的連鎖反應。。
另一方面,2005年的刑法改正將“體感治安”也作為立法理由之一,那正是第二種類型的積極的一般預防的體現。現代社會中,不確定因素很多,人們往往將漠然的不安集中于對犯罪的不安,往往試圖通過重刑化來象征性地消除這種不安,以獲得精神上的安寧。國家方面也能通過回應這種訴求以維持威信,進而獲得國民的支持與服從。對此,我感覺,刑罰正成為國家自導自演、國民自我滿足的手段。
有關特殊預防,以隔離、排除為中心的消極的特別預防被強化,以教育、改善為內容的積極的特別預防正趨于衰退。近期,因為重刑化,刑期一般更長,假釋也難以被許可。可以說,這種拘禁 (關押)的長期化,正反映了國民對隔離保安的期待。對于為不安所糾結,將自己等同于被害人的國民而言,犯人被觀念為與自己屬于不同性質的“敵人”。為此,國民關心的僅僅是犯人是否被排除,而沒有想到犯人如何回歸社會。但是,長期的拘禁 (關押)會使得受刑人難以回歸社會,這反而有礙于防止再犯這一目的的實現。
由此可見,近期的重刑化,通過將犯罪行為人視為“社會的敵人”,否定其與“善良市民”之間的換位可能性,既蘊含有容忍對行為人科處超出屬于刑罰的忍受程度的行為人之“責任”的刑罰的危險,同時,在實際效果上,也不能謂之形成了“最合適的預防”。因此,出于目的合理性的觀點,也難以將其正當化。
二、刑法的基本原則
(一)法益保護主義
1.社會倫理主義與法益保護主義。
上一講已經談到,刑罰以預防犯罪為目的。那么,屬于其預防對象的“犯罪”具有什么樣的性質,刑法通過預防犯罪,又意欲保護什么呢?
20世紀 50年代至 70年代,歐美曾就處罰同性性行為、賣淫、販賣淫穢物品等所謂“無被害人之犯罪”的是與非,一度引發爭議。由于違反了與宗教也聯系在一起的“倫理”,這些行為在傳統上一直被視為犯罪。要求繼續處罰的人們主張,這些行為有損于“社會的共同價值觀”,聽之任之會降低“社會質量”。相反,要求將無被害人之犯罪予以“非犯罪化”的人們則主張,依據“對于成熟的社會成員,能夠違反其意思而對其正當行使實力的唯一目的就在于,防止針對他人的侵害”這一米爾侵害原理,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利益,無論做什么都是個人的自由,國家沒有禁止的資格。這里可以看到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認為刑法的作用在于維持最低限度的“社會倫理主義”,認為刑法的作用在于保護人們的生命、自由、財產等“法益”的“法益保護主義”。
在承認多元價值觀共存的現代國家,不可能確定一種所謂絕對正確的倫理,即便能確定,也不應強加于個人。從根本上說,目的刑論背后的國家觀并非在倫理上處于優越地位的權威,只不過是為了實現人們利益的機構、裝置。基于此國家觀,通過犯罪預防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應該求之于保護現實法益。
“法益”的詞源是德語中的“法律性財貨”(Rechtsgut)。所謂“財貨”,一方面其本身實際存在,同時,因為對人有用而被賦予某種價值。那么,所謂“法益”,就是以具有予以經驗性地把握的可能性的實體(經驗的實在性)、對人的有用性 (與人相關的有用性)為理由,而需要法律保護的對象。刑事立法,只有在有助于保護此意義上的“法益”的限度之內,才能被正當化。相反,判例認為,散布猥褻物罪(刑法第 175條)是保護“健全的性風俗”(最判昭和52年 [1977年]12月 22日刑集 31卷 7號 1176頁)、賭博罪(刑法第 185條以下)是保護“勤勞的美好風俗”(最大判昭和 25年[1950年]11月 22日刑集 4卷 11號 2380頁),但這些不過是“社會倫理”的另一種說法,不能稱之為“法益”。
并且,由于國家的規制手段必須與所要達到的目的成比例 (廣義的比例原理),因此,基于法益保護主義,就出現以下要求:刑罰這一手段有助于實現保護法益這一目的(適合性或者有效性)、其他手段無法實現此目的(必要性或者補充性)、保護該法益所獲得的利益超出包含制約國民自由在內的禁止以及處罰的成本 (相當性或者狹義的比例性)。也有觀點認為,散布猥褻物罪的保護法益在于,“社會·文化環境”、“未成年人的健全培養”、“不想看此內容的人的情感”,然而,姑且不論這些是否具備了能謂之為“法益”的經驗的實在性、與人相關的有用性,但要保護這些,只要對散布的場所、宣傳的方法予以規制、附加年齡確認義務,即已足夠,全面禁止散布等行為,在超出了規制對象的必要且不可或缺的范圍這一點上,也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刑罰是最為嚴厲的制裁,謙抑主義認為,只有在其他手段無法達到保護法益這一目的之時,才可補充性地發動刑罰,這種謙抑主義也是比例原則的一種表現。而且,由于對刑罰正當性的疑慮尚未完全解消、人在非難他人時往往難以“剎車”,因此,要求刑罰具有抑制性態度的謙抑主義就是無比珍貴的警句。
2.父權主義①父權主義(paternalism),也譯為“溫情主義”,是指處于強勢地位者,自認為是為了處于弱勢地位的人的利益,而違反本人意志,介入、干涉其行動。其詞源是拉丁語中的“pater”。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都隨處可見這種情形,尤其是就國家與個人的關系而言,是指以為了保護個人利益為理由,而將國家干涉個人生活,或者對其自由、權利施加限制的行為予以正當化的原理。。
米爾的侵害原理是一種“他害原理”,以防止對他人的侵害作為法規制的目的。然而,在法益保護主義的框架之內,認為刑事規制的目的除了防止侵害他人之外,還包括防止“對自己的侵害”,從而對自損行為以及基于被害人同意的侵害行為也予以處罰,那么,這在何種程度上能被正當化呢?
這種保護本人利益的“父權主義”(paternalism),原則上超出了國家的任務范疇,難以借此將刑事規制予以正當化。通常情況下,什么東西有利于本人,只有本人才能做出最好的判斷。認為與本人相比,國家才是更好的判斷者,這就是一種權威主義。即便本人的判斷是錯誤的,自己的事情自己決定,這本身就存在尊重自律這一價值,從錯誤中學習,這里也存在實現自我的價值。不過,若認為個人是不完全的、是弱勢存在,在下述兩種情形下,就有例外承認基于“父權主義”的刑事規制的余地。
第一種情形是,尚不具備自律做出意思決定的前提條件,不能認為是本人完全任意地處分了法益(弱勢父權主義 =意思補全型父權主義)。例如,與未滿 13歲的少女發生性行為的,即便該少女對此持希望態度,仍構成強奸罪 (刑法第 177條后段)。這無非是為了保護對與性相關的事情并無判斷能力的少女。這種情形下,若直接認定是不符合少女“真實意思”的侵害,根據他害原理或許也能做出說明。另一方面,與未滿 18周歲者發生性關系的,構成各都道府縣的青少年保護條例所規定的淫行罪。然而,例如,在 17歲的女性邀約男性的場合,稱該女性為“受害人”,還是存在抵觸的。很難說已經達到結婚年齡的女性對與性相關的事情沒有判斷能力,而且,同意的性行為究竟侵害了什么法益②即使是父權主義,所保護的利益本身也必須是能夠稱之為“法益”的利益。盡管也有觀點認為,規制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淫穢物品的目的在于,守護本人而使之不致墮落,但試圖保護這種本人的倫理狀況的倫理父權主義(moral paternalism),與法益保護主義互相矛盾。,也并不明確。這里保護的應該是,“不得與年少者保持性關系”這種社會倫理本身,或者,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的“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的愿望。
而且,諸如《出資法》、《勞動基準法》所反映的那樣,因經濟理由而難以自由進行意思決定的場合,以及從《特定商品交易法》中所看到的那樣,因缺少相關知識、信息而無法做出合適判斷的場合,也有肯定意思補全型父權主義的余地。隨著社會的復雜化與高度化,以保護消費者的相關法制為中心,這種父權主義的適用領域也在不斷擴大。但是,過多適用父權主義,也會有向人們灌輸“自己認識”③即便是有關如何確保安全的問題,也可增強對國家的依賴感,在這一點上,這種大眾消費社會中的國民的自己認識,也正成為近期的重刑化與犯罪化的原因之一。之虞:自己屬于缺少自律性的“弱勢消費群體”,處于單方面接受服務的地位。
并且,將對該行為的“特別強烈的誘惑”作為有害于正常的自我決定的原因,也許能使意思補全型父權主義正當化。在將各種藥物犯罪的保護法益視為使用者的生命以及身體、精神的健康的場合,尤其考慮到藥物依存者本人的情況,在獲取、使用之際,其本人無法充分進行自律的意思決定,這也成為父權主義規制的理由之一。就賭博罪而言,雖然可以認為,這種規制是為了保護意志薄弱者而讓其不受賭博的誘惑,將其財產性損失防止于未然,然而,賭博的誘惑與依存性還未達到有損意思決定的任意性的程度,因此,要以意思補全型父權主義來將該罪正當化,就多少有些勉強。
第二種有可能使父權主義正當化的情形是,生命、身體的中樞部分等構成自我決定之基礎的重大法益,因本人的意思決定,以不可能恢復的形式喪失。在此情形下,即便本人意思并無特別瑕疵,仍可違反本人意思來保護本人 (強勢父權主義 =意思否定型父權主義)。處罰同意殺人、參與自殺的刑法第 202條,就屬于其適例。刑法第 202條的旨趣就在于,生命作為自我決定的根基,與自我決定這一利益相比,屬于更高位階的價值,因此,即便有違本人意思,仍須加以保護。相反,試圖以他害原理來說明刑法第 202條的觀點則認為,本條的保護法益在于,因本人的死而損害的家庭以及周邊人的經濟上、精神上的利益。但是,這種法益的內容本身過于不特定,也難以將 6個月以上 7年以下的懲役這種很重的法定刑合理化。另一方面,試圖以意思補全型父權主義來說明刑法第 202條的觀點認為,可以推定,一般情況下,自絕其命這一意思決定,并非是在正常精神狀態下所作出的決定,因此,即便有本人表面上的同意,仍不能由此否定生命的要保護性。按照此觀點,冷靜地深思熟慮之后,決意自殺的,則不構成刑法第 202條之罪。但是,顯然很難將本條理解為,只有在死的決意不是出于任意的場合才可適用。
在規制的收件人(對象)這一點上,父權主義還可分為兩種類型:處罰被保護人本身的“直接的父權主義”、處罰其他參與者的“間接的父權主義”。例如,將藥物犯罪的保護法益理解為使用者的生命、健康的場合,自己使用罪就是直接的父權主義,制造罪、轉讓罪就相當于間接的父權主義。
其中,從外形上看,間接的父權主義止于他害原理的框架之內。尤其是意思補全型的間接的父權主義,實質上也與他害原理處于連續關系。相反,直接的父權主義完全是處罰被害人本身,與刑罰的基本形象大相徑庭。不僅如此,在意思補全型父權主義之下,是被保護人不具備自律的意思決定的前提;在意思否定型父權主義下,是被保護人意欲放棄生命以及大致等同于此的利益,總之,無論是哪種情況,被保護人都處于無法期待刑罰作用的心理狀態下。青少年保護條例以及刑法第 202條都是處罰對法益侵害施加原因的第三者,而不是處罰“被保護人”。對藥物的規制,即便考慮到生命法益的重大性,可作為意思否定型父權主義而被正當化,另外,即便再加上考慮到藥物依存者的關系,以存在難以抵抗的欲求為理由,作為意思補全型父權主義也能被正當化,但作為規制方法,仍應限于處罰轉讓藥物等行為的間接的父權主義,采用處罰自己使用的直接的父權主義,對此還留有疑問①為此,藥物的自己使用罪的處罰根據,也可以認為是,具有因幻覺作用等的影響而侵害他人的危險。然而,僅以這種抽象的危險,能否將與其法定刑相當的刑罰正當化,仍留有疑問。。
(二)行為主義
法益保護主義以防止侵害法益這一刑罰制度的目的,將刑法正當化。這無外乎是來自國家方面的正當化。另一方面,要將針對個人的處罰予以正當化,就必須是該個人現實地以自己的行為引起了法益的侵害或危險。上一講曾談到,刑罰的忍受義務因行為人的“責任”而產生,此責任是針對自己的法益侵害行為而言的,以現實的外部行為為前提。并且,就個人的內心而言,絕對的自由是妥當的,因而不能僅以內心思想或意思作為處罰理由。這種現實的行為以及法益侵害·危險的必要性,可稱之為“行為主義”或者“侵害行為主義”。
原則上,從法益保護主義也可推導出這種行為主義。這是因為,通常情況下,要保護法益,只要禁止現實地引起法益的侵害或危險的行為,即已足夠。可以說,行為主義中的“行為”必須是“帶來法益侵害·危險的行為”,這也是法益保護主義的體現。但是,還不能說,以其危險意思為理由,處罰抱有犯罪意思的人,這完全無助于法益保護。過去的近代學派主張為了“防衛社會”,應以行為人性格的危險性作為處罰理由。這種“行為人主義”雖與行為主義相互對立,但仍可以說,它并不違反法益保護主義。即使在最近,在國外也可看到,由于對恐怖主義的不安情緒日益高漲,將持有某種特定思想者作為恐怖主義的預備軍而予以拘禁的情況。要消除這種處罰思想、處罰意思的情況,就有必要獨立于由刑罰制度的目的所推導出的法益保護主義,而持有由保障個人自由所推導出的行為主義或者侵害行為主義這種觀念。
刑法上的“行為”正是屬于處罰理由的外界變化與屬于處罰對象的行為人之間的接點。為此,一方面,行為主義中的“行為”必須作用于外界。對于在日記中批判天皇者,曾有判例對其處以不敬罪(大判明治 44年[1911年]3月 3日刑錄 17輯 4卷258頁),然而,在個人的日記中寫下某種思想,雖然也可謂動手這一“動作”,但由于其作用尚未及于外界,對此予以處罰就有違行為主義。行為主義并不單純是為了擔保外部的認識可能性或證明可能性,而是一種實質性原理,即必須從行為對外界的作用中尋求處罰的根據。前述近代學派的社會防衛論,雖然也以征表其反社會的性格的行為為必要,但處罰理由不在于行為的作用,而在于由行為所推知的性格,因而違反了行為主義。信奉迷信者為了殺死某人,將釘子釘入稻草人中,若以殺人罪未遂來處罰此行為,也違反了行為主義。另一方面,行為主義中的行為作為處罰行為人的根據,就必須以行為人的主體性參與為內容。為此,至少必須是基于行為人的意思,而有可能避免的動作或者不動作。由此可見,睡夢中的動作、反射運動均不能稱之為“行為”。
(三)處罰的早期化與法益概念的稀薄化
在被稱為“危險社會”的現在,例如,對持有、保管可能用于犯罪的工具、情報的行為也予以處罰,追求處罰的早期化的立法引人注目。例如,2001年的刑法改正規定,不僅處罰偽造的信用卡的持有行為(刑法第 163條之 3),連提供、取得、保管用于偽造的磁卡信息的行為(刑法第 163條之 4第 1款、第 2款),以及此提供、取得行為的未遂 (刑法第 163條之 5),也應予以處罰。又如,2003年的《有關禁止持有特殊開鎖工具等的法律》將偷偷攜帶螺絲刀等入室工具的行為也視為犯罪。誠然,在出于保護財產等法益的目的,僅處罰這些顯現在外的行為的限度之內,可以說,仍止于法益保護主義與行為主義的框架之內。但是,考慮到預備的處罰一直限于殺人、強盜等特別重大的犯罪,以及對持有行為的處罰原則上一直限于槍炮刀劍之類的工具、依存性藥物,作為實現保護財產這一目的的手段,這種早期的刑事介入是否真有必要且真正適當,就仍有探討的余地。而且,一度曾有人提議,通過改正《有組織犯罪處罰法》,增設共謀罪,在達成犯罪合議的階段即予處罰。如果這是僅以內心意思的一致即肯定成立犯罪,顯然違背了行為主義。基于行為主義的要求,至少必須是,各謀議人通過實施合意形成行為,實際創造出了侵害法益的危險。在其意圖與效果上,共謀罪究竟是處罰行為的危險性,還是處罰行為人的思想或者意思的危險性,仍有必要謹慎辨別。
近期的犯罪化,也招致了保護法益的稀薄化。例如,2000年的《有組織犯罪處罰法》與《騷擾①這里主要指因對特定的人的戀愛情感或其他親愛情感未得到滿足,出于泄憤的目的,而對該特定的人及其家屬等實施糾纏、監視、要求見面、要求交往、打無聲電話、闖入住宅等行為。——譯者注規制法》以“國民生活的平穩”、“國民生活的安全與平穩”為立法理由②2000年的《不正連接禁止法》將通過不正輸入他人的密碼而開啟其計算機的行為、提供他人的密碼的行為作為犯罪處理。這如果是以計算機的信息本身作為保護法益,就意味著早期處罰;若是以對網絡的信賴作為保護法益,則意味著法益內容的稀薄化。。與其說這些立法是要保護國民的實際的具體的利益,毋寧說,是為了回應國民“體感治安”的降低,試圖保護其“安心感”,作為象征立法的色彩要更濃一些。但是,“安心感”這種社會心理,更多是受媒體以及時代風潮影響的一種不安定的感覺,未必是基于合理的根據。在國民的不安缺少客觀事實佐證的場合,能解消這種不安的并不是刑事立法,毋寧說是對客觀事實的正確報道。時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了回應國民呼聲的象征立法不但沒有解消國民的不安,有時甚至反而起到了加深這種不安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國民的不安反映了客觀事實的場合,就應該認為,作為不安的對象的生命、身體、財產等具體利益本身才是保護法益。如果這些利益得到了保護,其結果就是,會給國民帶來安心感③如同事先考慮到奧姆真理教的《無差別殺人團體規制法》(1999年)那樣,為了解消國民的不安而進行的立法,就容易成為以特定的集團或個人為對象的“瞄準射擊的立法”。而且,正如曾有判例限于對某些特定的人進入公寓公共部位的行為判定成立侵入住宅罪(參見最判平成 20年[2008年]4月 11日刑集 62卷 5號 1217頁)那樣,在法律的實際適用上,“瞄準射擊”的傾向也很明顯。這種因人而異的選擇性處罰,因處罰的早期化以及法益的抽象化所引起的處罰規定的不明確化,而得到進一步促進。但是,以特定的人為對象的立法與法律適用,在較“行為”的危險性更重視“人物”的危險這一點上,有違反行為主義之嫌。。
另外,1997年的《器官移植法》將買賣器官的行為作為犯罪處理,2001年的《克隆規制法》處罰克隆人的胚胎移植行為。這些法律的保護法益,被認為是“人的尊嚴”、“公眾情感”,但屬于一種社會心理的“情感”本身不應該是法益,要肯定存在“經驗的實在性”,可以說,“尊嚴”還過于抽象。當然不應該直接否定這些規制,但在嘗試保護法益的更加具體化的同時,還要求將由指針等所作的規制也納入視野,并研討刑事規制的有效性、必要性、相當性。
(四)責任主義
要將刑罰正當化,僅憑行為人實施了侵害行為這一點還不夠,還要求行為人對該行為負有責任。行為人若無責任則不能受處罰 (無責則無刑)這一原則,就是責任主義。具體而言,沒有故意或者過失的行為(刑法第 38條第 1款)、不具有責任能力的行為(第 39條第 1款、第 41條)不受處罰 (排除結果責任);不得以隸屬于一定團體為理由,而就他人的行為被追究連帶責任 (排除團體責任)。不過,追究團體責任,這在不以自己的行為作為處罰理由這一意義上,也有違行為主義。
責任主義中的“責任”的內容,多被認為是非難可能性。但是,作為心理事實的“非難”,屬于非難方單方面的情感,并不能成為處罰的“剎車”。即便知道加害人屬于心神喪失者,也無法改變來自被害人與社會輿論的“非難”。相反,屬于責任內容的“非難可能性”,毋寧說,是指存在這樣的理由:從被非難方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既然作了這樣的事情)受到非難,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是因為,刑罰,必須是受刑人也信服的刑罰。另一方面,人們即便能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也會成為被害人,但往往很難想象自己也會成為加害人。因此,可以說,責任主義是通過站在行為人的立場,堅持必須存在能讓行為人甘愿忍受處罰的理由,借此力圖實現立場的互換性(換位思考)。
一直以來,責任主義的根據被認為是,緣自認為刑罰的意義在于對行為人責任的清算的責任報應思想。基于此立場,若行為人有責任,就應受處罰 (積極的責任主義),但是,對此應該理解為,行為人的責任即便是處罰的必要條件,也并非充分條件 (消極的責任主義)。
另一方面,主張從預防目的中推導出責任主義的觀點正成為有力學說。在改善刑論看來,沒有故意或者過失者,由于并不具有反社會的性格,并無改善的必要性;沒有責任能力者,由于不能理解刑罰的含義,對其不能期待刑罰的改善效果。在抑制刑論看來,不具有責任者,由于不處于因刑罰的預告而有可能放棄犯罪的心理狀態,無法期待刑罰的抑制效果。在積極的一般預防論看來,缺少責任者所實施的違法行為,原本就沒有因規范而產生相應動機的可能性,即便不處罰其行為,也不會有損國民對法秩序的信賴。的確,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對于預防的有效性與必要性,也屬于重要要素,在責任主義中,也存在能由預防目的來加以說明的一面。但是,不問有無責任一律加以處罰,更能加深人們對刑罰預告的印象,同時,也能堵住那種偽裝成無責任能力人而免罪的可能性,因而也并非沒有增大預防效果的一面。因此,僅僅以預防效果作為責任主義的根據,對此還有疑問。
相反,另有觀點主張,責任主義的基礎在于保障國民自由。也就是,若認可無責任之處罰,人們就會總是處于處罰的恐怖之中,也會導致其行動的萎縮,因此,責任主義就是,通過只處罰基于故意或者過失的行為,以保障對自己行為歸結的預測可能性。誠然,責任主義與罪刑法定主義一起,通過擔保處罰的預測可能性,發揮著自由保障機能,但是,將行為人的“責任”的意義完全還原于“對于自己受處罰的預測可能性”,對此不無抵觸。
對此,就可認為,責任主義的基礎在于,將行為人的刑罰忍受義務予以正當化。刑罰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預防犯罪來保護法益。但是,為了實現這種公益目的,刑罰對象人就被迫無償地做出某種特別的犧牲。行為人之所以必須甘愿忍受這種特別的犧牲,無非是因為他基于自己的責任,實施了侵害法益的行為。在這種場合下,比照位于法之基本的“相互性”,就只得甘愿忍受特別負擔。相反,在行為人并無“責任”的情況下,即便對其的處罰符合預防目的,也不得讓其忍受刑罰。為了整體的利益,迫使行為人做出沒有忍受理由的犧牲,這屬于全體主義的構想,應該說,這并不符合尊重個人原則(憲法第 13條)。
由此可見,責任主義雖然因預防的有效性、必要性以及保障國民自由等論據而被補強,但其根據最終仍在于,由尊重個人原則所推導出的“特別犧牲的界限”。
(五)罪刑法定主義
1.從人的支配到法的支配。
在古代社會,氏族之間的復仇與氏族之內的懲罰就相當于“刑罰”。它們并非是受近代意義上的“法”的規制而形成,不過是由習慣與宗教圈定了范圍而已。形成統一的政治權力之后,處罰完全交由國王等政治權力者及其官吏們的恣意。即便存在有關處罰規定,那也是為了讓官吏貫徹權力者的意向;而且,不向國民公布這種規定,也是一種慣例。在這種“罪刑擅斷主義”之下,處罰是為了進行差別性處罰與保持權力,因而人們自由安定的生活受到這種處罰的威脅。出于對這種抑制壓迫性刑罰的不滿,在啟蒙時期,要科處刑罰就必須存在事先公布的法律這種認識影響日廣,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等將此旨趣予以明文化。這樣,作為由“人的支配”走向“法的支配”這種觀念在刑法上的具體表現,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即“何種行為屬于犯罪、被科處什么刑罰,必須由行為之前所公布的法律來決定”。其后,盡管一度存在承認基于“健全的國民情感”的處罰的法西斯德國等少數例外,作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主義被多數國家所采納。《日本國憲法》以第 31條、第 39條、第 73條第 6號來保障罪刑法定主義,對罪刑法定主義的違反也屬于《刑事訴訟法》第 405條第 1號所規定的上告①在日本的刑事訴訟法中,上告,是指針對由高等裁判所所作的一審判決或者二審判決,以違憲、憲法解釋錯誤、判決有違最高裁判所的判例等理由,而上訴至最高裁判所,要求改變原判決。——譯者注理由。
2.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
一方面,罪刑法定主義以自由主義為根據。這是因為,若允許可以不依據法律進行處罰,出于對處罰的恐懼,國民的活動自由必然萎縮,因而要求通過事先的法律,讓國民對處罰具有預測可能性。處罰的預測可能性,對實現一般預防目的也很重要。費爾巴哈曾主張,為了通過刑罰預告達到“心理強制”的效果,罪刑法定不可或缺,可以說,那是力圖從刑罰目的論來為罪刑法定主義奠定基礎。而且,罪刑法定主義的自由主義要求,除了保障預測可能性之外,還包含這樣的內容:從國家對刑罰權的不合理、恣意的行使中保護國民的自由與權利。以法律將刑罰的發動要件予以明確化,可以期待能將裁判所與搜查機關的活動限制在一定框架之內,以防止不當地侵犯人權。
另一方面,罪刑法定主義還以民主主義或者國民主權為根據。基于國民主權的理念,剝奪國民權利的刑罰必須是基于國民的意思,屬于國民代表之議會所制定的“法律”的專權事項。尤其是在市民革命時期,可謂之與課稅權并列屬于國家權力之象征的刑罰權,由議會來掌握,這象征著國家主權由君王移轉至國民。
在民主主義的確立過程中,在對抗君主權力這一點上,民主主義的要求與自由主義的要求相互重合。相反,在現代大眾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又往往與自由主義相沖突。尤其是在刑事法領域,多數國民很難想象到自己會處于受處罰者的地位,毋寧說,對多數國民而言,他們的觀念是,實施犯罪者是與自己屬于不同性質的“敵人”,其存在不值得法律保護①裁判員制度的適用案件僅限于特別重大的事件,法務省對其理由作了說明,認為其意義在于,重大案件極大地損害了社會正義,因而可以讓屬于社會主人公的國民恢復正義。然而,這里的“國民”被期待完全站在聲討犯罪的一方。。這樣就將社會成員分為敵我兩方,將刑法觀念為“針對敵人的斗爭”的“敵我刑法觀”,在近期的不安社會,以力圖確定不安對象這種人們的訴求為背景,益發得到強化。對外國人犯罪的社會非難特別強烈,這難道不是試圖排除異質人員這種國民欲求的反映嗎?在此狀況之下,民意不僅向處罰的擴大化與重刑化傾斜,更難以避免處罰的恣意性與不合理性②因此,專家必須向國民展現,根據有關犯罪的正確信息與長年研究積累所獲得的睿智與視角,以此對形成經過深思熟慮的自覺的、有責任的“民意”提供幫助(參見松原芳博:“刑事立法與刑法學”,載《ジユリスト》1369號[2008年],第64頁)。。在大眾民主主義社會,要求順從國民大眾,以可能是恣意的、流動的“輿論”或者“國民情感”進行處罰,盡管主體已由君主轉變為國民大眾,但那仍屬于“人的支配”,而不能謂之“法的支配”。所謂“來自國家的自由”,不限于單純從作為統治機構的政府中保護國民的權利,還必須含有這樣的意義:從完全屬于主權者之集合的國民中,保護作為個人的國民的權利。
3.法律主義。
罪刑法定主義首先要求,根據議會所制定的“法律”來處罰。按照這種“法律主義”,不能根據習慣法、行政府的命令來處罰。不過,根據憲法第 73條第 6號,若有法律的授權,政令中也可設立罰則。在此情形下,授權內容的特定性就成為問題。《國家公務員法》第 102條第 1款、第 110條第 1款授權《人事院規則》來確定,屬于處罰對象的公務員的“政治性活動”的具體內容,對此授權,最高裁判所昭和 49年[1974年]11月 6日大法庭③大法庭是由日本最高裁判所全體 15名裁判官所組成的合議庭。對于違憲立法審查以及其他特定場合,由大法庭審理、裁判。與之相對應的是小法庭。小法庭是首先審理最高裁判所所受理的案件的合議庭,由 5名裁判官組成,最小必須是 3人。日本最高裁判所共有 3個小法庭。有些案件也會被移交大法庭。——譯者注判決 (刑集28卷 9號 393頁)判定合憲。另一方面,《地方自治法》第14條第3款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之外,普通地方公共團體可以在條例中設定科處 2年以下的懲役、禁錮,10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拘留、科料、沒收的規定。對于《地方自治法》的這一規定,最高裁判所昭和 37年[1962年]5月 30日大法庭判決(刑集16卷 5號 577頁)以條例是由公選議員組成的地方議會所作的自治立法、《地方自治法》的授權內容具有相當程度的具體性,且罰則范圍有限為理由,判定合憲。但是,《地方自治法》的授權對處罰對象未作任何限定,難言屬于內容特定的授權。而且,條例雖屬于居民代表進行的自治立法,可謂滿足了民主主義的要求,然而,地方議會屬于一院制,且承認議長具有專斷處分權,并未要求其審理達到國會那樣的慎重程度。如果認為,憲法第 31條所規定的法律主義,不僅要滿足民主主義的要求,即根據憲法第 41條以下所規定的國會組織結構以及立法程序而成立的“法律”應該反映民意,而且要滿足自由主義的要求,即應排除恣意的、不合理的處罰,那么,由地方條例來規定罰則,對其合憲性就不能說沒有值得懷疑的余地①在二戰后的改革時期,對于地方自治,不僅要求其具有民主主義的機能,而且作為對抗中央政府權力的制度,也許還被期待具有自由主義的機能。但是,地方自治體所制定的條例,其制定程序簡單,尤其是未經法制審議會等部門的專家的審查,從刑法的基本原則來看,有疑問的地方不在少數。而且,如同青少年保護條例、煩擾防止條例等那樣,其中很多條例的內容,幾乎關系到所有都道府縣,這樣就存在一個疑問:是否有規避更為慎重嚴謹的法律制定程序之嫌呢?。
4.禁止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
憲法第 39條規定,實施當時合法的行為,不處罰。也就是,對于在行為實施當時,即便在民事法或行政法上屬于違法,但不被科處刑罰的行為,不允許以事后制定的刑罰法規來處罰。而且,刑法第 6條規定,在刑罰發生改變時,適用處罰較輕的刑罰。事前無告知的“突然襲擊”式的處罰,對被告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而且,對一般國民而言,會讓其喪失對處罰的預測可能性,而萎縮其行動自由,因此,這種處罰為憲法所禁止。
這種禁止事后法或者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則,其效力及于有關犯罪的成立范圍與刑罰裁定的所有實體法②責任能力、處罰條件等,并非行為人的故意的認識對象,通常情況下,不屬于行為人在選擇行為之際的考慮情況。為此,就會被認為,溯及適用新設的處罰條件、對責任能力的變更,也不會有害于來自行為人方面的信賴。但是,不論不可罰的根據是什么,不被行為當時的法律所處罰都意味著,國家保障對其不予處罰,因此,以事后立法剝奪這種保障,有違公平觀念。,但是,不及于取證程序等純粹的程序法規定。問題在于,如何處理處于實體法與程序法之中間位置的公訴時效。對此,最高裁判所昭和 42年[1967年]5月 19日決定 (刑集 21卷 4號 494頁)認為,“犯罪后的法律使刑罰有變更時,根據依法律的規定應適用于該犯罪事實的罰條的法定刑來決定公訴時效的期限”,而且,2004年的刑事訴訟法改正對公訴時效的經過期限也作了下述旨趣的規定:在公訴時效的期限被延長的場合,對于延長之前的行為,適用刑事訴訟法改正前的時效期限。之所以認為禁止事后法的原則及于公訴時效,可以說,不僅是基于公訴時效關系到證據的遺散這一程序法上的理由,還基于公訴時效也與一般預防、特殊預防的有效性、必要性有關這種實體法上的理由③而且,要求延長或者廢止公訴時效期限的近期的媒體報道,除了證據的遺散之外,探討的完全是對遺屬情感的撫慰這一點,這無非是與那種認為刑罰目的在于滿足被害人情感、遺屬情感的刑罰目的論相對應。。
另外,對于按照行為當時的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屬于無罪的行為,能否允許通過改變判例來處罰呢?判例、通說認為,禁止事后法的原則不及于判例的不利益改變(最判平成 8年[1996年]11月 18日刑集50卷 10號 745頁)。可以說,該立場是將“法律”主義與禁止事后“法”相互聯動的觀點。也就是,從法律主義要求“法律”明示處罰范圍這一點來看,國民的信賴也理應是指向“法律”,只要該行為處于法律的框架之內,即便與行為當時的判例相反,也完成了“事前的告知”。有相當理由相信,基于行為當時的判例,自己的行為是合法的,對于此類情況,該觀點以由于缺少違法性意識的可能性而可阻卻責任這種方式,來維護對判例的信賴。然而,基于認為違法性意識的對象是“一般的違法性”這種通說的前提,在行為當時的判例是以不具有“可罰的違法性”或者“刑法的違法性”為理由而判定無罪的場合,對于因信賴判例而實施行為的行為人,就無法從違法性的錯誤的角度來予以免責。
有別于此,少數有力說認為,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具有一定的約束力,無論是法律人士還是一般市民,其行為既依照法律,也同時遵循判例,既然如此,禁止事后法的原則對于判例也應是妥當的。在此觀點看來,改變已經確立的最高裁判所判例的,這止于向將來宣告變更旨趣,對當下的被告人仍應宣判無罪。也可通過改變判例,對被告人適用因受最高裁判所的違憲判決而長期處于“死文化”的刑罰法規,考慮到這種做法的不當性,本說具有相當程度的說服力。然而,也留有這樣一些疑問:在并無以判例作為法律淵源這一傳統的我國,如何能劃定“確立的判例”的范圍?作出面向將來的宣言式判決,是否超出了僅解決個案這一司法權限?原本不過是“旁論”的宣言式判決,在多大范圍上具有先例拘束力?因此,至少在不對程序上的相關規定進行整理完善的情況下,還難以實踐“無溯及力的判例變更”。
5.禁止類推。
所謂類推,是指對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用語的事實,以該事實與符合此用語的事實之間具有類似性為理由,而適用該法律規定。刑罰法規的類推,在對于法律并無規定的事項,由裁判所來創造法律這一點上,有違法律主義,同時,在缺少事前告知這一點上,又有違禁止事后法原則。不僅是在判決書中明示地以類推手法推導出結論的情形,即便形式地采取了包攝于法律規定這一形式,但超出法律規定用語的“可能的語義”進行擴大解釋的情形,也有違罪刑法定主義。
自不待言,在解釋刑罰法規之時,不僅認可文理解釋,也認可目的論解釋。立足于法益保護主義的觀點,主要是從法益保護的視點而推導出這種目的論解釋。一方面,從確保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這一點來看,不允許超出一般人可能理解的含義范圍;另一方面,從防止刑罰權的恣意行使這一視點來看,不允許與其他相關規定在法律文脈上缺少整合性,也不允許違反法律條文的書寫規則。在此意義上,存在于一般用語慣例以及法律用語慣例中的“可能的語義”,對目的論解釋形成外在制約。相反,也有觀點主張,應比較衡量罪刑法定主義的要求與處罰的必要性,結合處罰的必要性的大小、與語言的核心含義之間的距離等因素,來推導出解釋的界限[1]。但是,如果是在處罰的必要性很大的場合,可以超越“可能的語義”予以處罰,這無疑是放棄罪刑法定主義的自由保障機能。
關于此問題,有以下疑問判例:1.將電力包含于舊刑法的盜竊罪的“他人的所有物”中(大判明治36年[1903年]5月21日刑集9輯874頁);2.對于把鯉魚從養魚池中放出的行為,判定屬于損壞器物罪中的對物“傷害”行為 (大判明治 44年[1911年] 2月 27日刑錄 17輯 197頁);3.將汽油機車包含于過失導致交通危險罪的“火車”中 (大判昭和 15年[1940年]8月 22日刑集 19卷 540頁);4.出于游樂目的的狩獵也包含于業務上過失致死傷罪的“業務”中(最判昭和 33年[1958年]4月 18日刑集 12卷 6號 1090頁);5.對于向野鴨放箭,但并未射中的情形,判定屬于《鳥獸保護法》中的“捕獲鳥獸”行為(最判平成8年[1996年]2月8日刑集50卷2號221頁);6.將存有淫穢圖像數據的電腦硬盤認定為“淫穢物”,判定使其內容處于不特定多數人可以瀏覽播放的狀態之下的行為屬于“公然陳列”(最決平成 13年[2001年]7月 16日刑集 55卷 5號 317頁);7.認為“公文書”也包括公用文書的圖片復印件(最判昭和 51年[1976年]4月 30日刑集 30卷 3號 453頁)。上述這些判例都是從法益保護的視點作目的論的擴張解釋,其中,1—6有超出一般用語慣例,7有偏離法律含義之嫌。反之,對于認為《國家公務員法》上的“特定的候選人”包含特定的提名候選人的觀點,判例判定這屬于類推擴張解釋,并不妥當(最判昭和 30年[1955年]3月 1日刑集 9卷 3號 381頁),應該說,此判決是從法律用語慣例的角度嚴格把握“候選人”的范圍,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判例 1、3、6、7,是力圖通過對既存法律規定的解釋,來應對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所產生的立法當時所未能預想到的情形。誠然,從民主主義這一方面而言,也許可以認為,對于將來的未知情形,立法者在一定范圍之內授權裁判所可將法律內容具體化;但是,若關注自由主義的方面,則不允許以屬于立法當時未能預測到的情形為理由,而超出“可能的語義”。一直以來,多以我國很難以立法形式來對應新發現象為理由,將判例的這種彈性解釋予以正當化,然而,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躍,甚至被稱為“立法的時代”的當下,似乎不能再搬出這種理由。
6.禁止類推原則的適用范圍。
禁止類推、禁止超出語義的解釋,就不利于行為人的方向而言,其效力不僅及于構成要件要素,其效力還及于,包括有關違法阻卻事由、責任阻卻事由、處罰條件、刑法適用范圍等規定在內的實體法上的所有要件事由。這是因為,若認為法律主義以及禁止事后法是針對實體法上的所有要件的要求,那么,由此推導而來的禁止類推,也理應及于同樣范圍。例如,盡管刑法第 41條規定,“不滿 14歲的人的行為,不處罰”,仍以其精神年齡相當于 14歲以上的人為理由而處罰 13歲的人,這顯然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①②與各論的規定相比,刑法總論的規定抽象程度更高,不少情況下,需要“理論”補充。例如,對于正當防衛,就不允許超出刑法第 36條的可能的語義,作縮小解釋(參見增田豐:《語用論的含義理論與法律解釋方法論》,勁草書房2008年版,第190頁以下)。(語用論[pragmatics]是記號論的一個分支,處理記號或者語言表現與其使用者之間的關系。——譯者注)。對于諸如有關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 (《母體保護法》第 14條)那樣,由刑法典之外的其他法律所規定的違法阻卻事由,該要求的效力仍及于此。
反之,有利于行為人的類推,由于沒有任何地方與罪刑法定主義的自由主義要求相抵觸,就應允許作超出法規用語限制的解釋。例如,將妨害執行公務罪 (刑法第 95條第 1款)的公務限于合法的公務;由“生命、身體、自由”(刑法第 37條)進行類推,而認可為了保護貞操、名譽的緊急避險;基于有關不知法律的任意性減輕規定 (刑法第 38條第 3款但書)的旨趣,對于缺少違法性意識的可能性的情形,也認定阻卻責任,這些都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不過,基于民主主義的要求,無論對行為人有利還是不利,禁止類推原則都同樣是妥當的。但是,在刑事訴訟法上,認可檢察官具有較大范圍的暫緩起訴權限,正如這一點所提示的那樣,可以作如下推測:在做出不處罰決定這一方向上,立法者在某種程度上允許相關司法機關進行彈性應對。不僅如此,對保護法益而言屬于不必要的處罰、違反責任主義的處罰,都有違后述刑罰法規的適正要求,因此,基于刑法基本原則而對處罰范圍加以限定,只要其內容合理,即便有違民主主義的要求,仍然可予以貫徹。然而,正如后述,需要恒常性地限定其處罰范圍的刑罰法規,其本身就屬于內容不明確或者過度寬泛的規定,因而處于違憲的質疑之中。
(六)刑罰法規的適正
1.明確性原則。
什么行為屬于處罰對象,這一點并不明確的法律,并沒有體現“事先告知”。以不明確的法律進行處罰,對行為人而言,屬于缺少“事先告知”的“突然襲擊”。對于一般國民,又會萎縮其行動自由。為此,刑罰法規的規定必須具體、明確,達到一般國民預測可能的程度,反之,若刑罰法規違反了此要求,也就違反了憲法第 31條①對刑罰的種類與具體輕重不作規定的“絕對的不定期刑”,沒有明確顯示刑罰的范圍,也有違明確性原則。。這種明確性原則,不是關注法律的內容,而是以使法律的事先告知具有實效性為目的,在這一點上,與罪行法定原則具有連續性。另一方面,包括禁止類推在內的罪刑法定主義,是對司法機關的要求,而明確性原則在第一順位上是對立法機關的要求。不限于此,不明確的刑罰法規,有將本不應屬于刑罰對象的行為也納入處罰范圍的可能性,因此,尤其是在與合憲限定解釋的關系問題上,與該法律的規制內容是否適當,并非沒有關系。由此可見,明確性、內容的適正都屬于“刑罰法規的適正”的內容。
最高裁判所昭和50年[1975年]9月10日判決(刑集 29卷 8號 489頁)是本原則的范例。該判例認為,明確性的標準在于,“按照具有通常判斷能力的一般人的理解,在具體情形下,對于某行為是否適用該規定,能否從中找到標準以對此作出判斷”,在此基礎上,判例判定,對于《德島市公安條例》中的“維持交通秩序”這一規定,“可以理解為,是命令應該避免造成,超出一般情況下,有秩序地、平穩地在道路上進行集團游行時,會隨之產生的對交通秩序的妨害程度的,對交通秩序更嚴重的妨害”,因此,作為構成要件并不缺少明確性。最近,最高裁判所平成 20年(2008年)11月10日決定(刑集 62卷 10號 2853頁)認為,北海道煩擾防止條例(《北海道有關防止顯著煩擾公眾的暴力的不良行為等的條例》[1960年])第 2條之 2第 1款第 4號中的“卑猥的言行”,“可理解為在社會一般觀念上,有違性道德觀念的下流、淫亂的言語或者動作,結合該條第 1款正文‘(任何人不得)對處于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沒有正當理由,卻實施 (下述)明顯讓其感覺羞恥或者不安的 (行為)’,要將其作為日常用語,對其做出合理解釋,這是有可能的”,因此不能謂之不明確,進而判定下述行為屬于“卑猥的言行”:在女性背后,用帶有數碼相機功能的手機,在長達 5分鐘的時間內 11次拍攝了該身材苗條的女性的臀部。對此,判決書中也附有主張本案行為不屬于“卑猥的言行”的反對意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疑問:僅拍攝一次或者僅直勾勾地盯著對方,這種行為是否屬于“卑猥的言行”?若認為此類行為不屬于“卑猥的言行”,這些行為與本案之間是否存在必然差別?因此,對于諸如本案行為的行為類型,“卑猥的言行”這一用語是否能實現“事前告知”,對此仍有提出異議的余地②另外,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2008年]7月 17日(判決書未刊登在公開的判例集上)認為,世田谷區清掃·廢物利用條例中所謂“一般廢棄物處理計劃所決定的指定場所”,作為構成要件并非不明確,而且,將技術性細節授權給該計劃也是被允許的,從而對違反區長的命令,從指定場所回收舊報紙的廢舊品業者,維持了有罪判決。。
2.體感治安的降低與不明確的刑罰法規。
近期,在以體感治安的降低為背景的刑事立法中,隨著保護法益概念的稀薄化與處罰的早期化,新創設了一些在明確性上尚存疑義的處罰規定。例如,以殺害女童事件為契機而制定的奈良縣《保護兒童免受犯罪被害的條例》(2006年)第 12條、第15條規定,對兒童實施“找茬恐嚇”、“阻擋去路,或者糾纏”行為的,構成犯罪。尤其是其中的“找茬”、“擋路”的范圍并不明確,而且,一方面鼓勵鄰居規誡兒童,可不認識的人斥責規誡兒童,卻難免不被作為“找茬”而受到處罰。
而且,根據《大阪府建立安全城區條例》(2002年)第 19條第 1款、第 24條第 1款的規定,除在社會一般觀念上具有正當理由的場合之外,在道路、公園等場所,攜帶棒球棒、高爾夫球桿的行為被認定為犯罪。但是,攜帶棒球棒、高爾夫球桿,這屬于日常行為,是否構成本罪完全取決于在社會一般觀念上是否具有正當理由,其界限極不明確。為此,該條例第 19條第 2款又規定:“對于攜帶棒球棒、高爾夫球桿者,警察在判斷是否存在違反前款規定的事實時,必須特別慎重。”第 19條第 2款的規定是一方面自己承認,第 19條第 1款的構成要件不明確或者過度寬泛,但同時又并非根據法律,而是根據警察的判斷來劃定處罰界限,應該說,這與“由人的支配走向法的支配”這一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在處罰范圍的明確性與體感治安的關系問題上,前不久的最高裁判所平成 21年[2009年]3月26日判決 (判決書未刊登在公開的判例集上)就是一個饒有興致的判例。被告人在夜間騎車健身時,將防身用的噴霧器放在胸前口袋里,對此,被起訴違反《輕犯罪法》第 1條第 2號①《輕犯罪法》第 1條第 2號:“沒有正當理由,偷偷攜帶刀具、鐵棒等其他有害于他人生命,或者會被用于嚴重加害他人身體的器具的”,處拘留或者科料。——譯者注,即“偷偷攜帶會被用于嚴重加害他人身體的器具”,一審、二審均判定有罪。相反,最高裁判所認為,“綜合考量該器具的用途·形狀·性能、與隱匿攜帶者的職業·日常生活的關系、隱匿攜帶的時間·地點·樣態以及周邊狀況等客觀要素,以及隱匿攜帶的動機、目的、認識等主觀要素”,攜帶該器具在社會一般觀念上具有相當性的場合,就屬于該號的“正當理由”,進而認定被告人具有“正當理由”,宣判無罪。所謂社會一般觀念上的相當性,是對包括主觀因素在內的各種各樣的要素進行綜合性判斷,這里就正是以此來劃定處罰界限,然而,正如一審、二審與最高裁判所的結論并不相同這一點所反映的那樣,其界限極具流動性。為此,甲斐中裁判官在對該最高裁判所判決所作的補充意見中,一邊確認被告人并無前科、前歷,迄今為止的生活均與犯罪無緣,同時又指出,“也鑒于被認為體感治安惡化的社會狀況”,可認定被告人具有“正當理由”。那么,從其文脈來看,對于有前科、前歷等的可疑人物,“體感治安的惡化”是否又會反向作用,肯定隱匿攜帶噴霧器的行為的犯罪性?由此可以看到,體感治安的惡化與“敵我刑法觀”之間的密切聯系。
3.刑罰法規內容的適正。
基于罪刑法定主義的自由主義要求,規定處罰罰則的“法律”,必須是滿足憲法要求的適正的“法律”。主張只要是國民代表制定的“法律”,就可不問其內容,這依然是一種緣自“人的支配”的構想,而不能稱之為“法的支配”。首先,根據有違保障表現自由的憲法第 21條等個別人權條款的刑罰法規來處罰,這不能被認可。而且,可以認為,法益保護主義、責任主義等這些刑法基本原則,其核心部分也融入了憲法第 31條,因此,處罰完全無害的行為的法律、處罰無故意無過失的行為的法律就有可能違憲。最高裁判所昭和35年[1960年]1月27日大法庭判決(刑集 14卷 1號 33頁)認為,《按摩師、針灸師以及柔道康復師法》第 12條、第 14條所禁止、處罰的醫療類似行為,必須是“有危害他人健康之虞的業務行為”,也就是,若某行為從法益保護主義的視點來看屬于無害的行為,就不能把該行為作為處罰對象。而且,比例原則以對法益保護的適合性、必要性、相當性 (狹義的比例性)為其內容,這也是來自憲法的要求,因此,規定了與犯罪的輕重完全有失均衡的刑罰的、違反了比例原則的處罰規定,也有違刑罰法規的適正原則。
4.合憲限定解釋。
正如上述有關醫療類似行為的判例、有關《德島市公安條例》的判例那樣,對于那些不明確的刑罰法規或者內容不適正的刑罰法規,會常常進行合憲限定解釋。但是,尤其是通過合憲限定解釋,以維持不明確或者過度寬泛的刑罰法規的效力,進而判定被告人有罪的,從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來看,這種情況并非沒有問題。
首先,不明確或者過度寬泛的法律未能實現適當的“事先告知”,反而是只有通過針對該被告人的裁判結果,其處罰范圍才能被確定,因此,對該被告人而言,這無疑屬于“突然襲擊”,有違禁止事后法原則。而且,不明確或者過度寬泛的刑罰法規,這之后還要繼續存續下去,因而其針對一般國民的行為萎縮效果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從認為禁止事后法的效力不及于判例變更的通說觀點來看,“法律”才是國民的行動指南發揮作用的基石,不僅如此,在對判決作出合憲限定解釋之后,實際上仍存在因判例變更而推翻此限定限制的危險,因此,凡是有可能被包括在不明確的法律之中的行為,國民都不得不控制實行避而遠之。相反,在認為禁止事后法的效力及于判例的少數說看來,由合憲限定解釋所表示的法命題正是國民的行動指針,因此,對保障國民自由而言,這種合憲限定解釋的結果的明確性尤為重要。然而,在通說觀點看來,這種作為解釋結果的法命題,是因為解釋之前的刑罰法規不足以作為行為指南,而加以補充,在能期待其作為事實上的行動指南發揮作用的限度之內,也要求其具有明確性。
另一方面,裁判所以合憲限定解釋這一形式,確立了超出個別具體案件的一般性、抽象性規范,這屬于裁判所在“改寫法律”,因而存在疑問:這種做法難道沒有侵害立法權嗎?尤其是,在認為禁止事后法的效力及于判例的少數說看來,——盡管是該說所事先預定的——,在作為合憲限定解釋之結論的一般性、抽象性命題具有法律約束力這一點上,更大程度上觸犯了三權分立原則。
因此,合憲限定解釋,一方面,應限于立足于防止對被告人進行“突然襲擊”、法律的告知機能、三權分立等視點,可毫無障礙地從該法律的用語及其旨趣中推導出來的場合;另一方面,立足于合憲限定解釋本身也具有告知機能這一視點,還要求作為該解釋之結果的法命題,其范圍止于能夠進行合憲規制的限度,而且必須明確。在無法滿足此要求的場合,法令本身就應視為違憲、無效。
對于《福岡縣青少年保護培育條例》第 10條第1款中的“淫亂行為”,最高裁判所昭和 60年[1985年]10月 23日大法庭判決(刑集 39卷 6號 413頁)作了下述限定解釋。最高裁判所認為,若認為其是指針對青少年的一般性行為,就會將真正處于戀愛關系者也包括在內,其處罰范圍無疑過寬,而若將其單純理解為反倫理或者不純的性行為,作為構成要件,又不具有明確性,因此,所謂“淫亂行為”,是指“通過采取誘惑、威迫、欺騙青少年或者使之困惑等趁其身心發育的不成熟,而采取不正當手段實施性交或者類似性交的行為,除此之外,還包括只能是認定,純粹是將青少年作為滿足自己性欲的對象的性交或者類似性交的行為”。但是,在本案中,第一,要從“淫亂行為”這一用語中推導出最高裁判所的解釋,非常困難;不僅如此,第二,解釋結果的后半部分仍然不明確,并且,對于這種具有濃厚倫理色彩的可罰性標準本身的合理性,也存有疑問。
另外,《廣島市暴走族驅除條例》(第 16條第 1款第 1號、第 17條、第 19條)規定,“任何人”未經管理者的許可,不得在公共場所實施使公眾產生不安或者恐懼的集合、集會或者示威等行為,對于違反以此禁止性規定為前提而發出的終止、離開的命令的,由該條例予以處罰。對此,最高裁判所平成 19年[2007年]9月 18日判決 (刑集 61卷 6號 601頁)一方面認為,從本條例的用語本身來看,禁止的對象以及終止、離開命令的對象,也包括社會一般觀念上屬于暴走族以外的其他人的行為,若直接適用此用語,其規制對象就會不當地涉及更大范圍的人,但判例同時又指出,若將其適用對象限定于“服裝、旗幟、言行等類似于此類暴走族,在社會一般觀念上,可以等視于此的集團”,就與憲法第 21條第 1款、第 31條不發生抵觸。本判決的特點在于,第一,重視條例的“旨趣”,并由此作出與其“用語”明顯相反的限定解釋;除此之外,第二,限定解釋的內容不是依據“行為”,而是依據“人”來選定。但是,這種依據“人”來選定的做法,具有明顯的敵我刑法觀的傾向,而且,在與行為主義以及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則(也就是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憲法第14條)的關系問題上,也仍留有疑問。
[1]松原芳博.國民意識產生的犯罪與刑罰[J].世界,第 761號(2007年),53以下.
[2]前田雅英.罪刑法定主義的變化與實質的構成要件解釋[A].中山研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 3卷·刑法的理論)[C].成文堂,1997.68.
責任編輯:王 瑞
Editor’s note:ProfessorMatsbara Yoshihiro ofWaseda University began to monthly serialize Special Research on Generality of Cr iminalLaw(it keeps on so far)from last April,explained theoretically and reasonabl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n important questions of Generality of Criminal Law of Japanese,which is different from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of conventional textbook.Its characteristics are:the first,attaching importance on systemsof crime theory,emphasizing that the systems of crime theory should actually become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compass to related problems;the second,attempting to infiltrate doctrin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 ime,doctrine ofprofitsprotecting and doctrine of responsibility into the criminal theory;the third,based on Theory ofViolatingLegal Interests(the theory of the valueless result),maintaining that carrying out doctrine of profits protecting and mechanism of liberty protection;the forth,taking the function of cr iminal law in modern society as the basin point,focusing on present tendency of current Japanese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criminal judicial.In the hornorofNippon-Hyroh-Sha.Co.,Ltd and ProfessorMatsbara Yoshihiro freel assignment of copy right,the book was translated by assistant professorWang Zhaowu and presented to the reader.This latest researching fruitwas completed by noted foreign and domestic scholars in orde to benefit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our criminal law.
criminal penalty;generality of criminal penalty;meaning of criminal penalty;doctrine of criminal law
D924
A
1008-6951(2010)03-0057-16
2010-02-22
松原芳博(1960— ),男,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務研究科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刑法學。
譯者簡介:王昭武(1968— ),男,湖北監利人,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日本同志社大學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