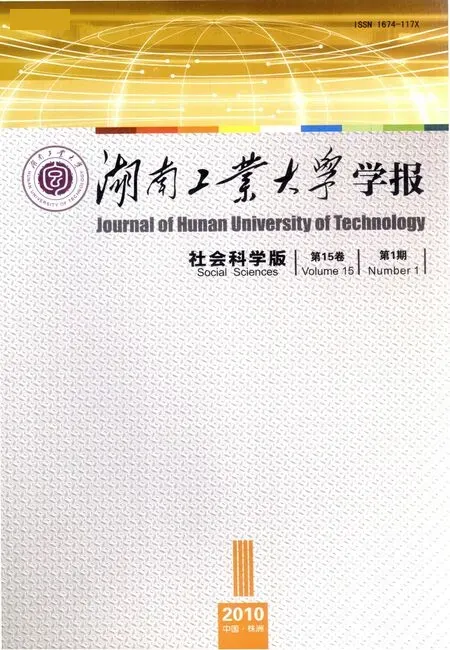從《〈希望〉編后記》看胡風編輯刊物的傾向
趙雙花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上海200241)
從《〈希望〉編后記》看胡風編輯刊物的傾向
趙雙花①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上海200241)
從《〈希望〉編后記》看胡風編輯刊物的傾向是:嚴肅的文學觀,繼承與發展魯迅精神以及主觀戰斗的現實主義。胡風所編《希望》比《七月》更進一步地實踐了自己的文藝理想和編輯理念,而每期的“編后記”則鮮明地揭示了這種傾向。
《希望》;胡風;魯迅精神
文學史上的“七月派”是以胡風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創刊的《七月》而得名。《七月》之所以在連綿的炮火中,在四處流落中不致湮沒無跡,能夠死中復生,是在“許多作家的協力和讀者的參加下而產生,成長的”,而這恰恰又證明了七月社編輯部“對于文藝界統一戰線結合點的存在的尊重,對于各派作家的創作方面的重視,對于作為友軍的許多文藝堡壘的尊敬,而且表示了我們對于文藝將在民族戰爭里而得到萬花燦爛的發展的預想”。[1]從這方面看,《七月》明顯的是為抗戰服務,為團結更多的進步作家服務的。當然,《七月》不僅僅滿足于這些,在胡風的理解里,文藝界的統一戰線不僅意味著政治傾向的一致,同時還是創作方法上的趨近。后因《七月》被查封,刊物改名為《希望》。《希望》從1945年1月到1946年10月共出版了2集,每集4期。在每一集的第一頁目錄的下方,都有一個“致讀者”的說明,其中一點是:“愿意廣收同好者的來稿,凡文藝創作與文化批評不論哪一類(暫不收純學術性的文章)也不論長短,由幾百字到兩三萬字,除了我們認為不好,或者實際是好的但我們不能理解的以外,都愿發表。”[2]那么,胡風們對所認為的“好”是怎樣的評判標準?也就是說他們的傾向性表現在什么地方?而且他們對保持這些傾向所做出的努力在文學史上又有什么作用呢?我們不妨結合《希望》的“編后記”來思考一下。每期必有的《編后記》可以說是刊物的眼睛,最直接地體現了胡風的編輯審美標準、用稿原則,最直接地的向讀者呈現了刊物的質量。我們可以從以下三點來分析:
首先,胡風在編輯《希望》時不斷申明文學的嚴肅性。在每一期的“編后記”里,胡風都會鄭重其事地簡要分析他所選文章的理由,而每一條理由都與文藝界發展的不良傾向有關,與努力把握整個民族的文藝走向有關,顯示出他作為一個文學編輯與文藝理論工作者的態度、眼光。他在第1集第4期“編后記”明確申明文藝的戰斗性,反對以游戲的態度進行文學創作,這對當時沉浸在勝利氛圍中的人們是一個必要的告誡。
這種嚴肅文學觀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重視文學的批判功能。批判,在胡風看來,實是文藝創作的應有之義。細讀《希望》每一期的雜文專欄,這些雜文從歷史、政治、文化等角度入手,直擊現實社會的各樣弊病,顯示出追求社會正義的勇氣與力量。如何取得斗爭的全面勝利,在胡風看來,人格的健全,精神的勝利是更為重要的事情,批判的鋒芒更是對準民族痼疾。在第一集第一期“編后記”中,胡風在評價路翎中篇小說《羅大斗的一生》時說到:“《羅大斗的一生》就是色彩濃郁的油畫的大幅。在這大幅上面,有色底滲透和線的糾結,人民的苦惱,負擔,和希求,在活的生命形象上使紙面化成了一個世界。在作品里看不到‘結論’就驚慌失措的批評家們也許要用顯微鏡來尋找‘主題’罷,但我不妨冒昧地說一句:我們所要求的人民的英雄主義是能夠從這里呼之即出的。而且還不妨再加一句:在文藝思想上,無論對于客觀主義或教條主義,這都能成為有效的一擊。”[3]其中所說的“人民的苦惱,負擔”不正是千百年來農民所受的精神奴役創傷的體現么?而這又無不是承續了五四時期魯迅開創的“改造國民劣根性”的主題。
在提到舒蕪的《論主觀》時,胡風說:“但《論主觀》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會受到影響的問題。這問題所涉甚廣,當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盡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讀者也不要輕易放過,要無情地參加討論。”[3]對于文藝批評,他的態度是:“只有通過批評,才有可能追索到生活世界和藝術世界的聯系,只有通過批評,才有可能揭開而且解剖一切病態傾向的真相保衛而且培養一切健康力量的生機。但批評要實現這樣的任務,就非處在能夠個人直說真話的民主政治的條件下面不可,因為批評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民主性的行為。只有在民主政治下面的民主的批評,才能夠反映時代,教育讀者,把創作實踐以及批評實踐本身推進真理的門。”[4]胡風是真誠地想得到批評的,也是真誠地想通過批評來追尋真理,促使文藝走向健康之路的。單單從隨后幾期陸續刊出的舒蕪的《論中庸》(1集2期)、《思想建設與思想斗爭的途徑》(1集3期)、《個人、歷史與人民》(2集1期)等進一步闡釋《論主觀》的文章就可以看出。
其次,是對魯迅精神的繼承與發展。胡風是很看重精神榜樣的力量的:“精神巨人所給予我們的力量,猶如他在他的那個時代苦斗了過來一樣,是要我們在我們的這個時代也堅強地苦斗下去的罷。”[5]雖然他不是每篇《編后記》都提及魯迅,但他從魯迅的眼光來看待文學則是毫無疑問的。在第二集第四期的《編后記》中,胡風似乎顯得特別的疲乏與無奈,由于出版公司的經營出了問題,刊物不得不脫期,而且能否繼續,心中還沒有底。但是這個月恰逢魯迅逝世10周年,胡風還是打起精神將這期幾乎做成了紀念魯迅的專刊。封底是胡風作詞的歌曲“魯迅先生頌歌”《由于你,新中國在成長》,封面內里引了魯迅先生的三條語錄,283頁的填白處也引用了魯迅的話。除此之外,刊登了魯迅寫給胡風的六封信,發表了胡風自己1937年10月寫過的專論魯迅精神的《關于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指出魯迅不是新思想的介紹者或解說者,卻是運用新思想同舊勢力做徹底斗爭的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斗士。魯迅戰斗的一個偉大特點是“把‘心’、‘力’完全結合在一起”。至于魯迅精神的現實意義,胡風在文尾指出:“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期的今天,魯迅的信念是明白地證實了:他所攻擊的黑暗與愚昧是怎樣浪費了民族力量,怎樣地阻礙了抗戰怒潮的更廣大的發展。為了勝利,我們有努力地向他學習的必要。”[6]同時,還發表了舒蕪的《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這篇長文以雄辯的氣勢論證了目前的中國還是魯迅當時所面對的中國——“在這個國家里,‘舊社會的根底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么……’”,“在這個國家里,充滿了‘做戲的虛無黨’……”。[7]我們所要走的道路還是魯迅所選擇的道路——“不斷鏟除著這樣的‘光明’,顯現出‘黑暗與虛無’之為‘實有’的道路”。[7]我認為這篇文章是對8期《希望》中的文學創作在追求、體現魯迅精神時的一個最好的注腳。
其它很多創作也是接著魯迅所開創的話題繼續說的。試揀舉兩例:耿庸《說到“民主”》歷數了野史記載的豪紳為競為賭而吃人的令人發指的行為,不僅指出這是魯迅“吃人歷史”觀的具體例證,而且指出“吃人歷史”的有可能再續,且是以“民主”的名義。署名“一筒”的雜文《關于“發抖”》,借史指出發抖實是奴隸心理病態的體現,而這又體現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中,哪怕是揭竿而起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陳勝吳廣也不過是農奴。奴隸實是我們民族的最基層,是支撐金字塔的龐大底座,這與魯迅提出的民族劣根性不是一致的嗎?
最后,與以上兩點緊密聯系的是胡風旗幟鮮明地提倡主觀戰斗的現實主義精神。在第二集第一期的“編后記”中,胡風重申了在抗戰結束后,關于抗戰主題的寫作必要性。對于表現抗戰時期的人民的生活變革與精神狀態的作品,胡風說“歷史總是由過去走向將來,更何況抗戰時期的社會性格現在還并沒有成為過去?”[8]所刊登的三個詩集正是表現了戰斗的理想與戰斗的情緒。在第二集第二期的“編后記”中,胡風指出“在現在的中國,一切都現出激烈的變動,一切都現出鮮明的對照。”[5]他還指出:“知識分子,無論他從現實人生中取得什么,怎樣取得,向現實戰斗給予什么,怎樣給予,總是要通過他的思想武裝,也就是精神發展的過程的。”[6]
胡風強調知識分子的精神改造,但這種改造與解放區《講話》中提到的“改造”卻有著不同的意義。這“改造”意思也是他發表在《希望》第一集第一期首篇位置的《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中所提到的“自我斗爭”。在這篇文章里,胡風以一種流暢、富含激情的雄辯氣勢論證了要取得民主的徹底勝利,在文藝領域里就必須堅持現實主義。這種現實主義從感性的對象來看,是血肉的現實人生,它“是思想內容的最尖銳的最活潑的表現。”[3]他認為“只有從對于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斗開始,在文藝創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創作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堅固。”[3]如何體現這種現實人生呢?“在對象的具體的活的感性表現里面把握它的社會意義,在對象的具體的活的感性表現里面溶注著作家的同感的肯定精神或反感的肯定精神。”[3]這對創作主體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不僅要發揮主觀能動作用,而且“主觀力量”要“堅強”,“堅強到能夠和血肉的對象搏斗,能夠對血肉的對象進行批判,由此,創造出包含有比個別對象更高的真實性的藝術世界。”[3]同時,作家要向“感性的對象深入,深入到和對象的感性表現結為一體。”[3]對于作家來講,這種批判、表現的過程也意味著“自我斗爭”,因為既然對象是充滿感性的,那作家的思維活動就不能逾越感性的機能;同時現實生活是紊亂、繁雜的,人們身上沉淀著幾千年累積而成的“精神奴役創傷”,如何不被它所淹沒、所同化而保持著批判的銳度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除了站在“和人民共命運的實踐立場”外,還應具備“堅強的生活意志”,即人格力量。胡風認為,只有“通過了這樣的自我斗爭,一方面,對象才能夠在血肉的感性里面涌進作家的藝術世界,把市儈的‘抒情主義’或‘公式主義’驅逐出境;另一方面,作家的思想要求才能和對象的感性表現結為一體,使市儈的‘現實主義’或‘客觀主義’只好在讀者面前現出枯萎的原形。”[3]這就是現實主義的斗爭。這是胡風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所發表的對于文藝創作的見解,我們可以明確地領會到,胡風對于新文藝“啟蒙主義精神”的繼承,以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文藝的走向應該如何的設計與解答。只有這樣的現實主義才能抗擊法西斯主義以及封建主義的精神壓制,才能取得最徹底的解放。而備受爭議的舒蕪的《論主觀》則從哲學的角度具體闡釋了何為主觀,主觀作用自身的發展是怎樣的情形以及為什么說發揮主觀作用是今天戰斗的武器。《在瘋狂的時代里面》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壓迫尤其是精神壓迫依然存在,舊的勢力做著最后的掙扎、叫囂,甚為瘋狂,而新生力量“被冤屈所啃嚼,被痛苦所燃燒,被失望所窒息”,也就陷入了另一種瘋狂里面。如何才能從這瘋狂的泥淖里走出來,獲得堅強與健康呢?胡風剖析到:“這堅強,這健康,從客觀上說,是產生自歷史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的結合里面,從主觀上說,是產生自巨大的熱情和遠大的認識的結合里面。”[5]前者提供了運用戰略的基礎,后者提供了相應的能力,而道路則在于客觀情勢里斗爭的過程。在這里,胡風強調了主觀、客觀結合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之上,主觀的努力是關鍵的環節。這依然是其在重慶時期“主觀戰斗精神”的重申。
每期的“編后記”提綱挈領般地點出了胡風在編輯《希望》時所持定的原則,足以代表胡風的文藝理想,也反映出當時文藝界的創作狀況。他所說的嚴肅的文學觀側重于對黑暗的批判,他所承繼的魯迅精神是對魯迅的戰斗性的強調。
[1]王大明,等.抗戰文藝報刊篇目匯編[G].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354.
[2]胡 風.編后記[J].希望,1945(1).
[3]胡 風.編后記[J].希望,1945(1).
[4]胡 風.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G]//胡風評論集: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15.
[5]胡 風.編后記[J].希望,1946(4).
[6]胡 風.編后記[J].希望,1946(1).
[7]舒 蕪.魯迅的中國與魯迅人道路[J].希望,1946(1).
[8]胡 風.編后記[J].希望,1946(2).
The Journal’s Tendency Seen from Its Editor Hu Feng’s Post-editorial Remarks of Hope
ZHAO Shuanghua
(Chinese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From"Post-editorial Remarks"of Hope,one can see the editor Hu Feng’s or the journal’s serious literary view,the spirit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from Lu Xun,and the subjective fighting realis m.Having in mind a clear editing idea,Hu Feng carried for ward his literary ideals further now than when he was editing July.Editorial remarks of each issue best express his tendencies.
Hope;HU Feng;Lu Xun’s spirit
G237.5
A
1674-117X(2010)01-0079-03
200-11-04
趙雙花(1980-),女,河南南樂人,山東省濟寧學院中文系講師,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
責任編輯:李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