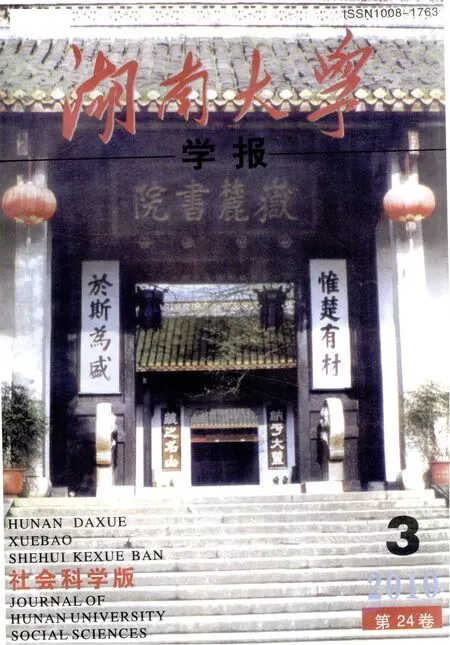存在主義文學的東方化表述——論村上春樹和王小波的小說*
楊經建,李 蘭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南長沙 410081)
存在主義文學的東方化表述
——論村上春樹和王小波的小說*
楊經建,李 蘭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南長沙 410081)
以王小波和村上春樹的創作相似性為出發點進而發掘其存在主義的意義蘊涵和藝術特質,是對東方式存在主義文學更為嚴謹而合理的探索途徑。事實上,村上春樹和王小波作品中的存在主義傾向有其共同的歷史文化及思想資源:同處于東亞文化圈和都遭逢現代性民族生存危機;他們的創作表明了東方式存在主義文學的成熟并表現在:首先,他們的小說作品展現了一個“荒謬”世界,這種“荒謬”已不再僅僅是人的一種生存感受,它充盈著的是對人的嚴酷壓制,它所帶來的是人的激劇異化。其次,他們的作品體現了對“孤獨個體”的強烈關注,作為人物形象主體出現的“孤獨個體”既接受了“孤獨”的客觀存在又從內心拒斥“孤獨”加諸于人心的苦悶和郁結。其三,他們的創作呈示出特定的詩性訴求方式,即憑借想象力和幽默品質來表達對存在主義“詩”之“思”的藝術言說。
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文學;東方化存在主義;王小波;村上春樹
20世紀后半期有兩位東方作家幾乎同時掀起了閱讀熱潮——他們就是村上春樹和王小波。他們雖然相隔萬里且素昧平生,但卻有著種種令人稱奇的巧合之處。倘若對他們的創作觀念和藝術理念稍加審視便可發現,存在主義文學的東方化正是將他們聯系起來的紐帶。
一 存在主義的東方化重構
無疑,存在主義是西方現代文明危機的產物,“究其實質,存在主義哲學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處于危機階段的產物,它既是對這種危機的曲折反映,又是對這種危機的病態抗議。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存在主義是一種危機的哲學。”[1](P33)情況的確是,西方文明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之后,終于在20世紀暴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危機,一些先進的西方國家普遍感受到一種文化與精神的危機。于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像一列即將出軌的列車,龐德將其比作衰暮之年的妓女,而艾略特看到的則是種植著尸體、生長著死亡的荒原。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更是用了比“危機”更聳人聽聞的“沒落”(Untergang)一詞。相對而言,對現代西方文明危機感受最強烈的是以海德格爾和薩特等人為代表的存在主義運動。“存在主義哲學,正是資本主義文明走向危機階段的產物,它反映和表達了現代人覺得自己喪失了意義之源,處在一個異己的世界里,完全沒有安全感的這種危機和焦慮的心理狀態。”[1](P34-35)存在主義思想家從人的生存結構分析出發,直面被技術理性所異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他們不再把空虛、孤獨、畏懼、煩惱、無意義、有限、缺憾等現象歸結為暫時的歷史現象,而是視其為現代人生存結構的內在要素。他們從生命存在的悲劇意識中挖掘反抗文化危機的力量,高揚和強調人之自由和歷史選擇的責任感。
“一種嚴肅的哲學總是既有現實性又有超越性,即使是一種唯心主義、主觀主義、非理性主義的哲學,只要它確實嚴肅地觸及到特定的歷史實際而又深刻地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問題——哪怕它的提法是片面的,回答是不正確的——這就仍然無害其為真正的哲學,就對人類永遠具有啟發意義。存在主義正是這樣一種哲學。它在現代文明的基礎上深刻地提出了人為什么活著,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何在,個人如何達到真實的存在,獲得本真的自我等等深刻的哲學問題,而這些問題并不僅僅為西方人所關心,也為東方人所關心,它們曾令人困惑,也令我們今人困惑。通過這些問題的獨特拷問和思索,存在主義突出地強調了人的存在的主體性,強調了個人的自為與責任,這不僅對西方人有現實意義,對我們也有啟發意義。”[1](P36-37)
必須申明,本文所提出的“東方化存在主義”是指當存在主義從西方語境中被抽取出來放置于東方語境后,它不再是由西往東的移植而是對東方已有話語資源的整合、重構基礎上的“新生”,存在主義文學由此獲得合法性身份并表現出強烈的東方化或本土化意向。眾所周知,中日兩國的文化本身就具有親緣性乃至同源性本質。日本明治維新以后,佛教和儒學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現代性變革的迫切要求,于是西方的現代思潮開始涌入東瀛,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的名字逐漸為日本知識界所熟悉。一戰之后,日本進入了危機頻繁的年代,社會在經濟危機和工農革命的攪擾中動蕩不安。驚恐焦灼、憂慮沮喪的情緒在普遍蔓延,許多知識分子都陷入了雖不甘于沉淪,但掙扎卻又徒勞無益的困厄之中。于是存在主義獲得了在日本進一步傳播的機會,并漸次風行于日本哲學界。可以說,“大凡在現代日本哲學史上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義的影響,在他們的思想上鮮明地打上了存在主義的烙印”。[2]日本近代先后出現過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三木清、和辻哲郎等本土化的哲學家,他們在吸收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成果的基礎上又對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和拓展,進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學體系。至此,存在主義哲學開始滲透入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雖然它并未大張旗鼓地占據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但已成為戰后日本社會意識中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潮。而生存于村上春樹時代的日本人,常常會被一種不安的情緒所侵擾,不是擔心世界大戰將臨,也不是對饑荒的懼怕,而是憂心于心靈的枯萎。
而理解20世紀中國“現代性”危機的特性,也為原本作為一種危機意識出現的存在主義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照視角。“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歷史文化的“現代性”轉換。然而這種“現代性”轉換恰恰是由世紀性危機——中國傳統文化衰敗的意識危機和民族生存的現實危機促成的。20世紀中國的“現代性”因此也負有雙重歷史使命:建構新的現代化文化體系以克服傳統文化衰落而導致的意識危機;建構現代民族國家以解決民族生存的危機。如果說,“五四”啟蒙運動期望以“科學”的方法克服意識危機,以“民主”的藍圖重建社會政治秩序,那么,隨著啟蒙運動內部的分化以及對“科學”和“民主”的理解出現分歧,“現代性”不再是一個統一的、自明的范式而是在西方各種思潮的影響之下分化成多個尖銳對立和緊張的主義話語的思想模型。各種“主義”話語對危機各有各的解決之道,但又因此帶來了新的問題:不僅傳統的危機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加劇了危機本身。可以這樣說,除了短暫的個別時期之外,這兩大危機籠罩著整個20世紀中國。[3]如果說“五四”啟蒙運動應對的是新舊社會更迭的陣痛之下歷史斷裂的危機,那么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所直面的則是文革劫難以及劫難之后信仰失衡的危機。“當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又重新開始自己的世俗化進程時,新意識形態如同當年的儒家文化一樣,也發生了嚴重的意義危機。隨著信仰世界的重新真空化和工具理性的高揚,這一危機不僅具有傳統的性質,而且也帶有現代的特征,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綜合癥狀。”[3]“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如此嚴重的意義危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的一種特殊現象。”“凡此種種,組成了一個深刻的、全面的意義危機,貫徹了 20世紀大部分時期。”[4]從這個意義上說,被定位為“危機哲學”的存在主義要在中國找到適宜滋生的環境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總之,從東方或東亞文化源流的角度來看,中日兩國同為西方哲學思潮的領受者,在將存在主義移植到本土的過程中,兩者也就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同質共鳴”。而藉由著這種“共鳴”,具有本土化思維特征的“東方化存在主義”的出現也就在所難免了。
應該說,所謂東方化存在主義不是以哲學概念的方式呈現的,因為在東方,本就存在著以文學的方式來思考哲學的傳統,譬如《道德經》、《莊子》,在此意義上,它更多地展現在東方人的生存體驗之中,尤其是呈現于文學創作中。由是,村上春樹和王小波的具有存在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的出現,無疑是存在主義在東方語境中“本土化”的一個表征,也表明了東方式存在主義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的成熟。雖然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已被公認為“東方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但本文之所以舍大江而取村上是由于:大江作品的輻射面和影響面并不見得就比村上廣;以大江一人或日本一國,難以代表和詮釋存在主義文學的“東方化”。筆者選擇村上春樹和王小波的小說作品進行整合性研究,一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具有相當的藝術水準——這在文學界、評論界都是公認的;二是他們的作品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如村上春樹的權威譯介者林少華所言,這兩位作家存在著一種“骨子里的相似”,甚至達到了“鬼使神差形神俱肖”,[5]正是這種“神似”使其具有了類似于數學上的合并同類項式的闡述的可能。三是就“東方”這個歷史文化范疇而言,將日本當代作家村上和中國當代作家王小波放置到同一個參照層面上進行考察和剖析,相對而言似乎更能嚴密而完整地展現出“東方化”語境下存在主義文學的形態特征。
二 以荒謬性存在為核心的主題話語
在存在主義哲學中,“荒謬”是現實世界真實的存在狀態。兼存在主義思想家與作家于一身的加繆其《西西弗的神話》的副標題就是“論荒謬”,加繆自己曾表示作品要表現的主題就是“面對荒謬的赤裸裸的人”。加繆認為,所謂荒謬是生命存在的一種特殊狀態。因此,從人與世界既定的關系出發,探索處于荒謬存在狀態中人的出路,賦予荒謬人以現實實踐的反抗,在原本并不自由的荒謬世界中探索人之為人的本真存在方式才是其意旨所在。海德格爾指出,作為“存在”的人面對的是“虛無”,人孤獨無依永遠陷于煩惱痛苦之中。他把人這種特殊的存在者稱為“此在”。“此在”發現自己未被征詢也未經自己同意就被無緣無故地拋擲在世,這種“被拋狀態”絕對的孤立無援,從根本上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但又不得不把已經“在世”這一事實承擔起來,獨自肩負起自己的命運。當人在當下的直覺體驗中看到自己的存在根本上是曖昧不明沒有根據時,人便感到無所庇護的恐懼和無家可歸的煩憂,感到根本的虛無和存在的荒誕,這正是人的存在的最大荒謬之所在。而在薩特的哲學中,世界是荒誕的思想非常明確。薩特在《厭惡》(又名《惡心》)中指出,“荒謬這不是我腦子里的一個概念,也不是一個聲音,而是在我腳下的這條沒有生命的長蛇,這條木蛇。不管這是蛇,或者爪子,或者樹根,或者禿鷹之爪子,都沒有關系。雖然沒有清楚地闡明什么,我卻懂得我找到了‘存在’的關鍵,我的‘惡心’的關鍵,我的生命的關鍵。事實上,我緊接著能夠理解的一切,都可以歸納到這種根本的荒謬中去。”[6]
在村上與王小波的作品中,荒謬的存在就寄身于日常生活形態中,但又處于被遮蔽的情形之下,人們對之漠不關心且視而不見。他們于是將現實中的荒謬進行了提純和放大,從而使得世界的荒謬本相變得更加清晰,存在的荒誕性成為他們創作的基本主題話語。與西方存在主義作家不同的是,這種東方式書寫所呈現的荒謬常常通過對歷史的回憶和現實的重現來實現與世界的溝通。可以說,村上的小說所敘述的故事本身有許多都是荒誕而離奇的,并且極富寓言性。正如杰·魯賓所指出的,“尋找”是村上作品的核心。[7]荒謬的世界在尋找的過程中展開,而在尋找的末端所放置的卻是徹頭徹尾的虛無。王小波的小說按所述時間而言,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歷史小說,如《紅拂夜奔》、《尋找無雙》;一是現實小說,如《黃金時代》、《我的陰陽兩界》、《似水流年》;一是未來小說,如《2010》、《2015》。但不論他的主人公生活在哪一個年代,其生存空間都是由荒謬構筑而成的。尤其在他的歷史和未來小說中,夸張的想象力已經發揮到極致,世界的荒誕也由此到達了頂峰。
事實上,對于存在本相之荒誕性的曝光,村上和王小波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他們都著眼于現實。“二戰”是一個經常飄忽于村上小說中的敘事背景,而“文革”則是王小波小說主人公的活動舞臺。其次,他們都借助了超凡的想象力。在村上的小說中現實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往往會同時出現,而王小波也慣于神游時空隧道,在古代和未來的想象空間中揮灑恣肆。由此可見,在兩者的作品中,對荒謬的發現雖然也是借助情緒體驗來完成的,但它并非通過沉湎于自身來領悟,而是藉由現實本身來訴說。因此,荒謬不是抽象的哲思,而是人們正在經歷著的世界。當現實世界讓人對于理性和理想的希望屢屢落空之后,人在荒謬背后讀到的就只有深深的絕望。歷史其實就是對現實的預言,而未來則是對現實的放大。
荒謬的世界之所以荒謬,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剝奪了人的自由,壓抑了人的天性,對人采取了嚴酷的壓制。在村上筆下的荒謬世界里,黑暗勢力高漲,人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到了逼仄的境地,人必須在成為犧牲品和失去自我之間做出選擇。《尋羊冒險記》中的“羊”操控著“先生”的心智,藉“先生”之手暗中控制著整個日本島,并牽制著主人公的一舉一動。《舞!舞!舞!》中控制日本地產界的黑色組織和日本政界人物一起合謀將老海豚賓館硬性拆除,同時隱秘控制招妓組織,秘密謀殺不守規矩的小姐。《奇鳥行狀錄》中,妻子的哥哥綿谷升不但控制現實的政治,更控制了人的思想,硬生生地將人變成“意識娼婦”。王小波的小說世界則是在集權與專制、權力與暴力的合伙預謀之下被推向荒謬的。在《黑鐵時代》里,所有上過大學的人都必須住進有營業執照的公寓,也就是黑鐵公寓。問題在于,黑鐵公寓是以邊沁的“圓形監獄”為藍本來設計的。這種“圓形監獄”利用建筑上的逆光效果,使得監視者的單向視線內化為犯人心理上無時無刻不在的一個存在,從而成功地將外在的他律轉化為了犯人內在的自律,毋寧說是被迫的自律,以至于讓個人逐漸演變成壓制自己的幫兇——這對于無辜的人而言就是最殘酷也是最變態的壓制。在這樣一個本末倒置的荒唐邏輯下“黑鐵公寓”堂而皇之地成為了“黑鐵時代”的核心。
村上和王小波之所以不惜筆墨地刻畫現實環境對人的嚴酷壓制,關鍵就在于呼喚“人的自由”依舊是東方文學的表現主題之一。而那種根基于社會權力話語和所謂的大眾“集體利益”之上的變態壓制越是顯得嚴酷,就越說明了人們對保持尊嚴和實現自由的強烈渴求。它不單展示了個體生命在荒謬世界里的孤苦和彷徨,更凸顯了人們內心深處對物欲橫流和私權泛濫的社會現實的深惡痛絕,以及對社會異己壓迫力量的無情鞭撻。這就恰好呼應了經典存在主義所主張的“人是自由的產物”、“人須得返歸真我”以及“人應該保持精神主體的特異性”。
存在主義哲學認為,只要人存在于社會之中,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承接他人眼光的評判,就不可避免地會遭受到異化。異化就是一個由真我到非我的離心式運動,從而造成本真自我的沉淪和失落,而荒謬的發現就是借助異化的感受來完成的。正是在存在者的異化狀態中,人們面前所鋪陳開的就是當下的生存空間:荒謬因此已不再僅僅是人的一種生存感受,它還能進一步影響到人的生存狀態,它充盈著的是對人的嚴酷壓制,它所帶來的是顯而易見的人的激劇異化。
而在村上的小說中人的異化大致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人物設置符號化。比如在《1973年的彈子球》中與“我”同居的雙胞胎姐妹,她們沒有名字也沒有來歷,如何稱呼她們也只源于她們平日穿的汗衫,一個叫“208”,一個叫“209”。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奇鳥形狀錄》中的“赤坂肉豆蔻”和“赤坂肉桂”以及《舞!舞!舞!》中的高級妓女咪咪。事實上,這些都是經過“人們”異化之后的人,已經喪失了存在的特異性,他們可以方便地消解于“人們”之中,如同滴水入海,完全無跡可尋。其次是人物內在的異化。在村上的小說中金錢、權力、名譽、地位這些浸透著人類欲望的物質可以把人異化成披著羊皮的“羊男”,變成像綿谷升一樣喪失良心和靈魂的野獸。而且,這樣的野獸又會在世界上肆虐,接著傷害、毀損其他的人,把其他人變成工具、殘廢、空殼、行尸走肉,使得其他人成為活著的死人、死去的幽靈、或者半死不活的受難者。
王小波小說中被異化的形象更可謂面目繁多。其中有些是整個外形都被異化了,比如《綠毛水怪》中的妖妖變成了水怪,《萬壽寺》中的薛嵩變成了馬,《這是真的》中趙助理變成了驢,《戰福》中戰福變成了黑狗;有些是部分的異化,比如《紅拂夜奔》中吹火工的嘴變成了鴨嘴。王小波的異化形象事實上是對人的生存本相舉重若輕的描摹,更是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荒謬世界的強烈批判和鞭撻。并且,除了同情弱者、抨擊惡者而外,王小波小說中的異化還具有消解現實郁結的作用。比如《2015》中的畫家王二,他所棲居的空間只允許“寫實的藝術”和“老百姓看得懂的藝術”,這令他渾身不自在,卻又不得不被逼著逆來順受。他靠畫畫營生,卻因沒有執照而被捕。事后他一聲不吭,只管往肚里咽氣,這才脹成了一個氣球,飄上了天花板,把警察們都弄得哭笑不得。還有《綠毛水怪》中的妖妖,敏感的她因為厭惡、且不得不面對世界的偽善,所以選擇變成水怪,久居大海,避開人世。
換言之,兩者創作中所描述的異化指的是個體生命失去了生存的尊嚴、價值和意義,最終失去了自我的結果,是人倍受荒謬世界的嚴酷壓制所產生的無奈情緒的另類表達。它所顯示的不僅僅是西方存在主義所說的人對于真我的疏離和拒斥,更包含了外在力量對人性以及基本人權的扭曲和踐踏,所以它更具有批判精神和隱喻色彩,它的象征意義也就更加豐富多彩且意味深長。
三 孤獨生存著的人物形象主體
問題在于,荒謬作為人與世界之間價值關聯的斷裂對于人而言是本源性的。這種本源性就來自于世界和人本身原初的虛無化。虛無構成了人在世界之中最為本真的生存境況。處身于這一境況,人的基本生命情態亦即人對這一境況的基本情緒體驗就是孤獨。“孤獨個體”原本是存在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哲學的核心概念,其“孤獨個體”指的并不是生活中感性而具體的人,而是具有特異性和區別性的精神個體,這個精神個體之所以“孤獨”,是因為“孤獨”是本己存在的狀態,也是本己發現自我的前提。
以海德格爾之見,孤獨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感受,它體現為個體對世界的一種出離狀態。實質上,孤獨感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性情感體驗,每一個時代、每一種文化中的個體當他從所寄身的世界中抽身而出的時候,當他反身自問“我是誰”的時候,都會生發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嘆。存在主義哲學所理解的孤獨是因世界的虛無性造成的生命無所依憑的孤獨,而孤獨會使人更加意識到孤獨的存在,存在的生命又會向孤獨去尋求意義。孤獨也永遠是最忠實于自己的,它順從著自己的精神,任何一種偽裝的繁盛和喧嘩都無法抵擋內心對話的清醒,是孤獨把人同紛擾的世俗世界拉開了距離,人才獲得一種看世界和看人生的不無悲觀卻是新特的視野。亦即,這是一種因自由而生的孤獨,所以在這種孤獨的后面蘊含著荒謬的意念。“存在主義最引人注目的是關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處境意識與生存意識是最鮮明的,也是存在主義的起點。”[8]也正是在“生存”的意識下,周圍的客體才不再是與主體對立的客體而體現為一種“處境”。于是生存意識(孤獨)與處境意識(荒謬)總是聯系在一起的,就像雅斯貝爾斯所說有處境意識即是意識到生存,達到生存意識與處境意識,要求一種直接的體認。[8]
故而,存在主義文學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會自覺體認和品味孤獨,他們幾近于一個個哲學家,孤獨成了一種冷冽卻同時又極為寶貴的生命體驗。而在王小波和村上的東方式存在主義文學作品中主人公們對于孤獨的接受和拒斥幾乎是并存的:一方面他們接受了孤獨的生存狀態,在對孤獨情緒的沉湎中領受著存在的荒謬和虛無;另一方面他們又從內心拒斥孤獨加諸于人心的苦悶和郁結,就在這種接受和拒斥的張力中,他們最終實現了對自我的體認。并且尤為重要的是,對他們而言孤獨既是他們不得不直面的困境,還是他們追求自由所必然導致的結果,更是他們追求自由所必須具備的前提。
村上小說的審美基調就是孤獨與無奈。其創作沒有氣勢如虹的宏大敘事,沒有雄偉壯麗的主題雕塑,也沒有指點自己走向終極幸福的暗示和承諾。但是他有生命深處刻骨銘心的體悟,有對個體心靈自由細致入微的關懷,有時刻警醒本初自我的高度敏感,而這一切最終都歸結為四個字:守護孤獨。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因為那種“刻骨銘心般”的孤獨感醞釀出了一種特殊的情調,恰好呼應了讀者們內心深處被現代文明抽空了的角落,讓讀者們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但較之孤獨與無奈本身,作者著重訴求的似乎是對待孤獨與無奈的態度。不難發現,村上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一個個平淡無奇的小人物。他們完全困囿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排斥與社會進行交流,不愛看電視也不愛讀報紙,喜好一個人靜靜地吃點東西,聽點音樂,偶爾也看一兩場電影。這幾乎就成了現代“零余人”的形象。村上的孤獨并不僅僅出自小市民式廉價的感傷主義,不單單是對個人心境漣漪的反復咀嚼,更多的是源于對人的本質、生命的本質以及自身處境的批判性審視和深層次質疑。與村上小說相似的是,王小波小說的主人公——“王二”們的孤獨也根源于荒謬而逼仄的外在世界;但與村上小說所不同的是,“王二”們的孤獨還應歸咎于他們個性本身的特立獨行——他們痛恨虛偽的道德和束縛人天性的“秩序”,把“蓄意”破壞既定秩序和捉弄張牙舞爪的可笑“權威”視為無趣人生的最大快樂。但在那個時代,言行出格、表現乖張、特立獨行,是最為求同伐異的“集體主義”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們有的被別人嘲笑為“小神經”(《似水流年》);有的在倍受打擊和陷害之后逃往了荒山野嶺(《黃金時代》);有的整日躲在地下室中,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我的陰陽兩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并且,在王小波的小說中“孤獨”和“寂寞”類似于一種流行病,只要是他小說的主人公就必得無疑。與村上小說的主人公們消極被動的態度所不同的是,“王二”們對待孤獨是積極且主動的。既然無法回避,不如主動承擔。尤其是,倘若居于“孤獨”就可以享受到“自由”的話,那“孤獨”也將不再是毒藥而會是佳釀了。所以“孤獨”在追求“自由”的“王二”們那里逐漸成為其自覺自愿的生命狀態,甚而成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精神品格。
在存在主義哲學中,“自由”也是一個處于核心地位的話語概念。雖然存在主義者對自由的解釋各有其獨異之處,但其共同指向則是,存在主義讓人在一個“沉淪”的世界里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和自由。個體在人世間的本然處境是絕對的孤獨無助,“此在”融身于其中的實在世界無法為他的生存提供堅實的根基和意義根據,孤獨個體想要獲致本然的自我或本真的存在,只有獨自擔當生命的全部問題。在這個前提下自由意味著個體必須選擇和創造他自己,把存在的責任全部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這就是薩特所謂“存在先于本質”。實際上存在主義時代最核心的問題也正是:讓自由接受荒謬之考驗,讓無所依靠而只有回溯到自身選擇的個體勇敢的面對周圍世界的悖謬。而只有存在的自由在荒誕前被見證,人的選擇所承諾的意義才成為可能。存在主義者在諸如個體的自由,選擇的重要性,承擔作為真實的人類存在的義務,人類生命除人類所賦予的以外沒有其他意義等觀點上看法都基本相同。誠如薩特在1960年所發表的童年自傳《詞語》中所寫:“我寫作,故我存在。”
而“自由”之于東方化存在主義卻同時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自由一方面仍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永恒的向往,另一方面還是人對抗荒謬現實、擺脫生存困境的方式。之所以兩種自由并存,是因為在東方世界里包含了民主、科學、自由之精神的現代性理念對東方思想文化從根源上的滌故更新還遠遠沒有完成。而現代商業社會對人的“物化”和“異化”又時刻盤算著把人打包成為商品,編譯成失去個性面目的符號,這就與歷史泥垢中所遺剩的殘渣余孽一同合謀將人變成了社會機器的奴隸和自身欲望的奴隸。在此意義上,自由其實就是回歸自我,也意味著允許存在方式的多樣性。追求自由也就是為“此在”去除規定他存在方式的枷鎖。
村上小說的主人公總在追求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但同時這些主人公們卻又對自由的實現抱著悲觀的態度。在他們而言,或許自由根本就是絕難變為現實的一種想望——自由不僅是難以實現的,追求“自由”的“后果”還往往是非常嚴重的。在《海邊的卡夫卡》中,圖書管理員大島就曾對主人公田村卡夫卡說:“田村卡夫卡君,或許世上幾乎所有人都不追求什么自由,不過自以為追求罷了。一切都是幻想。假如真給予自由,人們十有八九不知所措。……在這個世界上,是建造高而牢固的樊籬的人類有效地生存下來,如果否認這點,你勢必被趕去荒野。”——這既類似于一種警告,又仿若是對實際情況的客觀陳述,而王小波的主人公們就是這么一群“被趕去荒野”的人。
王小波的“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系列小說中的世界則是一個“無智、無性、無趣”的荒謬世界,公共權威對私人生活空間進行肆意的踐踏和侵犯,無休止的傳喚、審訊、批斗成了主人公們的生活主題。而履行統治職能的國家權力機構,諸如派出所、監獄、改造農場和采石場、再教育營地、習藝所、堿場、公司等,無處不在地鉗制著人的日常生活;竊聽器、攝像機則漫布了整個生活空間。系列小說中的主人公——“王二”們都厭惡這種平庸的世界,不務正業且不履常規,顯得“和別人不一樣”。事實上,“愛自由”是作為“王二”們的本質來存在的,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與自身存在所并立的無法割裂的精神特性。
東方式存在主義者之所以如此迫切于對自由愿望的表達,關鍵就在于東方有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發展格局——直至如今,西方許多現代化的進步意識都還沒有在東方得到完全充分的發展,然而包括了自由觀念在內的這些進步意識卻又是東方世界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基礎條件。于是東方的存在主義者們就自覺地承擔起了呼喚自由的重任——“追求自由”是他們個人的思想要義,跨入自由之境更成為了他們的畢生理想。
四 對“存在”之“思”的東方式訴求
海德格爾在其《詩·言·思》中指出“一旦人類思考了無家可歸,那么悲慘的事將不再發生,正確地思考并牢記于心中,這就是把短暫者引進居住的唯一召喚。”在這種“唯一召喚”下存在者進入理想的生命狀態 ——“詩意地棲居”。[9]“在海德格爾看來 ,美學與其說是一個藝術的問題,倒不如說是一種與世界聯系方式。”[10]這也意味著,由存在的本體論范疇推導出審美的本體論性質,因此對于審美活動的本體論內涵的揭示就不僅僅是一個美學問題,而且是一個文化哲學問題。所有這些表現在存在主義文學中就是一種“知性寫作”的藝術思維方式。如昆德拉所言文學是“關于存在的詩性沉思”[11]。故而卡夫卡筆下的甲殼蟲、小動物、饑餓藝術家,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貝克特劇中的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帶有“死屋”和“地下室”氣息的病態人物都是最為有力的存在主義者,他們開辟了文學面對靈魂的新的方式,在思索著存在的種種問題中表達著一種“迷惘的形而上學”[12]。他們的創作每每在荒誕的生存中發現希望(意義),就是為生命存在的品質樹立起一個神圣價值參照,沒有神圣價值參照的存在只是一種深淵似貧乏。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存在主義文學對人的生存性荒誕的勘探直指人的心靈深處,對荒誕根源的探索是從人的自身尋找原因,有一種深沉的自我追思和自我檢視,是一種雅斯貝爾斯所說的“偉大度量”。[13]于是在存在主義文學中,“詩”(藝術)與“思”(哲學)以不同方式對同一本源加以言說,“詩”是人進入存在的開端,是穿透人的歷史的詩性啟悟——一種深刻的個體化理解和體驗;“思”是對存在顯現的本真的領悟,存在之“思”是原詩(U r-dichtung),一切偉大的詩篇總是沉醉于一種本源之“思”中——一種批判性創造,“詩”的本質因而以“思”為依據。
由于東方的歷史文化和話語知識譜系缺乏宗教的終極關懷意識和神圣拯救情懷,東方式存在主義文學對“荒誕的存在”和“孤獨的生存”的表達并不是一種深邃的哲學體悟,而是一種特定的東方化訴求方式。在王小波和村上的小說中這首先表現在其創作將經典存在主義對于“詩之思”的“思”——知性思維的偏重轉向對“詩”——偏重于創作的感性抒寫層面。問題也許在于,感性化抒寫是東方民族通過直覺和感悟把握世界所偏重的表現方式,東方傳統詩學關注現象世界、感物吟志并追求一種情調或境界,很少對人生萬物作深入玄妙的形上思索而因此缺少大的哲學思辯。因此東方文學在某種意義上缺乏那種對人的生存環境和狀況進行持續追問的勇氣,缺乏解決人類的靈魂問題的能力。于是王小波和村上的作品大都以純粹的心靈化或想象化的審美原則來重構文學的真實內涵,以便將(外在的)理想社會和(內在的)理想生命境界通過想象性關系連接起來,并藉審美之途來安頓此岸的生存。這或許是“詩意地棲居”的東方式解讀。
毋庸置疑,王小波和村上都是想象力異常卓越的作家。很明顯,村上的小說世界演示出了不亞于科幻、魔幻小說的大跨度的想像力。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光怪陸離,神鬼莫測。例如《尋羊冒險記 》、《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奇鳥行狀錄》以及后來的《斯普特尼克戀人 》,無不以看似荒誕離奇的想像力點化出現實世界中的本質性真實和人們的心理真實、潛意識真實以至靈魂的真實。而《海邊的卡夫卡》整部小說就是由想象構成的巨大迷宮,作品的題旨本身即是一個巨大的隱喻。簡言之,村上的小說一方面傳達現代人的焦慮、苦悶、迷惘、困窘、無奈和悲涼,點化他們的情感方式和生命態度;同時又給人以夢幻,為人們拾回破碎了的青春、愛情和生命,產生一種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瞬間接通時進入澄明天地的驚喜之情。
王小波的小說則在話語形式上擺脫日常生活秩序的制約而徹底地放棄經驗性、常識性的思維邏輯,使創造力超越一切常識狀態直逼種種奇跡般的可能性存在狀態,從而不斷地將敘事話語推向廣闊的想象化的審美空間。《萬壽寺》就在“我”所在的現實世界和薛嵩所在的小說世界之間平行展開了。薛嵩的世界是想象的世界,是動態的世界,是流動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則是現實的世界,是靜止的世界,是呆滯的世界。在“我”筆下所誕生的那個充滿了想象力的薛嵩的世界,對于“我”有著遠超于現實的意義。因而,小說中的世界就成了“我”超脫現實的翅膀,載著“我”于困境的上空御風翱翔。因此,王小波的創作往往能使憂郁、絕望、恐怖、焦慮等具有生存本體論意義的情緒體驗在獲得審美價值后進入敘事過程,以審美想象性來開發一種人性深處的生存狀態,一種更為潛在、也更為豐茂的生命情態,其內涵的意蘊由此也成為人的存在狀態的本體象征。
可以看到,“想象”對于東方存在主義文學而言,更具有實實在在的功能性作用。藉由著詩性的“想象”,這些主人公們可以找到心靈的棲居之所,進入無可阻擋的自由之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僅可以用來逃離現實的羈絆,它還能夠改變現實,乃至于影響命運的發展和走向。相對而言,兩者的“想象性”書寫的區別在于,王小波更像頑皮的孩子快步急蹈,而村上則有如優雅的鄉紳從容漫步。
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是以非理性主義為根基的存在主義的基本思想傾向。懷疑精神與危機意識在藝術審美層面的顯示則是悲劇性品質與悲劇基調。實際上,從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到雅斯貝爾斯的《悲劇的超越》,存在主義文學的悲劇品質就已昭然明示。對此國內學者如此言說:“存在主義的陰郁品格、悲劇基調、極端非理性主義和懷疑主義傾向,也使它難以在包括作家在內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那里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普遍的理解。”[1](P253)其實不止國內學者,當代西方研究存在主義的權威學者巴雷特亦有同感:“存在主義的確是歐洲表達方式,它的陰郁情調與我們美國人朝氣蓬勃和樂觀主義的性情格格不入。……像存在主義那樣討論問題的情調,必定被美國人看做失望與挫敗的征候,以及一般說來,也是趨于沒落的文明衰竭的征候。”[14]存在主義將人的整體生存狀態視為一種悲劇性的荒誕處境,存在主義文學的悲劇性品質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所呈現的“病態的愉悅”。[15]即如他在《地下室手記》中借助人物痛苦而孤獨的靈魂發出的絕望的哀鳴:“人們孤零零地世界上——苦就苦在這里!據說太陽賦予萬物的生機。太陽升起來了,可是看著它,難道它不是死人么?一切卻死了,到處卻是死人。只有一些人,而包圍他們的沉默——這就是世界。”其文學形象更多的是空無所有、一事無成卻又奮斗不息的“荒誕的英雄”——西西弗斯。乃至可以說,正是加繆筆下的“荒誕的英雄”——西西弗斯孕育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悲劇精神。
王小波和村上的創作盡管也一樣表現出“荒謬”與“孤獨”,同時也一樣具有著“他人即地獄”的思想傾向,但卻有別于西方存在主義作家那種以個體生命為本位的存在論立場,他們往往會不自覺地汲取東方文化中歷經久遠的儒、道、佛三位一體的安生立命哲學,淡化了尼采式極端精神和偏執意識所帶給的各種癥狀——將尼采的由毀滅和創造構成的悲劇精神變成了心存憂患的藝術體驗。面對著“荒謬”與“孤獨”,他們的作品始終不是以悲劇基調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審美幽默。
康德認為“在一切引起活潑的撼動人的大笑里必須有某種荒謬的東西存在著。”[16]這就暗示了,“幽默”所指涉的不僅僅是引人發笑的言行,更在于存在主體對于隱身于現實中的荒謬和乖離的發現,以及人們旨在消解此種情境下所產生的不安和郁結時的一種反應和態度。正如王小波在《紅拂夜奔》的前言里指稱:“我認為有趣像一個歷史階段,正在被超越;智慧被超越,變成了‘曖昧不清’;性愛被超越,變成了‘思無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會變得莊嚴滯重。”[17]也因此,王小波和村上作品中的主人公有著極為不同的幽默品格,鮮有加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那種悲憤情懷,作家的敘述筆調也不再僅限于抑郁、灰暗、沉重。兩者筆下的人物群體都無視被設置的生活軌道,王小波欣賞一只“特立獨行的豬”,村上春樹對毅然失蹤的大象情有獨鐘。兩人都力圖通過被邊緣化的小人物冷眼旁觀主流社會的光怪陸離,進而直面人類生存的窘境,展示人性的扭曲及使之扭曲的外在力量的強大與荒謬。不同的只是,村上的幽默是一種外冷內暖式的幽默,導致其作品中的人物通常都沒有尖刻的諷刺,沒有激烈的言語,更沒有反叛的舉止,他們的幽默比較安靜,但卻又讓人忍俊不禁。比如《挪威的森林》中的渡邊,其個性中沉郁和幽默幾乎是并存的。尤其是,村上善于將現實存在世界反照烏托邦的面目去寫,它所呈現的不是是非而是一種整體性荒謬:從前提到一切具體結論、細微末節的荒謬,但所有的荒謬背后都有一整套符合現實合理性的邏輯推理。在某種程度上,村上式幽默可以緩解小說內世界的無聊和壓抑,但卻不能為主人公們在實際意義上解開郁結。王小波以“時代三部曲”為代表的小說在幽默反諷的助推下展現出一種存在本體論的視角和獨特的悲劇氣質。如《黃金時代》中王二和陳清揚以精神上、性愛上的放浪不羈、輕松游戲消解了神圣、虛偽、莊嚴,而其中鼓動著一種奇異悖謬與酣暢反諷。王小波之所以注重幽默的運用,是因為在這種幽默中借助“王二”系列形象熔鑄了作家本人與生俱來的狂放、戲謔和狂歡本性,它能使敘述人在紀實與虛構、現實與想象、現時與歷史、生活與本文所構成的開放性敘述空間自由出入、往返。它是憑借寫作行為和書寫方式的一種充滿痛楚與迷惘的實踐。它反映的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現實世界的荒謬,它消解的是這個荒謬世界里的所謂的價值和意義。而兩者創作的幽默品質的區別僅僅在于,快感回落之后,村上沁出的多是凄寂與達觀,王小波則讓人萌生冷冽與悲涼。
質言之,幽默之于東方式存在主義文學而言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創作態度,正是藉由著幽默,王小波和村上作品中的主人公們才卸除了掩藏于他們內心深處的沉重,實現了從存在的焦慮——“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向“生命可以承受之重”——生存的憂患的轉換。
[1]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2]徐崇溫.存在主義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648.
[3]許紀霖.二種危機與三種思潮——20世紀中國的思想史[J].戰略與管理,2000,(1):67-72.
[4][美]詹明信.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A].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C].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5]林少華.2007讀書印象:王小波和村上春樹之間[N].中華讀書報,2007-12-19(12).
[6][法]薩特.厭惡[M].鄭永慧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1.164.
[7]林少華.哈佛教授眼中的村上春樹[N].中華讀書報,2004-05-26(11).
[8]李均.存在主義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5,6.
[9][德]海德格爾.詩.言.思[M].彭富春,戴暉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145,189.
[10][英]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M].王杰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00.
[11][捷]昆德拉.小說的藝術[M].唐曉渡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36.
[12]歐陽謙.貝克特的存在感悟:一種形而上的寓言劇[J].文景, 2007,(3):15-17.
[13][德]亞(雅)斯貝爾斯.悲劇的超越[M].亦春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30.
[14][美]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哲學研究[M].段德智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10-11.
[15]何云波.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文化精神[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85.
[16][德]康德.判斷力批判[J].韋卓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4.180.
[17]王小波.紅拂夜奔:序[M].王小波全集(第4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Oriental Narrative of Existential Literature——A Case Study in Haruki M urakam iand Wang Xiaobo
YANG Jing-jian,L ILan
(College of Liberal A rts,Hunan No 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the similarity betw een Wang Xiaobo and Haruki M urakami’s creations on literature,then exp lores it’s significance and artistic qualitieson existential literature.Haruki M urakami and Wang Xiaobo’sworks have show n the tendency that their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re homologous:They are both East Asians and have encountered ethnic survival crisis;Their wo rks have demonstrated the maturity of the o riental existential literature:Their novels show a“ridiculous”world w hich is alienation to human;Their wo rks embody the deep concernson the“lonely individual”;And their creations have show n the specific demandsof poetic form and exp ressed their thinking to the performance of existential literature w ith imagination and humor.
existentialism;existential literature;oriental existentialism;Wang Xiaobo;Haruki Murakami
I206.7
A
1008—1763(2010)03—0076—08
2009-10-28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金資助課題“20世紀中國存在主義文學論”(09YJA 751025)
楊經建(1955—),男,湖南瀏陽人,湖南師范大學現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文化.